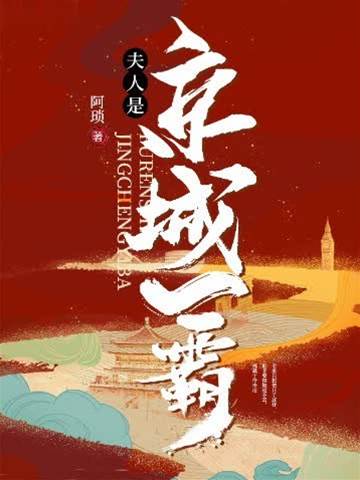《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180回:又是一場攻心計
“松將別來無恙。”染稍挽起羅衫大袖,為松針親遞上一盞熱茶,粲齒笑道。
松針忙地自圈椅上起,雙手接過,彎腰謝說:“有勞嬸嬸。”
他上一次見到染,還是在錦縣驛里。臨行前,對自己那個別有深意的笑,令他至今都記憶猶新。原來在冥冥之中,他和建晟侯之間的“緣分”,自那時就已牽連起來。
隋斜瞟了眼忍俊不的染,才多大,應該比松針還要小幾歲,就被松針喚作“嬸嬸”了?而且松針得面不紅耳不赤,開口就那麼自然麼?他這門親戚攀的,讓隋著實頭疼。
松針還惦記再寒暄客套兩句,卻被隋抬手打斷,要他閑言敘。
松針撓頭窘笑,繼而呷了口茶潤潤嗓子,便將國主凌澈的話一五一十地帶到。
聞言,隋哂笑一聲,長指散漫地搭在太師椅扶手上,隨意捻兩下。
“賢侄,你要是還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待一會兒在我這里用了飯便回去吧。”
“這,這……國主確實是這麼代侄兒的啊。不管叔叔想干什麼,東野配合您做就是。”松針將上得溜直,大義凜然地說。
隋挑眉側目,細長的瑞眼似乎已將松針看穿。他如此打太極,無非是想拿一下主權,這是松針唯一能爭取一下的東西。
但著急的人不是隋,亦不是坐在他旁邊的染,更不是避在東正房里暗聽的侯卿塵。
時間眨眼即逝,松針快些坐不住了。
染朝鄧媳婦兒使了個眼,鄧媳婦兒即刻為松針把茶盞添滿。
“嗐,早說了我不是這塊料,非得我演這麼個角兒!”松針狠拍了下自己的大,憤慨地道。
他再度起,昂首說:“東野荒不斷,侯爺卻坐擁百余畝良田,我來時瞧那稻谷長勢甚好,今歲必收。東野人雖很食稻谷,但侯爺若是想賣,東野樂意照單全收。”
Advertisement
“不賣。”隋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哈欠,覺得自己聽了個笑話。
“你,你還要怎樣?國主允諾侯爺盡管出價,東野就是再貧瘠也差不了侯爺這份錢。”松針據理力爭地道。
隋支開長站起來,朝水生吩咐:“帶松將去前院歇一歇,晚膳備些好酒好菜送過去……”
“叔叔,別啊,侄兒大老遠來一趟,不能就這麼被您打發走了!”松針騰地一下撲上前,扯住隋的風袖苦苦央及道。
隋眸微垂,不豫地瞅向他那只手。松針是拿開也不是,不拿開還不是。
他索咬了咬牙,說:“侄兒錯了,侄兒不該跟叔叔耍心眼兒。叔叔手里到底有多糧食?東野買,東野全買,是我們需要叔叔幫忙度過荒。但懇請叔叔高抬貴手,千萬別抬價,您知道到了歲末我們還得給北黎納貢。”
到此,松針上所有的“皮”,終被統統掀下來。
隋和他打了一場心理戰,他輸得很狼狽。主權讓給隋,他變了被的一方。
隋沒有坐回來跟他繼續相談,不過改了口徑,邀他晚夕同自己一起用飯。旋即,還是被水生送回金甲塢中小憩。
郭林在霸下洲廊下假模假樣地轉悠,可算逮住寧梧的影,徑直將拉到月門之后。
他目深地盯著,口起起伏伏,說:“今兒出去欺負了?”
“就這?”寧梧冷笑,銳利的鷹眼卻略略閃一下,眼底里藏著一。
“不就是姓夏的他們家嗎?趕明兒我找個機會替你出氣。”
“用得著你來幫我?一個臭未干的黃丫頭,我至于和置氣?再說夫人已替我出頭。”寧梧隨手揪了把樹上綠葉,一腦拋到郭林頭頂。
Advertisement
郭林也不惱,抬起大手撣了撣,憨笑道:“我不是怕你欺負麼?沒事就,知道你手好,但又不是時時可亮出來。”
寧梧擰眉,厭嫌地瞥他一眼,撂下一句:“沒什麼事我回了,你們后院有那麼多活,老跑出來什麼懶?信不信我到侯爺和夫人面前告你的狀?”
“眼瞅著就要落幕,還干什麼干?再說我好歹是個頭兒,怎地不能清閑一會?”
郭林無所畏懼地提高嗓門,彰顯自己在侯府中的地位。
寧梧覺得他那傻乎乎的樣子很是可,然而還是送給他一個大大的白眼。
二人所站之,恰是府中人走的必經之路。沒過一會兒,便將范星舒給吸引過來了。
“要我說你什麼好?選這麼個破地兒和寧姑娘言語,郭呆子,你還真是個呆子啊!”范星舒一壁說,一壁繞開寧梧,他太清楚的手段,要是被打上一拳,沒有三五天絕不可能緩過來。
寧梧鷹眼一掃,狠狠地說:“你皮子又了?”
“沒、沒。”范星舒急忙陪個笑臉,朝寧梧拱了拱手。
寧梧懶得跟他們繼續廢話,眼睛脧向前面垂花門方向,終是問出口:“東野只派松針一人過來,那個小郡主沒有跟著麼?那些走狗扈從沒有尾隨?”
“就他一個人,我查過了。”郭林拍著脯道。
其實凌恬兒很想跟松針一起來見隋,畢竟有正當理由再次邁建晟侯府,求之不得。凌澈不同意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大興山被康鎮巡防得太切。羅布試過好幾次,差點就被邊軍給逮住。
郭林心里明鏡兒這一點,可他絕不會在寧梧面前夸贊康鎮。他不覺得自己比康鎮差勁兒,他堅信自己定能打敗康鎮,到時候就沒人能跟他搶寧梧了。
Advertisement
“要是松針這次和侯爺談妥,咱們和東野之間的來往就此打開。寧姑娘還想會會那小郡主?到時候機會多得是。”范星舒捋了捋折扇扇墜,誚諷地說。
寧梧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不屑地說:“要是懂規矩便罷,要是不懂規矩,我見一次打一次。”
范星舒大笑著走出月,幽幽地道:“有寧姑娘這般護著夫人,夫人真是好福氣。”
“他這話是啥意思?”
寧梧乜斜一眼郭林,抬手就是一掌甩在他肩膀上,“你登哨亭上玩兒去吧。”
晚夕和松針用晚膳,染沒有面,僅由侯卿塵和范星舒作陪。一頓飯一直持續到亥時初還未散席。
寧梧每隔上半個時辰,便進來跟染詳述一氣。染默然聽著,倒沒怎麼表態。
著上來困意的隋,要紫兒替他洗漱就寢。隋臨回屋前,口里還低低咕噥著詩文。
鄧媳婦兒立在一旁,笑說:“自從夫人讓大壯家的那倆兒子過來旁聽,咱們大就來了神,很怕自己落后,可有上進心了。”
“我不圖大有什麼作為,康健、識字、懂道理就好。”
染起走到明間里,過門往堂后花廳里瞧了瞧,里面的聲音斷斷續續。不擔心隋等人,反而替松針把汗。他落在這麼幾個人手里,能有什麼好果子吃?
大抵又過去二刻鐘,庭院里約傳來松針含糊不清地嚷,染方知他們把人給灌醉了。
隋進來時周酒氣,染用溫水絞了把臉帕遞給他,“侯爺還清醒麼?”
隋接過去認真臉,又不不慢地褪掉上外衫,“醉的人只有松針。”
“灌醉他有什麼目的?”
“是他自己非要喝,我們相勸不住,府里又不差他這點酒水,只好隨了他的意。”
Advertisement
“狡辯。”染坐在妝奩前拆開發髻,將那支鐵釵小心地擺放好,才躺回床榻上。
隋洗漱畢,跟著上了床榻。
他展開修長的軀,一臂枕在腦后,說:“東野沒得選,松針心里頭清楚。他只是在試探我的底兒,松針,準確地說是凌澈,他不相信咱們有那麼大的胃口。”
“咱們胃口確實不算大,照比那房家、夏家還差得遠。況且掙東野的錢是次要的,我們首選得穩住錦縣。總不能看著錦縣百姓肚子不管,反而把糧食賣給東野人。”
隋側臥過來,眈向染,說:“這點我當然明白,娘子,你也向我個底吧,咱們今年能收上來多糧食?”
“怎麼,讓我嚇唬一下,底氣馬上就不足啦?”染咯咯地笑起來。
隋大方承認道:“是啊,娘子了底,我出去才能量力放狠話嘛~”
“裝什麼裝?以為我不知道你翻過我的賬簿?”染翻過,用手肘撐起子,解頤道。
“按常理,咱家后面那一百多畝稻谷,加上靠海那六百多畝土豆,還有金生在外陸續收購的那些散戶,大抵能有多糧食,我心中有數。只不過……”
隋幽幽地湊到染面前,高的鼻子已到的翹鼻上,那雙細長的眼佻達地盯的瞳仁。
“但凡娘子經手的田地,長勢都會特別好。府后良田如此,府中藥草如此,連那靠海荒地都能在娘子手里起死回生。”
“你,你什麼意思?”
染連連向后閃躲,隋莫不會窺探到那隨空間的了吧?真是千防萬防家賊難防。
真想叉著腰,氣回道:“老娘不有空間靈泉,連我自己都是穿過來的,怎麼樣,害怕了吧?”
染也就是想想,隋的腦回路本就與眾不同,再把他給嚇傻了咋辦?雙好治,腦子卻不好治。可眼下該怎麼忽悠住他呢?
猜你喜歡
-
完結940 章

農門長嫂富甲天下
倒霉了一輩子,最終慘死的沈見晚一朝重生回到沈家一貧如洗的時候,眼看要斷頓,清河村的好事者都等著看沈家一窩老弱病殘過不了冬呢。 她一點都不慌,手握靈醫空間,和超級牛逼的兌換系統。 開荒,改良種子,種高產糧食,買田地,種藥材,做美食,發明她們大和朝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原打算歲月靜好的她一不小心就富甲天下了。 這還不算,空間里的兌換系統竟還能兌換上至修仙界的靈丹,下到未來時空的科技…… 沈見晚表示這樣子下去自己能上天。 這不好事者們等著等著,全村最窮,最破的沈家它竟突然就富了起來,而且還越來越顯赫。這事不對呀! ———— 沈見晚表示這輩子她一定彌補前世所有的遺憾,改變那些對她好的人的悲劇,至于那些算計她的讓他們悔不當初! 還有,那個他,那個把她撿回來養大最后又為她丟了性命的那個他,她今生必定不再錯過…… 但誰能告訴她,重生回來的前一天她才剛拒絕了他的親事怎么辦?要不干脆就不要臉了吧。 沈見晚故意停下等著后面的人撞上來:啊!沈戰哥哥,你又撞我心上了! 沈戰:嗯。 ———— 世間萬千,窮盡所有,他愿護阿晚一生平平安安,喜樂無憂。
181.6萬字8.33 135289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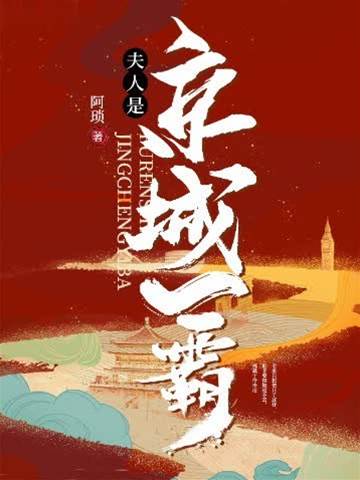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9 章

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宣威將軍嫡女慕時漪玉骨冰肌,傾城絕色,被譽為大燕國最嬌豔的牡丹花。 當年及笄禮上,驚鴻一瞥,令無數少年郎君為之折腰。 後下嫁輔國公世子,方晏儒為妻。 成婚三年,方晏儒從未踏進她房中半步。 卻從府外領回一女人,對外宣稱同窗遺孤,代為照拂。 慕時漪冷眼瞧著,漫不經心掏出婚前就準備好的和離書,丟給他。 「要嘛和離,要嘛你死。」「自己選。」方晏儒只覺荒謬:「離了我,你覺得如今還有世家郎君願聘你為正妻?」多年後,上元宮宴。 已經成為輔國公的方晏儒,跪在階前,看著坐在金殿最上方,頭戴皇后鳳冠,美艷不可方物的前妻。 她被萬人敬仰的天子捧在心尖,視若珍寶。
33.7萬字8.18 14518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80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