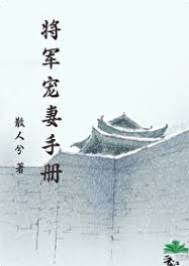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235回:不再茍且地活著
房門微頓,門外人停下腳步,顯然將染的話聽了去。
隋劍眉一立,聞聲去,卻見是范星舒挑簾走進來。他仿佛被染的那句話所及到,想要極力掩飾住自己心的震。
“侯爺,夫人,需要星舒做些什麼嗎?”范星舒躬行禮道。
“去踩一下苗刃齊的近況,看他會對眼下局勢有何措施。就勢去金生那邊瞧一眼,互市閉市,對桑梓米鋪的沖擊最大。我們和東野的易大抵要暫停。”隋有條不紊地吩咐下去。
染覺得很是,跟著說道:“邱家和房家那邊早準備好兩千石稻谷,因著以前咱們信譽良好,允咱們只付定金就可提貨。這回東野突發,糧食只怕要暫先擱置在手里了。”
“這種事誰也預判不到,屬下去去就回。”范星舒正說,須臾,旋走出建晟侯府。
隋再次和染對視,帶著幾分戲謔,道:“娘子猜一猜,范星舒當初究竟為什麼會被死?”
“他聽到‘宮’二字這麼敏,想來是跟元靖帝的死因有關。不過當下不是研究這個的時候,我還是去見下吳夫人吧,看們都是什麼態度。若不愿寬限時日,我這邊也好及早把銀子預備出來。”
“兩千石稻谷囤在我們手里不算難事,即便面對錦縣百姓零售也有銷路。娘子先前調教的好,金生和丁易可在外替咱們撐起整個產業。”
“你給我戴高帽子啊~”染上前,墊著腳將手臂挎在他的側頸上,仰頭含笑,“有東野那塊,咱們就是錦上添花。沒了東野也不要,大不了再尋出路。雒都那邊不是還沒靜呢?即便真對你起了殺心,我跟你浪跡天涯便是。”
Advertisement
隋攬著的腰肢往自己軀上,恨不得要把進自己的骨里。他低頭銜住的,吻得沒甚麼章法,只知道用悍勁兒,帶著讓人無法拒絕的驕霸。
染讓他親了個夠,弄得邊通紅一片。
“信我,這一次我再不會被打倒。”隋攢著頭,神凜然地道。
染頷首著,垂頸應是。
到隋那被制太久的東西就要迸發出來,他在等待那個“天時、地利、人和”的節點,到時候他將徹底撕掉偽裝,重新屹立在世人面前。
卻說范星舒過了后晌才回到侯府,眼下整個邊境集市里的商戶均到影響,桑梓米鋪亦沒法子避免。但由于邊境那邊防措施很牢固,暫還沒有流民逃錦縣境。
康鎮作迅速,在平常巡邏中就堵截過多死角,甚至連靠海荒地那邊的邊界上,都已派兵過去把守。不僅如此,連丁易手下的人都被征調過去做雜役。
苗刃齊那頭開始沒什麼反應,是到了快午時才派衙役出街,四巡防維穩。
錦縣上的百姓們鬧了幾次小規模哄搶,不知從哪兒聽到流言,說是那野夷要打過來了。衙役們連批評帶說教,總算把市面上慌的況了下去。
“金生讓我回來支會夫人,府外營生一切都好,他和丁易暫能應付過來。倒是擔心侯府安危,畢竟咱侯府后面就是大興山,去歲貢品丟失那事就是從后山開始鬧起來的。”范星舒一五一十地匯報。
他這邊正說著,水生又從屋外走進來,笑加加地道:“夫人,按您的意思,我們已去外面采購不東西回來,咱家不缺糧食,就補了點炭火和菜蔬,剩下雜七雜八的什暫都夠用。”
Advertisement
兩邊的大局勢是他們無法控制和預料的,但是侯府眾人的安危和這幾年辛苦積攢下來的底子不能到影響。染需守護好這些家當,待明年開春還得指著它們繼續變大變強呢!
隋站在霹靂堂庭院里,靜靜地向安睿手中的那只海東青。它被安睿養的膘壯,忽一展翅,型大的驚人。頃,海東青讓安睿放了出去,它向著雒都方向越飛越遠。
“侯爺放心吧,這只猛鷹聰明著呢,過不了多久就能飛到顧將軍府上。”安睿只有在談論起這些海東青時,臉上才會泛起笑意,話語才能多說幾句。
時隔甚久,隋再次向顧白發出信號。當初主切斷和顧白之間的聯系,是因為他們之間通信的海東青不明不白地死去,隋恐被暗藏在雒都部的有心人盯上。
隋不想讓顧白到自己牽連,他在暗地里為自己所做的事已經夠多的了。可如今他不得不重新開啟這條線,他需要在雒都里安一雙眼睛。尤其是梅若風的突然造訪,讓他知到,自己又被一力量重新拉回到當初那個圈子里。
東野現下正著,若真要與他們切割開,隋必須重新審視他和雒都之間的關系。
“看好這幾只猛鷹。”隋收回遠的視線,沉聲道。
郭林扶著長刀自外面回來,看見主子在此,忙上前叉手說:“侯爺,地上地下都檢查的差不多了,這回甭管是什麼東西都別想闖進來!”
隋扯了扯角,哂笑道:“最初是攔不住凌恬兒,之后是攔不住羅格,再之后是攔不住范星舒,最后連校事廠的番子也給放了進來。郭林啊,也就是夫人板著我的脾氣,不然你覺得我能饒過你麼?”
Advertisement
郭林不好意思地賠笑,狡辯道:“這不能比較,我手里這些家將都是臨時抱佛腳,您知道的,真正有本事的人當初都被您給解散了。”
“將熊熊一窩。”隋負手搖頭,諷道。
郭林也是跟隋太悉了,想都沒想,口就說:“哎,侯爺可是北黎的奉國大將軍,您熊,我們才熊!”
隋瞪起細長的眸,繃著線往外蹦字兒:“郭、林!”
郭林趕跳到一丈外,涎著臉皮道:“侯爺息怒,待大志他們帶老人兒回來,您就等著瞧好吧!保準讓侯府的戰斗力蹭蹭往上升。”
“你過來。”隋朝郭林勾了勾手指,道。
郭林一個勁兒搖頭,說:“屬下不敢,您這腳再不似從前。您康復那會兒天天被您摔打一百八十回,真是夠了。”他一面說,一面往外跑,口里直念叨:“我去廚房看看晚上吃什麼菜,聽水生說今兒出去買了。”
見郭林離開,安睿復叉手說:“要是侯爺手,屬下陪您練練。”
隋誹笑道:“我是想逮住他,狠狠教訓他一頓罷了。”
又過一日,侯卿塵還沒有從東野歸來,范星舒便陪同隋去了趟邊界。
隋沿著邊界線一路走到赤虎關,再從赤虎關去往駐地大營。二人甫一進來,便聞到陣陣米香。隋俯往將士們的碗中瞧了瞧,頓時心中一凜。
“侯爺給的、剿流寇得的,從苗刃齊那里榨出來的逐一見底。”康鎮的聲音兀地出現在后。
“軍心要穩,尤其是當下這個節骨眼。不要擔心糧食問題,就算雒都那邊撥不下來,我也不會讓你的兵著。”
聽到隋這樣說,康鎮的眼淚差點掉下來,他嗚咽道:“侯爺……”
Advertisement
“康鎮,這兩三萬軍士從今以后先姓‘康’再姓‘北黎’,他們是你的袍澤弟兄,讓他們吃這種飯,誰替你賣命,誰去擋住對面的野夷?”
周遭聽到他們對話地士兵們頓時肅然起敬,大家上不說什麼,心里卻像是被什麼鼓舞了一般,他們這些臭丘八終于被人當回事了。
在回侯府的路上,范星舒憂慮地問:“侯爺,幾萬軍士的糧食,咱們拿什麼填上?就是把夫人手里的錢全部拿出來也不夠用的啊!”
“以我的名義管錦縣上的大戶們去借,打建晟侯名頭的白條,既然東野靠不住,就利用他們最后一次。雒都下發的軍餉或許會遲到,但絕對不會不給。這個時候把康鎮急,他再反了,就是替東野打開北黎的東大門。”
“侯爺是打算借著這個機會徹底回歸世人視野?”
隋搔了搔坐下壯馬的馬耳,又瞥向旁邊的范星舒,玩味地道:“你不是一直都很期待麼?”
“侯爺,我……”范星舒一時語塞。
“梅若風該回到雒都了,想必劍璽帝也知道我的真實境況了。錦縣眾人就更不必說,原本以為拿住東野,還可以再撲騰一下。可惜,這回真沒時間了。”
對于隋帶回來的這個消息,染有點吃不消。不是擔心欠下大筆債務還不上,是覺得隋這次的賭注太大。
他想有個華麗的出場,對這幾年茍活在錦縣上有個代。至通過這個舉,能讓一方百姓念起建晟侯的好,而不是像當初來時那樣,引起那麼多人的不滿。
但經過一番掙扎,染還是同意了隋的決定。
既然不能坐以待斃,那就主出擊博一次!
“明天一早我就出府,替你一家一家地去借!”染義無反顧地道。
隋指在臉頰上挲兩下,疼惜地說:“傻姑娘,在外低三下四的活,你這些年已做的足夠多,這滋味該讓我一。”
染驀地紅了眼圈,原來他不是想有個華麗的出場,他心里仍把自己當北黎的將軍,他在以這種方式護住腳下的土地。
夜又深了,二人坐在暖閣火炕上,研究著明日出府的路線,先去誰的府上,再去誰的別院,染甚至能講出他們的一些格和癖好。
“侯爺,塵爺從東野回來了……”水生自門外稟報。
“快請他進來!”隋急忙穿下炕,還不小心帶翻了小炕桌上的燈燭。
“塵爺他不是一個人回來的。”水生的聲音越發不對勁兒。
染也著急忙慌地跟過來,水生那臉像死人一樣恐怖,他說:“塵爺把東野國主和小郡主一并帶回了侯府。”
帶翻的燈燭燃起一摞宣紙,小炕桌上的火苗瞬間四起。計劃永遠沒有變化快,誰都不知道下一瞬會發生什麼,這一次,到底是福還是禍呢?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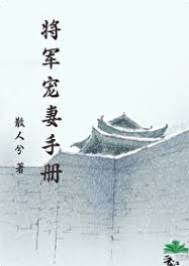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