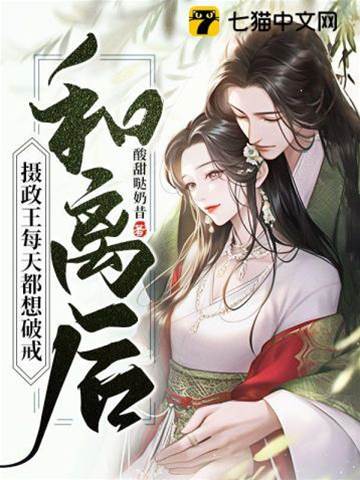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紅鸞記》 第一百三十章 反目
樓衍跟姜宴走在臨湖的步道上,鵝暖石鋪的蜿蜒小道不知通往何,一側的湖裏偶爾能見鴛鴦鳥兒在水裏嬉戲。
姜宴問他:「真的打算這樣嗎?」
「嗯。」
「可是小衍,我覺得我覺得我還沒準備好。」姜宴有些不安,經過這些事後,他越發的不確定他是否能勝任那個高不勝寒的位置。
樓衍在湖邊停下來,在這裏還能看到魏如意小臉通紅的跟張嬤嬤說著什麼,他目微微了些,就好像綠茵草地上飛下了一隻風箏,輕輕的,但極溫。
「太子不會聽勸的,一旦他折進去,你不拿這個位置,便是蕭王拿。蕭王拿下那個位置後會有什麼後果,不必我說你也知道。可若不是蕭王,就只剩下一個更加平庸的廉王。」
樓衍輕聲說著,目一直在那個穿著胭脂抹長的上。
姜宴掃了眼,不敢多看,只看著水裏的鴛鴦:「我知道了。」
他淡淡垂下眉眼,彷彿還記得當年爬牆看的樣子,一轉眼,已是別人的妻子了。
時間過的可真快。
魏如意察覺到有目在上,扭頭看了眼樓衍,與他四目相對后,臉紅到了耳朵,卻想到了解決辦法,笑著跟張嬤嬤道:「那帕子尊上知道在哪兒。」
「尊上……」
「是啊,他親自收起來的,我不記得放哪兒了,要不等我回頭問問他再給您?」魏如意笑道。
張嬤嬤聞言,這才點點頭,還叮囑道:「夫人,這帕子十分重要,您可千萬要找到。」
魏如意認真點頭,張嬤嬤這才依依不捨的走了。
魏如意長舒一口氣,不過想起昨晚……
「小姐,上鈎了,上鈎了!」
知雨忽然激的喊,魏如意這才發現魚竿了,忙讓人手忙腳的去拉魚竿,不過魚還沒拉上來,就跑了,惹得眾人一陣嘆息。
Advertisement
風吹過,枝葉晃了晃,細碎的把這一群人都照得格外明,沉靜的國師府也終於熱鬧了起來。
樓衍看了眼那樹上飄下的落葉,目微微抬起。深秋了,事拖了這許久,也該解決了。
接下來幾日,魏如意都沒能再如之前一般見到樓衍,他總是天不亮就出門,大半夜才回來,若不是魏如意每次迷迷糊糊覺有人抱著,都以為樓衍幾日未回呢,但這幾日的奔波,也很快有了回報。
「聽說皇上因此而當場吐暈過去了,現在事還沒傳開,但很快大街小巷都會談論起來,畢竟誰能想到所謂誤信人讒言,那人便是當初皇上最為倚重的雲丞相呢?而且今兒朝堂上,有子烈的史直接就開口罵了皇上,說他濫用臣,枉顧人命。」胡清微坐在一旁拿著新曬好的果仁咬了口才低聲道。
陳言袖的傷勢好了許多,坐在一旁,瞧見魏如意氣不錯,問胡清微:「這些事,誰告訴你的?」
胡清微小臉微微一紅,魏如意跟陳言袖會意的對視一眼,才笑道:「小姜公子可真是得閑,還有空與姐姐說這些。」
「是我偶然問起的,因為祖父一直擔心皇上的子,但他又從太醫院退了出來,只能我問問了。」胡清微忙解釋,但魏如意跟陳言袖都只是笑而不語。
說了會兒話,魏如意想留們二人用膳來著,但們都各自說府里有事,便離開了。
魏如意知道,言袖姐姐八是等著姜宴回去呢。
「小姐,看起來昭王妃和昭王殿下不錯。」知雨在一旁笑道。
「是啊。」魏如意說完,略有些落寞的坐了下來。如今小夭和大春都因為二春之事而被安排遠離開這些事了,想要知道外面的事,也不如之前那般方便了。
Advertisement
剛想著,木英便從外頭回來了。
「小姐,雪無痕已經照您的要求把人送去京兆府好幾日了,但一直沒靜。」木英過來道。
「正常,現在京城發生這些事,京兆尹就是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輕舉妄的。」魏如意挲著下,在屋子裏來回的走著。
「那……」
「去把這件事告訴牧雲。」魏如意忽然道。
木英不解:「您是打算借國師大人的勢力來下手?」
魏如意笑嘻嘻看:「我現在也是樓家的人,自然要用樓家的人,而且我還打算把京城這些鋪子都拿出來。」樓衍相扶太子登基,必然需要大筆的銀錢,他雖然收賄賂,可他收的錢大多都用在百姓上了,手裏能用的必然不多。
打定主意,魏如意立即就讓人去辦了,現在一點兒也不想耽擱把蕭王碎萬段!
下午,魏如意還在想著天兒漸漸冷了,該添幾件冬了,國師府忽然就湧了一群兵模樣的人來。
「魏如意在哪裏!」
來人大喝。
國師府的人各個都警惕起來,魏如意看著這群人居然就這樣進來了,有些驚訝,從屋子裏走出來后,看著領頭的護衛,只覺得很面生,看起來不像是常在府臉的人。
「何事?」
「皇上有令,你涉嫌謀殺親魏老夫人,現在我等就要緝拿你歸案!」說完,領頭的便要親自來抓魏如意,魏如意往後退了半步,牧雲這時候已經帶著人趕過來了。
他看到這進來的十幾人,立即問道:「你們是哪個府的?即是皇上之令,聖旨呢?」
「皇上乃是口諭,沒有聖旨。怎麼,國師府如今是連皇上口諭都不聽了嗎?要造反嗎?」男人輕喝,威嚴十足,看起來真是十分有底氣。
「沒有聖旨,我怎麼信你是皇上的人?」牧雲繼續道。
Advertisement
「金令在此,還有膽敢阻攔者,殺無赦!」說罷,那男人便拔出了刀來。
聽到『殺無赦』三個字,魏如意的心微微了一下,前世也是這三個字,然後國師府流河的。
「小姐,你別怕,有國師府的人在,奴婢看他們怎麼把您帶出去!」木英護著道。
但這句話卻似乎提醒了魏如意,恍然大悟般抬起頭看向牧云:「尊上現在在哪裏?」
牧雲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問,卻道:「皇上早上吐之後,應該留了尊上幾人在養心殿。」
「養心殿……」魏如意想著養心殿,皇帝有個習慣,那就是在養心殿說話時,不會留外人,甚至太監都不會多留,正是最好的可乘之機。而且皇帝也不會用這樣低劣的手段來抓自己的,如今要抓自己走的人,必然是為了使衍哥哥分心。
看著面前目錄兇的男人,稍稍往後退了一步,才冷聲道:「牧雲,抓住他。另外立即通知尊上,皇上可能有危險。」姜棣不希太子掌權,但皇帝如今都吐了,必要把權利給太子,所以他可能會不擇手段。
牧雲看到警惕起來的魏如意,眉心微微擰了下。
「牧雲,你愣著做什麼?」魏如意看他不,還奇怪的著自己,詫異問道,可下一秒,牧雲便七竅流的倒在了地上。
木英嚇了一跳,剛要運功,就覺得頭一暈,直接倒在了地上。
周圍的侍們也紛紛出腰間的劍,可不等手,就七竅流的倒在了地上。
知雨嚇得小臉慘白,卻愣生生的擋在魏如意前:「你們都是什麼人!」
「魏小姐跟我們走了,自然就知道了。」
為首的男人似乎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況,抬手將知雨打暈,直接朝魏如意抓來。
Advertisement
不過他唯一算的是,魏如意天生跑得快。
在他打暈知雨的瞬間,魏如意已經扭頭跑回了僅僅三步之遙的房間。
好門栓關好窗戶,捂著劇烈跳著的心,輕喚:「雪無痕?」
喚了幾遍,依舊沒靜。
想雪無痕也定是中招了,可是誰會讓他都中招呢?而且方才這些人用藥,居然一點察覺也沒有,這天底下除了用毒的莎慕家,還有誰有這樣的本事?
可莎慕家不會跟姜棣聯合的,那麼還有誰呢?
一腦袋的問號,但前頭已經有人在踹門了。
回頭看了看,乾脆躲到了浴室里,還特意打開了浴室外頭的窗戶。
外頭的人找進來時,直接就找到了窗邊,而後才聽那男人呵斥:「追,務必找到魏如意!」
「是,但萬一跑了怎麼辦?」有人問他,男人只冷哼一聲:「能跑一次,我就再抓一次。國師府我都能如此容易的進來,何況別的地方?」
魏如意的心狂跳著,是啊,按理說國師府應該是最固若金湯的地方,可為何這麼容易就被他們闖進來呢?
魏如意不解,不過張著張著,忽然想起昨夜睡到一半,衍哥哥好似低聲跟說了什麼。那時候因為太困了,聽得迷迷糊糊,只約記得要小心,還有方才牧雲那個一言難盡的眼神跟他帶來的量的護衛……
魏如意:「……」
該不會是衍哥哥引狼室吧,讓自己小心,是小心這些人嗎?
「沒找到,人應該還沒跑。」
有人來回稟,魏如意覺脖子一寒,好似被什麼冷的東西盯上了一般。
努力往這木架子後頭了,但那人影已經在慢慢靠近了,甚至魏如意還能聞到他上那腥氣。
完了。
魏如意出所有的葯在手心想出去一搏,可不等出去,便被人從後頭捂住了。
半刻之後,那群人便扛著一個麻布袋迅速從國師府撤離了。
此時的養心殿。
樓衍看著妄圖藉著給皇帝送葯之機下殺手的太監被抓住,看著太監看向自己時的震驚和不解,淡淡開口:「居然有人敢行刺皇上,可見平王妃一事被翻出來,幕後的確是有人縱。」
「縱?」皇帝的兩頰已經微微凹陷了下去,看著樓衍,冷笑:「那卿說說,是誰在縱,目的又是什麼?」
「縱之人臣不清楚,但皇上若是想知道也很簡單,演一齣戲即可。」樓衍道。
一側姜宴默默看了他一眼,沒出聲。
皇帝看向他,目冷:「演戲?」
「是。」
高公公站在養心殿的門口,看著疾步過來的蕭王,淺笑行禮:「殿下,皇上正在裏頭見昭王和國師呢。」
「本王有要事稟報。」姜棣掃了眼裏頭,十分的鎮定,似乎有什麼事盡在掌握一般。
「可是……」
「公公只管去回稟就是,是要事!」姜棣又道。這次他的計劃絕對是萬無一失,樓衍千算萬算,也絕對算不到自己這一步。
就在高公公遲疑之間,殿忽然傳來驚呼聲。
高公公嚇了一跳,立即朝裏頭問:「皇上,您可還好?」
裏面沒有聲音。
高公公還在遲疑要不要推門,姜棣卻似乎料到會有此一遭般,上前便推開了殿門。
大門打開,腥氣也隨之飄來。
樓衍面冷肅的站在一旁,而姜宴手執長劍,已經斬殺了一個手拿匕首的小太監,至於皇帝,則面慘白的捂著帶的口臥在床邊,眼中滿是憤怒。
「父皇——!」
姜棣快步走過來,外頭的護衛也隨之而來,高公公也立即去傳太醫了。
他看了眼拿劍的姜宴,皺皺眉,立即道:「父皇,您可還好?」
「皇兒。」皇帝勉強出這一句,姜棣看他氣數將盡的樣子,忙跪在地上,道:「父皇,都怪兒臣來遲一步。兒臣方才便已經查到有人要行刺了,非但如此,他還擄走了國師夫人打算來要挾國師及如今掌握京城護衛大權的陳家。若是父皇放任不管,那我朝危矣。」
「是誰?」
皇帝目深沉的著他。
姜棣似難以啟齒一般,看了眼站在一側同樣眉頭深鎖的樓衍,道:「是太子皇兄。」
皇帝滿目失,躺在床邊,深深看著他:「你確定是他?他沒有道理這麼做,朕已經給了他想要的一切,他不會這麼做的。」
姜棣跪在地上磕著頭:「兒臣不敢撒謊,若是父皇不信,可查查這個小太監,他上必定有太子皇兄給他的信,否則他一個小太監怎麼敢對您手?」
皇帝看了眼樓衍,沒出聲。
姜宴會意,上前人翻找了一番,果真是翻出一塊小小的玉章來,這是太子府每人都有的東西。
姜棣見東西順利找了出來,繼續道:「這幾日自從凌家的事被翻開開始,太子的緒就一直十分低落,想必父皇也知道其中原因。當初太子能為了平王妃而出家,後來他又再次出山,為了什麼,想必父皇比兒臣更清楚。」
「那你……希朕怎麼罰他?」皇帝問向姜棣。
姜棣微微一愣,皇帝怎麼會這樣問?
他抬起頭來,看著一旁的的確確死去的小太監,再看皇帝捂心口的樣子,眉心微擰。
這時候,太醫已經過來了。
太醫手忙腳的要替皇帝把脈,皇帝只抬手將他打發了下去。
高公公還想起勸勸:「皇上,先讓太醫看看……」
「朕沒事。」皇帝冷淡說完,鬆開手,眾人這才看清,他的心口衫雖然有,可裳卻半點沒破。
姜棣反應過來,他這是被人給算計了。
「父皇,您沒事?太好了,嚇壞兒臣了。」姜棣到了邊想提議死太子的話又咽了回去。
「是嗎?」
「是,兒臣如今已經連失幾位親人,實在不想父皇您再出事了。只是太子,他可能只是一時糊塗,既然父皇如今沒事,兒臣願意代太子過,還請父皇不要責備太子。」姜棣道。
皇帝角泛起冷意:「代他過?」
他輕哼一聲未置可否,姜棣只咬住了牙關。
樓衍掃了眼姜宴,皇帝沒有繼續套姜棣的話,是想給他留一條活路吧。
說來姜棣也是幸運,若不是在他之前已經死了三位皇子,端看皇帝如今一副恨不得吃了他的樣子,也斷然不會容他。
「朕沒事,都退下吧。」皇帝沉沉道。
樓衍抬手行禮,皇帝卻沒理他,只看了眼姜宴:「宴兒留下。」
姜宴早知道會是如此,行禮應下。
姜棣跟樓衍一塊兒出來,人還有點沒回過神。他沒想到這幾日他苦心收集證據,並且心思縝的推斷出太子今日可能會為了平王妃一家而直接手,而且為了萬無一失,他甚至用了一直埋伏在父皇邊的眼線,沒想到,居然這麼輕易就被樓衍設下一局。
「國師大人真是好本事,能讓父皇都陪你演這齣戲。」姜棣邊走邊笑。不過幸好他已經做好了失敗的準備。
樓衍沒理他,只看著前方甬道中站著的人,似乎是等了他許久了。
他緩步上前,行了禮:「殿下不是說今日不得空過來嗎?」
「本宮若是不過來,怎麼會知道國師大人竟然對父皇這樣忠心耿耿呢?」太子著他,笑容漸漸涼薄。
他要父皇生不如死,才能償還嫻兒這麼多年被他囚所帶來的痛苦,才能償還自己信任被背叛的痛楚!
可偏偏,樓衍知道了他的計劃后,竟阻止了它!
猜你喜歡
-
完結986 章

農門有喜無良夫君俏媳婦
東臨九公主天人之姿,才華驚艷,年僅十歲,盛名遠揚,東臨帝後視若珠寶,甚有傳位之意。東臨太子深感危機,趁著其十歲壽辰,逼宮造反弒君奪位。帝女臨危受命,帶先帝遺詔跟玉璽獨身逃亡,不料昏迷後被人販子以二兩價格賣給洛家當童養媳。聽聞她那位不曾謀麵的夫君,長得是兇神惡煞,可止小孩夜啼。本想卷鋪蓋逃路,誰知半路殺出個冷閻王說是她的相公,天天將她困在身旁,美其名曰,培養夫妻感情。很久以後,村中童謠這樣唱月雲兮哭唧唧,洛郎纔是小公舉。小農妻不可欺,夫婦二人永結心。
173.1萬字8.18 37020 -
完結237 章
重生后王妃咸魚了
沈妝兒前世得嫁當朝七皇子朱謙,朱謙英華內斂,氣度威赫,為京城姑娘的夢中郎君,沈妝兒一顆心撲在他身上,整日戰戰兢兢討好,小心翼翼伺候。不成想,朱謙忍辱負重娶出身小門小戶的她,只為避開鋒芒,韜光養晦,待一朝登基,便處心積慮將心愛的青梅竹馬接入皇宮為貴妃。沈妝兒熬得油盡燈枯死去。一朝睜眼,重生回來,她恰恰將朱謙的心尖尖青梅竹馬給“推”下看臺,朱謙一怒之下,禁了她的足。沈妝
37.5萬字8 18649 -
完結91 章
念卿卿(重生)
別名:攬嬌 梁知舟一生沉浮,越過尸山血海,最后大仇得報成了一手遮天的國公爺。人人敬著他,人人又畏懼他,搜羅大批美人送入國公府,卻無一人被留下。都說他冷心冷情不知情愛,卻沒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漫長的夜里,是如何肖想自己弟弟的夫人,如癡如狂,無法自拔。他最后…
32.2萬字8 2844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80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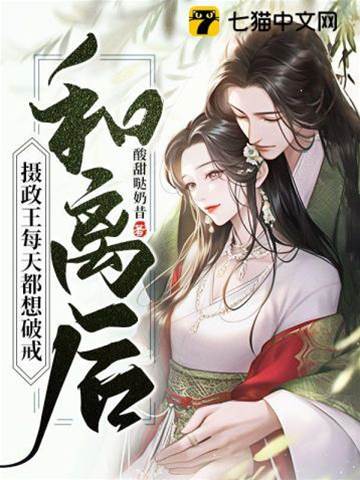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