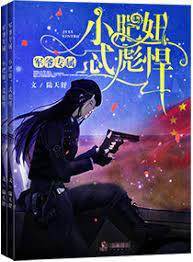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我的紈絝相公》 第二百零五章 三人聯盟
文丞相想吐又捨不得吐的時候,打殺了一晚上的姚羽然沉沉地睡去了,而在姚羽然上的趙恆之卻睜開了眼睛,試探喚了一聲,「親親娘子?」
「嗯?」
趙恆之一驚,正要笑著胡說幾句搪塞過去就見姚羽然抱著自己的手狂啃,啪嘰啪嘰地一口接一口,忽然皺眉委屈道:「怎麼吃不到啊?」話落又啃開了,吃不到就繼續啃,總會吃到的!
瞥了眼被口水糊了的手臂,趙恆之無言以對,隨手扯了搟麵杖強行塞到姚羽然手上,著角哄道:「親親娘子,啃這個,老香了。」說著看了眼姚羽然的大白牙,暗自點頭,牙口看著不錯,說不定真啃得。
至於廚房的搟麵杖為何會在此,是因為這搟麵杖其實是之前躲在犄角旮旯里畫圈圈詛咒敵人的趙恆之的金箍棒,可惜沒派上用場就帶回來了。
不得不說,睡夢中的姚羽然好哄得很,抱著搟麵杖啃得嘖嘖有聲也不覺得疼,趙恆之這就放心了,但又生怕姚羽然一個用力過猛將搟麵杖磕得坑坑窪窪的,這不是影響搟麵嗎?於是他心道:「親親娘子,小心點啃,不然一會子就啃沒了。哎對,輕點,這就對了。」
鬆了一口氣的趙恆之看了眼不亦樂乎且出猥瑣笑意的姚羽然一笑,屈指彈了彈的額頭,見皺眉,趕收回手,卻又不甘心地上小巧地耳朵,正打算趁敵人失守討回一二利息時,心頭忽然不忍,只了兩下見得去蹭了蹭被子就不再逗弄了,利落起往外去。
深更半夜,月朗星稀,清風徐徐,請問我們的趙大人是要去香竊玉嗎?當然不是,趙大人對趙夫人之心天地可鑒,日月可表,雖然這樣尷尬的時間地點不想是要去辦正事兒,但趙大人確實是要去辦正事,還是有生以來讓他腰板聽得最直的正事兒。
Advertisement
在某間廂房,趙大人停下了腳步,猶豫著是該敲門呢還是該喊人?可好像怎麼樣都會吵到別人?還沒想出個章程的趙大人鬼使神差地湊到門上瞧,只是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心裏正憾沒能見著冷人酣睡圖時,門悄無聲息地打開了,白散發,一雙清冷的眸子盯著他直瞧,一陣風吹過。白與黑髮翻飛,眼神又冷得不像話,活像夜半索魂的——阿飄!
趙恆之不自覺咽了口水才遲鈍地要大喊「鬼啊!」
當然,我們楚樓主功夫之高強,惜閨譽之謹慎,半點沒給趙恆之鬧大的機會,一手捂住趙恆之的,一手拎著趙恆之往屋去,右腳一帶屋門悄無聲息地關上了。
趙恆之被隨手扔在地上,對上楚樓主「你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的眼神時,停頓了片刻,抱著自己瘦削的軀躲進了角落,雙眼警惕地看
著楚簫,活像正要被惡主欺負的奴才。
楚樓主的額角跳了跳,決定先發制人,冷著臉問道:「你想幹什麼?」一個正兒八經的男人夜半三更看另一個鋼鐵直男的香閨,咳,廂房,這企圖不言而喻。而且,眼前被葉君君小多了的男人,真的還是個正兒八經的男人嗎?
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君君者腐,鋼鐵直男楚簫在葉君君的潛移默化中,腦袋裏不知不覺多了「腐」這一類的思維。
「我、我哪有幹什麼?」趙恆之了子,那意思太明顯了,分明是你不由分說地將我拎進廂房的,不該是我問你你要幹什麼?我們夜探香閨的趙大人選擇地忘記他窺一事。
楚簫無語天,為直男,還是個武藝高強的直男,他覺得既然不能好好說話打一頓就好了,於是化大灰狼的楚簫逐步向瑟瑟發抖的小白兔趙大人,獰笑一下,正了拳頭要砸時,趙大人忽然沒事兒一樣地起了,邊拍上的塵土便往桌邊走,也不顧楚簫茫然的神一屁坐下,自顧自地幹了一杯水后開口道:「天兒不早了,別浪費時間,快過來,我有事與你說。」
Advertisement
楚簫過破舊的窗扇看了眼當空皓月,心道,確實不早了。想著走到趙恆之的對面坐下,卻覺得有點不對勁,憑什麼浪費時間的了他?
趙恆之卻沒給他反擊的機會,直了腰板,目清亮而堅定地盯著楚簫看,認真道:「我想明白了,我願意幫你們。」話落覺著說的不明白,又道:「幫你們對付文知理那個老賊。」
看著彷彿換了個人的趙恆之,楚簫並未吃驚、詫異或覺得驚嚇,因著他正想著,趙恆之也不一定是嘛,也可以攻的,就像這樣,軀雖瘦弱,可這樣的眼神讓人覺得,趙恆之是堅不可摧的,再攻不過了。
一心想干大事的趙恆之可不知道冠楚楚的楚樓主心烏七八糟的想法,反而盡地展開自己三寸不爛之舌的功力,表達了他對姚羽然至死不渝的,願為弱窩囊的,也願為而出的,雖然該是個聽者聞者皆落淚的人至深的古代故事,簡稱「為而戰」,但神遊天外的楚簫一無所覺,而彷彿憑空出現的慕乘風神複雜難辨。
而在慕乘風出現的那一刻,趙恆之目瞪口呆地住了,緩了片刻后看看裳隨意的楚簫,又看看貌似冠整齊的慕乘風,憤憤不平地出手指向二人,「你,你們,你們對得起小君君,對得起傾悅公主嗎?!」
這樣的誤會……慕乘風和楚簫已經免疫了,慕乘風淡定地開口道:「趙大人,不早了,你說你願意幫我們對付文知理,可是真的?」青竹失手,慕乘風正愁沒法子接近趙侯爺套話,
今日他本是來找楚簫商議的,沒想到瞌睡遇著枕頭,趙恆之主找上門了。
他先是質疑,趙恆之的骨頭他算是見識了個徹底,甚至懷疑莫非是趙侯爺已經心思縝到懷疑上楚簫才讓趙恆之打敵人部探聽消息,但聽見趙恆之「為而戰」的宣言后,他選擇相信他,而歸結底,他是相信姚羽然的眼,否則郎無妾無意的聯姻也不可能逐步修正果。
Advertisement
其實,趙恆之沒來之前,他就是想從趙恆之下手,但始終過不了心裏那關,他不想一次又一次地對不起姚羽然,可仇深似海,他沒得選,而不管走不走出這一步,他的心都是煎熬的。幸好,趙恆之開竅了,他心的愧疚也可以些。
震驚之下的趙恆之並未忘了今夜的使命,只是「我們」二字又膈應了他一下,卻是不再糾纏,點頭道:「我又不是傻的,總不能老等著他來殺吧?兔子急了還要人呢。」說著彎腰就要鞋,卻是忽然頓住,納悶道:「你跟那狗賊有仇?」
慕乘風一頓,心輕嘆一聲,他到底是急躁了,否則怎會一時大意輕易曝在人前?可仇深似海,他真的忍不了了。這時候,他想起的還是姚羽然,以及日後可能會實施的計劃,他直言不諱道:「有仇,不是他死,就是他亡。」
繼續鞋子的趙恆之深以為然地贊同道:「那狗命咱們定下了。」話落從鞋底的階層取出了味道不可名狀的——春宮圖,隨意仍在桌上后又繼續另一隻鞋子。
楚簫與慕乘風齊齊掃了一眼默默散發著味的春宮圖,表一時間難以名狀,楚簫一人卷手輕咳了一聲,慕乘風則移開了眼打量著簡陋破舊的屋子。
「還有這個。」趙恆之將一封被摧殘地不樣子的書信扔在地上,看了眼各行其是的二人奇怪道:「你們怎麼不看?」說著沒半點尷尬地翻開春宮圖,「快瞧,這上面可有好東西。」
楚簫與慕乘風表示懷疑,堅持不低頭看向春宮圖,只神嚴肅地看著趙恆之。
趙恆之可不管,直接拎起春宮圖湊向二人眼前,一本正經地解釋道:「好好瞧瞧,這上頭的人名兒可都是文知理的爪牙,雖然只是小嘍啰,但聊勝於無不是?」自然讓二人接住春宮圖,他又拆開書通道:「你們再看看這是什麼。」
Advertisement
二人的視線隨趙恆之的話移,只一瞬間,二人面巨變,似喜似悲,似惱似嘲,再看向趙恆之的目複雜難辨。
趙恆之坦地對上二人的視線,解釋道:「這是在王連兩家搜出來的,我甚至事關重大不敢輕易出去,沒想到今日竟用上了。」略作一頓,看向慕乘風,「我敢拿出來,是因為我相信羽然,而且,方才我也從你眼中看出了刻骨的恨,
我相信你是真的想報仇。」
慕乘風沉默了,在相信姚羽然這一件事上,他與趙恆之殊途同歸。
「這些東西……趙夫人知道?」
趙恆之理所當然地點頭,卻是道:「自打來米縣,就沒閑過,大約是暫時忘了這東西,保不齊什麼時候就想起了,反正是要給你們的,早給晚給都是給,我樂意做個好人。總是,東西給你們了,怎麼利用你們看著辦,有什麼本大人能幫得上的也儘管開口。」
「趙大人,在下有個不之請,請大人做回貪如何?」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2261 章

影視世界當神探
陸恪重生了,還重生到了美國。但他漸漸發現,這個美國并不是上一世的那個美國。 這里有著影視世界里的超凡能力和人物,他要如何在這個力量體系極其可怕的世界存活下去? 幸好,他還有一個金手指——神探系統。 一切,從當個小警探開始……
416.5萬字8.18 46115 -
完結358 章

嫡女無雙:惹火棄妃太搶手
手握大權卻被狗男女逼得魚死網破跳了樓。 可這一跳卻沒死,一眨眼,成了草包嫡女。 不僅如此,還被自己的丈夫嫌棄,小妾欺負,白蓮花妹妹算計。 你嫌棄我,我還看不上你;你欺負我,我便十倍還你;白蓮花?演戲我也會。 復雜的男女關系,本小姐實在沒有興趣。 和離書一封,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 原以為脫離了渣男是海闊天空,可怎麼這位皇叔就是不放過她? 說好的棄妃無人要,怎麼她就成了搶手貨了?
81.3萬字8.09 94242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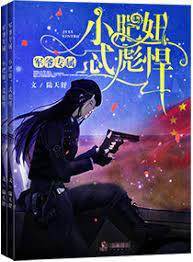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
完結529 章
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一朝穿越,慕容輕舞成了慕容大將軍府不受寵的癡傻丑顏二小姐,更是天子御筆親點的太子妃!略施小計退掉婚約,接著就被冷酷王爺給盯上了,還說什麼要她以身相許來報恩。咱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躲躲藏藏之間,竟將一顆心賠了進去,直到生命消亡之際,方才真切感悟。靈魂不滅,她重回及笄之年,驚艷歸來。陰謀、詭計一樣都不能少,素手芊芊撥亂風云,定要讓那些歹人親嘗惡果!世人說她惡毒,說她妖嬈,說她禍國?既然禍國,那不如禍它個地覆天翻!
89.6萬字8 47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