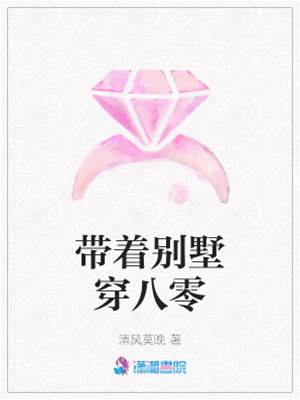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杳杳歸霽》 第14章 奶鹽
港區之旅結束, 回到京市后,蘇稚杳覺自己又被關進了一個巨大的牢籠里。
年前最后幾天的行程和宴請煩不勝煩, 周圍人的笑臉虛虛實實, 眼前來去的每個人,都戴著偽善討好的假面,像鬼魅, 游戈在這座燈火迷離的城市間。
蘇稚杳有些煩了。
為什麼賀司嶼不能和他們一樣呢?
怎麼, 難道全世界就他一個男人不把放在眼里嗎?
真氣人。
蘇稚杳的祖父已逝多年,祖母是個頗為傳統的人,事事嚴照祖訓和禮俗辦,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國,除夕夜,所有親族都要回到老宅團聚。
上流社會沒什麼年味, 所有人都太世故,之所以不遠萬里也要回來吃這頓團圓飯, 不過都在惦記著老太太名下不菲的資產。
老宅在京市遠郊, 蘇老太太在那兒有個莊園,那天下午臨去前,蘇稚杳在房間里發了個微信。
蘇稚杳:【孟教授新年快樂, 好久沒去滬城,我媽媽還好嗎?】
孟禹:【新年快樂, 杳杳】
孟禹:【你媽媽很不錯, 別擔心】
蘇稚杳:【謝謝孟教授,年后我過去一趟】
孟禹:【沒問題,我這幾天出差, 初九回國, 別跑空了】
“杳杳, 可以出發了哦。”楊姨溫地敲了敲的房門。
蘇稚杳放下手機:“來了。”
一下樓,就看到客廳沙發,蘇柏在聽蘇漫聊公司項目,邊還有溫竹音依著喂車厘子的畫面。
“好不容易過年得閑,你們父倆也真是,公司的事兒就放放吧。”溫竹音嗔道。
蘇漫聽話地說:“行,聽媽的。”
溫竹音挽住蘇柏的胳膊:“老柏,漫給你母親準備了顆野山參,兩百多年呢,早半年前就開始找人搜羅了,說是市面上就這麼一顆。”
Advertisement
“嗯。”蘇柏吐出車厘子核:“回頭帶上,漫自己拿去給你。”
溫竹音給蘇漫遞去一個眼神。
“好。”蘇漫笑了下。
溫竹音出并不好,能和蘇柏再婚,除了有同窗的緣分,也是自己聰明。
聰明的人貪心得都很有分寸。
溫竹音見好就收,輕聲岔開話題,發出疑:“時間差不多了,小杳服還沒換好嗎?”
問完這句時,蘇稚杳剛從旋轉樓梯走到底,一聲不響經過客廳。
溫竹音轉瞬變了語氣,笑著說:“老柏你看,小杳穿這款大比模特上還漂亮,是不是?”
蘇柏沒回答,只是確認的服足夠暖和后,站起:“杳杳,這幾天住你那兒,要帶的東西別忘了。”
楊叔和楊姨是夫妻,平時真心待蘇稚杳很好,蘇稚杳不想因為自己,誤了這對老夫妻的年夜飯,所以沒有讓楊叔單獨送。
其實蘇稚杳知道父親指的是帶自己的東西,可一想到要和繼母繼姐坐一輛車,心里更不舒服,忍不住任嗆話:“我哪有姐姐這份心思,能有什麼帶的。”
蘇稚杳沒留下聽蘇柏教育,話落,徑直去了停車庫。
抵達老宅時天將暗未暗,青林綠池環繞的蘇氏莊園卻早已燈火通明,佇立中,像一座巧奪天工的四合院式古典園林。
新中式宴廳華貴氣派,水晶吊燈像發的瀑布,傭人們來回穿梭,忙碌地布置餐品。
那些叔伯姑嬸們言笑晏晏,站的坐的都有,平常一年到頭不見人,這會兒倒是團團圍著老太太有說有笑,殷勤得很。
蘇柏一到就領著他們過去打招呼。
蘇稚杳興致缺缺,慢吞吞跟在后面,在看到程覺的那瞬間,一愣,神終于有了反應。
Advertisement
“杳杳!”程覺喜悅地喊。
他一白正裝,靠坐在老太太旁的沙發扶手上,似乎和老人家聊得很融洽。
這邊,溫竹音暗暗搡著蘇漫遞出禮盒,蘇漫拜年的話剛出口,蘇老太太恍若不聞,一看見蘇稚杳,立馬笑逐開地招招手。
“囡囡,快過來,到這兒來。”
蘇稚杳來不及思索程覺為什麼會在這里,人先走過去:“新年好。”
蘇老太太握住蘇稚杳的手,不掩飾喜,拉坐到自己邊,態度對比強烈,直接忽略了蘇漫的存在。
蘇漫尷尬地收回捧出禮盒的手。
“可許久沒見你了,以后要和阿覺常來啊。”聊了會兒,蘇老太太說道。
蘇稚杳聽得奇怪。
還沒開口,程覺已經懂事地搶先回答:“蘇您放心,我一定一有空就帶杳杳回來看您!”
蘇老太太笑幾聲,又連說了幾聲“好”。
蘇稚杳嫌程覺多管閑事,悄悄瞪他一眼,然后認真說道:“,我自己也能來,不用麻煩小程總。”
“誒,”蘇老太太不同意這說法:“你和阿覺的親事,很滿意,囡囡啊,歲數大了,就想長眠前看到你家。”
確實上了年紀,說幾句話就有氣無力。
蘇稚杳卻頓時到索然無味。
祖母是個慈祥的老人,作為流,年輕時手商戰也不乏雷霆手段,很人尊敬,喜歡聰明的孩子,從小到大最疼蘇稚杳是真的,但和蘇柏一樣,名聲地位看得重,萬事以家族利益為先也是事實。
蘇稚杳有點累,不想說話。
蘇老太太拍拍手,言簡意深的語氣:“可就你這麼一個親孫。”
這話說得,讓蘇漫是安靜站在那里都顯得如此難堪。
Advertisement
擅做面子的溫竹音臉也變得不太好看。
溫竹音在蘇家妯娌里一直不待見,這下老太太的意思也很明白,就沒把們這對上趕著倒的母當過自家人。
一室人都在默默看笑話。
蘇柏出來做和事佬,接過蘇漫手里的禮盒,擺到茶幾上:“母親,漫給您的野山參,這可是個好東西啊,補氣!”
“這玩意兒多得放不下,我都不知道扔多了。”蘇老太太一眼沒瞧,拄著拐杖站起來:“吃飯吃飯,囡囡,阿覺,來跟一塊兒坐。”
蘇稚杳可不想和程覺一塊兒坐。
尤其一場家宴,老太太全程都在思量訂婚的日子,說四月份日子好,就是太趕了,七八月份不錯,再晚就是今年年底……其他長輩都跟著應和,特別是程覺,春風得意的緒都浮現在臉上。
蘇稚杳心煩意,敷衍地吃了幾口,就一副困得不行的樣子,蘇老太太偏心,獨獨放先回房間休息。
離席時經過,一個不經意的瞬間,蘇稚杳和長桌那一頭的蘇漫遙遙對視了眼。
前后只有一秒。
但很奇怪,當時蘇漫那個的眼神,有妒忌,有冷意,有屈辱,依稀還有幾分看不懂的嘲弄和忍不甘,十分復雜。
就好像是在怨恨奪走了本該屬于的東西,可這里的一切本就不是的。
莊園大得像城堡,房間眾多,蘇稚杳被安排在三樓,住蘇柏隔壁,這層的臺風景好,也清靜。
蘇稚杳沐浴后就裹著睡袍上了床。
客套不如睡覺,不打算再出去了。
程覺的微信消息彈進手機:【乖乖,快出來,我放煙花給你看!】
今晚的郁悶,程覺要負一半責任。
蘇稚杳沒好氣問:【大老遠跑這兒來,你想干什麼?】
Advertisement
程覺還冤:【這可就冤枉我了,你一定要我過來,我也不好拒絕是不是】
蘇稚杳和他直白說明:【婚姻是我自己的事,他們怎麼說都不作數,程覺,你知道我不會和你訂婚】
程覺難得正經:【杳杳,我知道你現在呢還不想結婚,但我保證,你嫁給我之后,會一直是京圈最風的公主,我對你是認真的】
他好像是認定了,就是他的,而只有他一個選擇。
可是喜歡和互相喜歡,是兩碼事啊。
蘇稚杳無語,臉著枕頭往里陷。
深刻到自己再不勾搭上某人,別說解約,人都要直接被架著送去給程家了。
與其困縛在豺狼虎豹窩里被一點點啃噬,寧愿被最烈的猛鷙叼走,起碼見過長空,死也死得明白。
蘇稚杳倏地坐起,深吸口氣,利索地翻進那個人的短信界面。
賀司嶼的名字,此刻就像救世主。
【新年快樂,歲歲安康】
敲出這條短信后,蘇稚杳安詳平躺等待,可半小時過去也沒收到回復,今晚心甚是煩躁,耐心耗盡得極快。
坐起來,編輯新短信:【國貿新開的日式餐廳,聽說主廚是從日本請過來的米其林三星大師,等你下回來京市,我們一起去吃吧[可]】
過去會兒沒回應。
蘇稚杳沒話找話:【我的珍珠還在你那兒呢】
又過去半小時。
他是在忙還是故意已讀不回?
蘇稚杳再坐起,這回來勢洶洶:【賀司嶼,上回請我喝咖啡的五百塊,你忘了給我報銷】
【支持微信轉賬】
【我的微信和手機同號,你快點兒加我】
雖然那天沒去喝咖啡,但這不重要,主要是想加他微信。
沒一會兒,嘀一聲,收到了短信回復。
蘇稚杳笑起來,眼睛亮晶晶,不愧是資本家,一提到錢馬上就有靜。
點進去一看,笑容隨之消失。
這人就寡淡一句:【我沒有微信】
拒絕的理由都找得這麼敷衍。
蘇稚杳微惱,一口氣敲了好多個問號甩過去,每個問號都拆分一條短信,頗有不死不休的氣勢。
或許是吵得不可開,賀司嶼不得不及時回復:【開會,別鬧】
除夕夜還開會……難道他人在國外。
蘇稚杳忽覺自己此刻的行為不太通達理,安分下來,不自覺地揣起他說“別鬧”這兩個字時的語氣。
是不耐煩的,還是溫的?
肯定是不耐煩,他每次對都那麼冷淡。
蘇稚杳著被子躺回去,子蜷起來,郁悒回:【哦……】
甚至連想象都想不出賀司嶼溫會是什麼樣,想著想著,還不小心睡了過去。
再醒來是在一陣哭鬧聲中。
聲音是從隔壁房間的臺傳來的,隔著玻璃門若有若無,但蘇稚杳還是被吵醒了。
大約今晚上溫竹音委屈了,父親在哄。
不過很快就沒了聲。
這里是蘇家老宅,眼皮子底下,七八房親眷的耳朵都聽著,溫竹音有再大的怨艾都得裝裝樣子,不敢鬧大。
蘇稚杳沒在意,只是又想到蘇漫那個眼神,心緒莫名有點不安。
手機落在枕頭邊,蘇稚杳過來想看看自己睡了多久,先看到了賀司嶼的短信。
時間是在半小時前,他問:【銀行卡號】
蘇稚杳呆滯住,才從惺忪睡意中慢慢清醒過來,這人還當真想要還錢了。
五百塊在這圈子里都抵不到五分,蘇稚杳不信賀司嶼看不出真正的目的,除非他就是真心實意地準備和兩清。
腔里一子不明不白的別扭。
良久不知作何反應,蘇稚杳直接回撥了通電話過去。
沒有等太久,對面接通了。
他好像在看書,電話里有窸窣的翻頁聲,混著信號雜音的還有他沉靜的呼吸。
明明就在,他卻不開口。
他不先開口,蘇稚杳也不開口,秉住氣暗暗和他較勁。
過了十幾秒,賀司嶼大概是覺得稚,不和相持,低沉出聲。
“說話。”
手機在耳畔,男人的聲音一出來,蘇稚杳耳窩一,手指頭跟著麻了下。
他的嗓音是有厚度的,帶著鼻息間淡淡而慵懶的氣音,沒什麼語氣,但滿男人的質和魄力,聽得人多胺涌。
蘇稚杳滾進被子里掩住半張臉,側躺著,沒坐起來,聽聲音就浮想不已。
如果哪天生氣了,他用這樣的聲音溫一點哄哄的話,再氣可能也堅持不到兩分鐘就原諒了。
蘇稚杳突然忘了自己剛剛在不舒服什麼。
“嗯……嗯?”裝傻,拿出畢生演技,剛睡醒一般,迷迷糊糊問:“賀司嶼?”
賀司嶼不作聲。
蘇稚杳沒管他,自顧往下演,著聲說:“我玩兒手機,玩睡著了,按錯號碼了……”
賀司嶼不明意味淡呵一聲,語調不不慢:“你的手指得多有本事,連著區號十三位數,偏就一路撥到我這來了。”
“……”
這理由是餿的。
蘇稚杳知道自己不占理,支支吾吾思索須臾,強辨道:“彈鋼琴的手,你以為呢?盲撥號碼而已,要是在港區saria輔導過我,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三協奏曲,我今天肯定都能閉著眼倒彈。”
這話聽著,好像是在控訴他。
也不管是對是錯,總能找到自己的理,細細的聲兒一出來,就自然而然帶上幾分可憐,嗔怨他不與人為善,讓這麼委屈。
賀司嶼聲音放輕:“這是在怪我?”
一想到催婚都催到了定日子的地步,而在與賀司嶼的往方面始終毫無進展,蘇稚杳就熬心,半怨半悶地咕噥:“賀先生現在過意不去了?”
都開始喚他先生了。
就好像前陣子費盡心思想讓他名字的人不是。
接著,聽細細沉:“欠一餐和欠兩餐,其實也差不多……”
又算計他。
賀司嶼停頓好些秒,才回應:“欠不欠的,不都是憑你說。”
他語調平淡,卻沒從前那麼冷。
心抑郁的時候,中會產生某些破壞的毒素,像化學質,造態度的悲觀。
如同此刻,蘇稚杳聽到他這麼說,腦子里獲取到的信息不是“說了算”,而是“都是生拉扯胡攪蠻纏”。
蘇稚杳小聲埋怨起他:“還不是你天天沒空沒空的,諸葛亮都沒你難約。”
賀司嶼被惹得很淡地笑了聲,但語氣依舊冷靜:“蘇小姐為何非要約我?”
“我追著你這麼久,你都不知道為什麼?”一陣難言的沮喪堵在心間,蘇稚杳一把扯著被子過頭頂,整個人都窩到里面。
“為什麼?”他問。
蘇稚杳憋了好一會兒,才悶聲悶氣地說:“想要和你朋友啊……”
賀司嶼靠著休閑椅,一本厚重的《圣經》擱在上,國還是正午,書房落地窗外灑進一室明的晴,他左耳戴著一只藍牙耳機,不知是在認真看書更多,還是聽電話里的閑言碎語更多。
——鐘意你,想和你朋友,不可以嗎?
這話說過。
言猶在耳。
這部被稱為上帝語言的《圣經》,羊皮質書封墨綠燙金,書頁殘缺泛黃,里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損,明顯已經很老舊了,他卻還留著。
甚至從書皮到頁,有塊塊斑駁的深褐臟污,約是拉丁文上曾濺過一片,沉淀多年后留下的痕跡,有種鬼祟的神。
賀司嶼垂著眼,翻過一頁,不急著回應。
他目凝落在書頁,眼里是麻麻的拉丁文,腦中想的卻是,這姑娘還真有趣。
周圍的人要麼想方設法對付他,要麼倉皇從他邊逃離,汨汨長河中,卻像下游一朵頂著浪濤想要逆流而上的水花。
很難不惹眼。
當了某一種唯一,的機再不純,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賀司嶼拇指慢悠悠挲尾戒,口吻晦暗不明,聲音很低:“確定是我麼?”
蘇稚杳沒聽清:“什麼?”
賀司嶼結微微一。
他太久沒講話,蘇稚杳在電話里他:“賀司嶼……賀司嶼?”
的聲音是很輕的,像在棉花糖,會有些撒的味道,他名字的時候也是。
賀司嶼沒應,多聽了自己幾聲。
“人呢……是國外信號不好嗎?”對面的孩子開始碎碎念,發起牢,仔細聽有細碎的雜音,然后是砰砰聲,應該是拽開被子坐起來,敲了兩下手機。
賀司嶼無聲勾了下角。
“怎麼知道我在國外?”他終于淡淡出了聲。
蘇稚杳沒懷疑,以為信號總算通順了。
“我不知道,但你肯定不在京市。”頗有些頑俏,輕笑說:“因為今天京市沒有下雪。”
京市一到雪天,他們總能見到。
“唯心主義不可取。”他說。
“就不能是浪漫主義嗎?”嘀咕:“要是唯心的話,我就該說是我沒用法把你召喚出來了。”
賀司嶼邊的弧度不經意間泛深了點。
金燦的日跳躍在他黑的睫,墻壁上掛鐘的指針在悠哉轉,嘀嗒嘀嗒聲中,他突兀察覺到自己在笑。
一刻意留心,就不自然了。
賀司嶼有意識地將抿直線,緩緩合上書,聲音也沉了些:“好了,我還有其他事。”
蘇稚杳懂事且知趣,不想打擾他辦正事,所以非常配合:“喔,那我掛了,新年快樂。”
“……嗯。”
就要掛斷前,蘇稚杳又住他,小心翼翼地試探問:“那我們現在……是朋友了嗎?”
電話那邊安靜許久。
才聽見他沉著嗓子,意味深長地反問:“哪種朋友?”
猜你喜歡
-
完結1497 章

天才雙寶:傲嬌前妻抱回家
一場意外,她懷了陌生人的孩子,生下天才雙胞胎。為了養娃,她和神秘總裁協議結婚,卻從沒見過對方。五年後,總裁通知她離婚,一見麵她發現,這個老公和自家寶寶驚人的相似。雙胞胎寶寶扯住總裁大人的衣袖:這位先生,我們懷疑你是我們爹地,麻煩你去做個親子鑒定?
267.8萬字8 65089 -
完結100 章
萌妻迷糊︰第一暖男老公
他陰沉著臉,眼里一片冰冷,但是聲音卻出其的興奮︰“小東西,既然你覺得我惡心,那我就惡心你一輩子。下個月,我們準時舉行婚禮,你不準逃!” “你等著吧!我死也不會嫁給你的。”她冷冷的看著他。 他愛她,想要她。為了得到她,他不惜一切。 兩年前,他吻了她。因為她年紀小,他給她兩年自由。 兩年後,他霸道回歸,強行娶她,霸道寵她。
8.9萬字8 2666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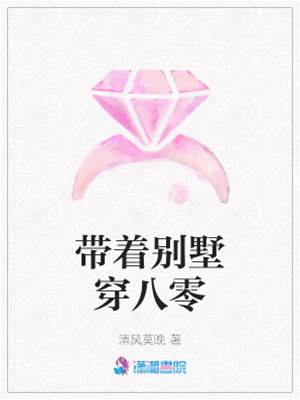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32 章

辣妻致富1990
身價千億的餐飲、地產巨亨顧語桐,訂婚當天被未婚夫刺殺! 再次醒來的她,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了生活在1990年的原主身上! 原主竟然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住進了貧民窟? 還在外面勾搭一個老流氓? 滿地雞毛讓她眉頭緊皺,但她顧語桐豈會就此沉淪! 一邊拳打老流氓,一邊發家致富。 但當她想要離開傻子的時候。 卻發現, 這個傻子好像不對勁。在
61.2萬字8 14929 -
完結921 章

一胎三寶:夫人又又又帥炸了
被設計陷害入獄,蘇溪若成為過街老鼠。監獄毀容產子,繼妹頂替她的身份成為豪門未婚妻。為了母親孩子一忍再忍,對方卻得寸進尺。蘇溪若忍無可忍,握拳發誓,再忍她就是個孫子!于是所有人都以為曾經這位跌落地獄的蘇小姐會更加墮落的時候,隔天卻發現各界大佬紛紛圍著她卑躬屈膝。而傳說中那位陸爺手舉鍋鏟將蘇溪若逼入廚房:“老婆,什麼時候跟我回家?”
229.5萬字8 73055 -
連載342 章

從摸魚開始成為學霸
【校園學霸+輕松日常+幽默搞笑】“你們看看陳驍昕,學習成績那麼優異,上課還如此的認真,那些成績不好又不認真聽課的,你們不覺得臉紅嗎?”臺上的老師一臉恨鐵不成鋼地
83.3萬字8.18 41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