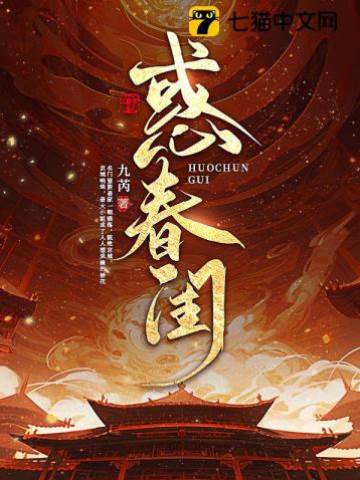《花嬌》 第22章 第 22 章
熾烈的秋潑進乾坤殿, 綿長的線里翻騰著細微的塵粒。
大殿外聚了不人,謝紜陪坐在太上皇側, 大夫人方氏也被傳了來, 太上皇念著是兒親家,沒讓跪,給安置在一把錦杌。方氏憂心地看著舒筠。
舒筠跪在乾坤殿的正中, 手心掐出一把冷汗,喃喃地說不出話來,不懼被太上皇懲罰, 懼的是與皇帝的事被人知曉,屆時不宮也得宮去了。
王君明白舒筠的顧慮,稍一思忖,便決定將事往自己上攬,提著擺徑直往太上皇跟前一跪, 含著委屈的腔調,
“外祖父忘了嗎?昨個兒上午扎營用午膳時,君兒給您請安, 您親口答應讓君兒住琉安宮, 于是君兒便住了進去....”
太上皇聽得一頭霧水, “我昨個兒答應你了?”他怎麼不記得有這事?
王君反而理直氣壯, “若非您開口, 給君兒一萬個膽子也不敢擅闖琉安宮呀?”
太上皇扶著額, “這話倒是。”
謝紜卻不信這套說辭,指著舒筠, “那呢, 怎麼進去的?”
王君眨眨眼, 又看了一眼太上皇, “我一人無聊,便央求外祖父答應我捎帶一人,我便帶上了筠妹妹。”
王君與謝紜也算是老對手了,王君說的話,謝紜一個字都不信,怕是掂量著太上皇記不好,故意瞞天過海呢,
“昨夜我在湖邊散步消食,聽到一聲突兀的尖,極像君外甥,君兒啊,你當真是奉旨進去,還是溜進去的?”
王君聽得那聲“君兒”,起了一皮疙瘩,平日里謝紜仗著自己輩分高,每每遇見王君這些晚輩,總頤指氣使,擺長輩的譜兒,王君看格外不順眼,
Advertisement
也毫不客氣回過去,“一聲夜鶯也能安在我上?我昨個兒在琉安宮還聽得有人在底下與將軍大呼小呢,一聽便知是謝姑娘的好嗓子。”
“我看你是故意嫁禍我,嫉妒我比你外祖父寵,故而一清早折騰這麼一出,哎喲,外祖父,今日天清氣朗,您不去狩獵嗎?”
這話踩了太上皇的痛,他也嫌謝紜無事生非。
謝紜臉愈發難看,昨夜聽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王君的聲音,不可能出錯,直覺告訴,事不是這麼簡單,想了想,與太上皇建議道,
“舅舅,泡個溫湯本不是多大的事,可若王君假傳圣旨,便是欺君大罪,您不可不治,以外甥來看,您不妨將將軍請來對證?”
林是皇帝的人,誰的面子都不會給,他不會偏袒王君。
謝紜這一嚷嚷,不公主王孫借口請安來旁觀,若不弄個清楚明白,上皇也沒法代,畢竟晚輩太多了,若每一個都像王君這麼鬧,豈不了套。
于是上皇派人去傳林。
王君和舒筠相視一眼,均是心下擂鼓,王君昨夜剛得罪了林,也不知林會不會幫,林倒是不至于坑害舒筠,怕就怕在林為了皇帝抱得人歸,徑直承認是皇帝的旨意,那就糟糕了。
舒筠臉白的厲害,王君稍稍往后挪了挪膝蓋,握住了的手,“別怕。”
謝紜瞧二人這做賊心虛的模樣,越發相信自己的判斷。
林本在獵區排查患,聽得侍衛傳喚,立即趕來乾坤殿,侍衛路上已告訴他殿形,他行至殿門口,取下佩刀,大步,眼神稍稍一抬,便看到王君苦地著他,林裝作沒看到的,任憑王君把眼睛眨瞎,他也沒什麼表。
Advertisement
王君眼拋給了瞎子,氣得口發脹。
林來到太上皇跟前,不待太上皇問便開了口,
“回稟太上皇,昨夜著實有手令從乾坤殿出,待臣戍衛琉安宮,護衛兩位姑娘安全。”
林這話說得模棱兩可,乾坤殿的指令可以是太上皇發出,也可以是皇帝發出,而眾人并不知皇帝昨夜駕臨行宮,故而只能是太上皇。
“有嗎?”太上皇這下是真的對自己的記產生了搖。
林面不改,“臣豈敢欺君罔上?”
“沒錯的。”王君與林一唱一和,猜到必是皇帝有了待,心中底氣十足,面上越發裝得委屈,鼻子一一搭,
“外祖父,君兒一向乖巧,豈敢撒謊,說來,這還是外祖父頭一回許諾君兒呢。”
林見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得格外,生怕淚沫子沾到自個兒上,連忙挪得離遠了些。
這廝演戲的水準爐火純青。
有了林作證,太上皇再懷疑也不能夠了,畢竟林沒有撒謊的理由,他老人家了額,也沒太把這樁事放在心上,“吧,事到此為止,既然朕許了君兒,君兒今日又了委屈,就繼續住著。”
王君破涕為笑,當即謝恩。
謝紜自是十分不服氣。
林收膝站起,冷冰冰看了謝紜一眼,轉而朝上皇拱手,
“上皇,王姑娘與舒姑娘的事是澄清了,但謝姑娘搬弄是非,混淆視聽,壞您聲譽,影響秋獵大典,此事不可不究。”
謝紜聞言唰的一下站起,然變,“林,本郡主與你無冤無仇,不過是昨夜...”看了一眼上皇也不好將昨夜闖琉安宮的事抖出,只得轉了話鋒,“沒錯,是我誤會了君與舒家妹妹,這也不是多大的事吧?”
Advertisement
林沒有看,太上皇也沒有看。
太上皇只盯了林幾眼,林的子太上皇了解,絕不可能摻和到姑娘家的爭執里,他突然開口要治謝紜,很蹊蹺,不過蹊蹺歸蹊蹺,林既然開了口,太上皇必須懲治。
于是他老人家下令,“著謝紜閉門思過。”
謝紜正待委屈辯駁,
林忽然靠近太上皇,悄悄耳語幾句,也不知他說了什麼,太上皇臉明顯凝重,旋即改了口風,
“著嬤嬤掌摑二十下,再閉門思過。”
謝紜差點氣昏過去。
誰也不明白為何林非要逮著治謝紜,大約是這位謝大小姐得罪了軍中第一刺頭。
謝紜被當眾打得鼻青臉腫,再也沒臉出門,為禍京中多年,第一回吃了這麼大虧,也算大快人心。
事塵埃落定后,舒筠與林道謝,王君念著林今日替出了口惡氣,決定不計較他昨晚的失禮,隨舒筠一道追他至丹樨,朝他施禮,“多謝將軍相救。”
林淡淡看著,吐出兩字,“不必,”隨后看了一眼靦腆溫的舒筠,朝王君皮笑不笑道,“若不是舒姑娘,我可不管你死活。”
王君欽佩的心頓時見鬼了,木著一張臉咬牙切齒睨著他,“林,你真是不知好歹!”
林懶得理會,朝舒筠拱了拱手,快步回了林子。
王君從沒這麼丟臉,惱得狠狠跺了幾下腳。
舒筠在一旁安道,“好啦,今日天氣不錯,我陪你去騎馬?”
王君想起舒筠讓教騎馬的事,深吸了一口氣,又往林的背影扔了一記眼刀子,方攬著舒筠回了琉安宮,一想到能名正言順待在琉安宮,王君的心便妙了,二人早早用了些午膳,出門時,撞上舒家遣人來尋舒筠,舒筠只得讓王君先過去,帶著芍藥來到西苑。
Advertisement
舒筠到了西苑,瞧見父親舒瀾風急得在廳來回踱步,舒瀾風不知里,只責怪舒筠,
“你待會便把東西收拾好搬回西苑,那琉安宮豈是咱們能住的地兒?你瞧,今日差點惹上風波,君雖是好意,但規矩不可破。”
舒筠看著滿臉風霜的父親,心口的委屈差點要溢出來,哪里愿意去住那勞什子琉安宮,若不是皇帝,今日也不用這麼大驚嚇,今日謝紜的跋扈可見一斑,當真與謝紜共侍一夫,怕是不知道怎麼死的,可惜滿腔的苦水只能往肚子吞,舒筠不敢告訴父親,只吶聲點頭,
“兒知道了,只是君尚在馬場等兒,待晚邊回來,兒再搬如何?”
舒瀾風見兒眼眶泛紅,淚水要落不落,只當嚇壞了,心疼至極,“不哭,怪爹爹語氣不好嚇著了你。”
舒筠怕父親擔心,了眼角的淚,“我沒事了爹爹,您去忙吧。”
舒瀾風著實還有很多公務,吩咐芍藥照顧好舒筠便離開了。
主仆二人稍事休整,至午時正邁出行宮。
還未繞至前方的草原,便已聞得縱馬林的喧聲,大雁南飛,馬鳴鹿啾,一條狹長的水泊從東面山林蜿蜒而出,橫貫草原又延至西邊的深林。
快下丹樨,芍藥忽然想起還未捎帶水囊,又急急趕回琉安宮,舒筠迎風而立,向獵場,蒼蔥蘢,群山環繞,四周一片蓊郁之,那些鮮怒馬的年與姑娘,則了蒼茫山里的點綴。
東西兩面的林子便可狩獵,口各有一個馬棚,里頭拴著不高頭大馬,遠遠的瞧見王君在西邊林子口挑選馬匹,舒筠慢悠悠去尋。
草原甚為寬闊,眼瞅著沒多遠,走起來卻十分費勁。
大晉民風開放,男大防雖有,卻也沒過分苛刻,譬如未婚的男便是可一道出游,舒筠踏上綿的草坡,便見長姐舒靈與柳侯家的世子柳鳴晨站在不遠。
柳鳴晨個子并不高,只比長姐高半個頭,可他神極為溫,見長姐發梢沾了一片薄葉,便不著痕跡替摘去了,長姐那麼端重的一個人,在他面前也出了靦腆溫的神。
二人不知說了幾句什麼,一道往前方林子里去,柳鳴晨見長姐手里提著個水囊,主接了過來,長姐寬袖垂下,柳鳴晨空出挨著長姐那只手,舒筠清晰地看到二人的手指借著寬袖遮掩悄悄了。
放眼去,草原雙對,有年輕的丈夫扶著妻子上馬,相攜縱山野,有母親牽著年的孩在草原上嬉戲,哪怕是上了些年紀的老爺,也背著手領著妻子有說有笑往皇帳方向踱去。
舒筠不由自主浮現幾分艷羨,多麼有煙火氣的畫面啊,可惜不能屬于。
也不知這一生要怎麼辦?
即便能功說服皇帝放棄,那還敢嫁人嗎?不敢,男人嘛對得不到的總會惦記著,若嫁人生子,哪一日帝王不高興了,便要逮著發作,不會也不敢去連累旁人。
離開京城遠赴他鄉茍且生,爹爹一生的抱負便葬送在手里了。
明明很是熾熱,上卻沒由來的發冷。
遠的王君發現了,朝揮手,舒筠暫且下酸楚的念頭快步朝奔去。
這時一道暗含沙啞的嗓音喚住了,
“筠妹妹。”
舒筠猛地止住腳步,慢慢轉過眸來,
將將半個多月未見,裴彥生仿佛換了個人,他形容消瘦,下顎布滿胡渣,眼眶略深陷下去,一雙眸早沒了往日的神采,滿含苦著舒筠。
面朝舒筠那張臉后,裴彥生干裂的搐了下,換了個稱呼,“舒姑娘....”
舒筠看著這樣的他,心里堵得慌。
原先嫌裴彥生做事不過腦子,眼下才知道,裴彥生也不是能肖想的。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此地是皇帝耳目,舒筠更不敢與他談,事已定局,不如狠心些才好,舒筠一字未言,轉跑開了。
后的裴彥生也沒有追來。
舒筠一口氣跑到王君邊,王君也看到了裴彥生,見他還盯著舒筠在瞧,嘖了一聲,將舒筠拉扯至馬棚旁邊的圍欄,隔絕了裴彥生的視線。
“你沒有發現裴彥生不對勁嗎?”
舒筠茫然著,“什麼意思?”
王君手攬著的肩,臉一言難盡,“前段時日裴彥生大打擊,在家里不吃不喝,臨川王妃給他下了一劑猛藥,”
舒筠睜大眼,面疑。
王君湊近耳邊道,“王妃給兒子吃了那種藥,將自己的外甥送他屋子,二人春宵一度,如今兩家已開始議親,大約年底便要迎過來。”
舒筠吃了一驚,心底犯上一惡心,神怔怔說不出話來。
半晌,烏眸轉,語氣低落,“也好,至不再被我耽擱。”
王君又往裴彥生的方向了,見他不知何時離開了,這才將舒筠拉出來,
“行了行了,事都過去了,你也別難過,說句心里話,即便沒有舅舅,你們倆也長久不了。”
“淮王妃只是心高氣傲,行事還算要面子,臨川王妃連這種事都做得出來,不喜歡你,指不定怎麼折騰你。”
“好了,不聊這些,咱們騎馬吧?”
王君替舒筠挑了一匹矮瘦的馬,舒筠謹小慎微地坐上去,勒著韁繩不敢,王君自個兒騎湛,卻不怎麼會教學生,兩位姑娘折騰片刻,只在原地打轉。
王君有些泄氣,舒筠也被折騰得氣吁吁。
恰在這時,林從林子里巡防出來,撞上兩位姑娘倚在馬棚形容沮喪,便多看了一眼,王君瞧見他便一肚子火,將臉別開。
林卻是扶著腰刀大步走過來,
“兩位姑娘這是作甚?”
舒筠起朝他施禮,“將軍。”
林避開不的禮。
王君見他主搭腔,也不好裝作沒聽到,冷冰冰道,“筠妹妹不會騎馬,我正在教。”
林刮了刮臉腮,瞅了一眼舒筠,語氣還是那般吊兒郎當,“學騎馬是吧?”
王君有些不了他這副模樣,沒吭聲。
舒筠指了指那匹矮馬,“將軍,這馬兒我騎上去怎麼都不肯,將軍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林笑了笑,“本將雖會騎馬,卻不會教人騎馬,不過,我可以請個會教的來!”
王君心里想這樣最好,也不想看林的臭臉,不過林肯幫忙,也沒表現得過于明顯,“那多謝了。”
林二話不說便離開了,走到丹樨前,招來一侍衛,吩咐幾句,那侍衛快馬加鞭離開了。
王君等了一會兒不見人來,也沒太放在心上,舒筠怕攪了的興致,便道,
“你帶著我騎,我坐在你后便是。”
王君的父親也是軍中老將,家里兄長給挑了一匹玉驄馬,這次狩獵自然牽了來,先翻上馬,再將舒筠拉上來,舒筠抱著腰,任憑馳騁。
王君擔心舒筠害怕,也不敢騎得太快,二人騎了大約半個時辰,行至一片高坡,此地視野極為寬闊,待馬速慢下來,舒筠這才從王君后睜開眼,雙眼倏地一亮。
猜你喜歡
-
完結2204 章

退親後,我嫁給了渣男他叔
九皇叔,他們說我醜得驚天動地配不上你。 揍他! 九皇叔,他們說我行為粗魯不懂禮儀還食量驚人。 吃他家大米了嗎? 九皇叔,她們羨慕我妒忌我還想殺了我。 九王爺一怒為紅顏:本王的女人,誰敢動! ——一不小心入了九皇叔懷,不想,從此開掛,攀上人生巔峰!
326.9萬字8.18 116114 -
完結1946 章

農女雙雙的種田悠閒生活
老穆家人人欺負的傻子穆雙雙,突然有一天變了個樣!人不傻了,被人欺負也懂得還手了,潑在她身上的臟水,一點點的被還了回去。曾經有名的傻女人,突然變靈光了,變好看了,變有錢了,身邊還多了個人人羨慕的好相公,從此過上了悠閒自在的好日子!
341萬字8 118440 -
完結115 章

和清冷權臣共夢,嬌嬌臉紅心跳
【甜寵 雙潔】薑四姑娘年幼便喪失雙親,常年躲在薑家的內宅裏從未見過人,及笄後還傳出相貌醜陋膽小如鼠的名聲,引得未婚夫來退親。隻是退親那天,來的並不是她未婚夫,而是未婚夫的小叔,更是她夜夜入夢的男人。薑芙有個秘密,從及笄後她每晚就夢到一個男人,那男人清冷淩厲,一雙鐵掌掐住她的腰,似要將她揉進懷裏......後來未婚夫退親,京城眾人譏諷於她,也是這個男人將她寵上天。---蕭荊性子清冷寡欲,年紀輕輕就掌管金吾衛,是京城貴女心中的最佳夫婿,隻是無人能近其身,更不知蕭荊早就心折夢中神女。夢裏乖順嬌媚的小姑娘,現實中極怕他,每每見了他都要躲開。可她越是怕,他就越想欺負她。“你夜夜夢到我,還想嫁給旁人?”又名:春/夢對象是未婚夫小叔
20.9萬字8.23 33958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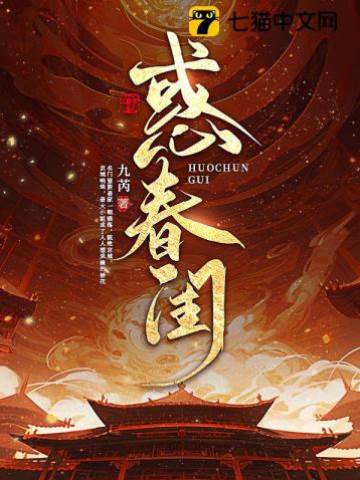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