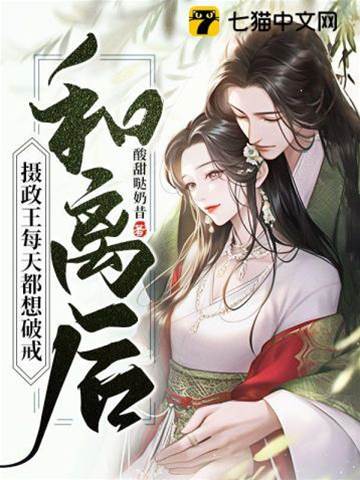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悍妃從商記》 第二百九十九章 君王多疑
驍王府。
“王妃,有濟世醫館的消息。”貝兒向花清錦稟報道。
花清錦目一抬,“說。”
“濟世醫館的掌柜昨日被人急匆匆的接到了文遠侯府,消息被人封鎖,不過如此興師眾的,多半是侯爺的出了問題。”
花清錦瞇了瞇眼睛,“都說濟世醫館的掌柜不懼權貴,怎麼文遠侯府的事他倒是上起心了?”
貝兒低了聲音說道,“王妃,您先前讓貝兒查平王府,果然不出您所料。”
花清錦輕輕勾了勾角,仿佛早就知道了這個結果一般,“真的是?”
“王妃英明。”貝兒垂首答道,“天底下沒有誰是真的查不到的。”
花清錦站起來,緩聲說道,“當初文遠侯開口,幫易親王府和平王府度過危機,如今花想容親自將文遠侯救回來,倒也算是還了恩。”
“只是不知道,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聯系。”花清錦眉眼低垂,聲音清冷。
“貝兒有一事不明。”貝兒沉默了片刻后有些猶豫的說道,似是并不確定自己要說的話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你說吧。”花清錦掃了一眼,開口說道。
貝兒這才開口,“貝兒不明白,文遠侯病了就病了,為何定要鎖消息?”
文遠侯雖然是朝中大員份特殊,但生老病死都是人之常,生病著實沒什麼好鎖消息的。
“你說得對。”花清錦抬眼,目中閃著詭譎的亮,“文遠侯的病沒那麼簡單……或許他本就不是生病。”
貝兒一驚。
“文遠侯的獨子于書文并不是個不的廢,聽說他前些日子回了府中安心做。”花清錦沉道,“如此看來……鎖消息就該是他的手筆了。”
Advertisement
“王妃您的意思是,于公子發現自家父親病得蹊蹺,因此沒有張揚?”貝兒開口道。
花清錦輕輕點了點頭,“病的蹊蹺……多半是中了什麼毒吧。”
說到這里,花清錦的角輕輕勾起,歪了歪頭,意味深長的說道,“花想容留在文遠侯府中,是想要查清此事吧。”
貝兒尚在吃驚中沒有緩過神來,“怎麼有人敢給文遠侯下毒?”
花清錦轉過來,目灼灼,“我問你,天底下有這個膽子的人多麼?”
貝兒想都不想就搖頭答道,“怎麼可能會多。”
花清錦點了點頭,接著問道,“那就算有這個膽子,有本事將毒帶進文遠侯府的又有幾個人呢?”
貝兒不明白自家王妃為何這麼問,垂下頭去道,“貝兒愚鈍,不明白王妃意中所指。”
花清錦冷笑一聲,“我是說……下毒的人,恐怕就是當朝皇上。”
貝兒大吃一驚,整個人向后退了幾步才穩住形,尚且不怎麼接文遠侯被人下毒的事,就又得知了個更加驚人的猜測。
皇上給重臣下毒,這樣的事若是昭告天下,天威何存?朝中的忠臣良將豈不是都要心寒?
“怎……怎麼會?”貝兒咬著下說道。
“皇上對他并不放心。”花清錦聲音清冷,仿佛一個沒有的殺手,“就像當初對柳家那樣。”
并沒有將扳倒柳家的功勞全都攬在自己的上,并不是一個狂傲自大的人,知道當初自己的一點心里算計只是垮了皇上心中對柳芙毓的最后一點信任而已。
“天家……天家無。”貝兒整個人都有些發抖。
Advertisement
天家無,無論你為這個朝堂立下了怎樣的汗馬功勞,無論你為這片天下的安定費盡了多心,無論你居怎樣的高位,都抵不過皇上說一句朕不再信你了。
只要皇上不信,你就要死,無論通過怎樣的方式。
“的確。”花清錦倒沒有因為此事有毫的心寒,在的心中,世事原本就該是這樣的,“不過皇上在這個時候發難,對我們有不的益。”
貝兒這才從驚慌中回過神來,像自家王妃一樣細細思量己方的形勢。
“花想容留在文遠侯府是要查清真相的,可天底下最不想讓真相公之于眾的人……是皇上。”花清錦負手立于窗邊,意味深長的說道。
貝兒恍然大悟。
花想容正在做的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費勁周章查出真相,最終得罪的人會是最得罪不起的皇上,可若是無功而返,平王府與文遠侯府之間的關系,恐怕就會變得有些微妙了。
對于此時正和東宮相持不下的驍王府來說,沒有什麼是比這還好的消息了。
“吩咐藏在東宮中的人,手吧。”花清錦一字一頓的說道。
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是絕不會輕易放過的。
“貝兒明白。”貝兒行了一禮,轉退了下去。
東宮。
“太子殿下。”侍衛單膝跪于褚辰景的面前,開口稟報道,“那邊……似乎打算手了。”
花清錦安排的人的一舉一早已被褚辰景看在眼中,今日那人收到了驍王府的消息,目的自然顯而易見。
“驍王妃為人聰明縝,也算是不世出的奇子,可惜啊,到底被皇后娘娘催的沉不住氣了。”褚辰景不慨道。
Advertisement
以他對花清錦的了解,花清錦不會在這種有患的時候手,那能解釋決定的唯一理由,就只能是皇后娘娘一刻都不聽的催促了。
“可要屬下現在就將抓來?”侍衛冷聲問道,他容不得這東宮之中有人危害太子的安全。
“急什麼。”褚辰景的聲音中很是輕松,“既然知道了他要手,接下來就該想想……怎麼把事鬧大。”
侍衛一怔,一時不解其意。
“過幾日請父皇過來一趟。”褚辰景拖長了聲音說道,“一定要過幾日,不給那人充足的準備時間可不行。”
侍衛猛的抬眼,“殿下英明,屬下明白了。”
侍衛退下后,褚辰景著大殿門前侍衛逐漸遠去的背影,角緩緩的流出一意味深長的笑意。
說起來他和花清錦之間也算是有些緣分,怎麼說也是曾經結過婚約的人,不想如今竟走到了這一步,當真是世事難料。
他忽然覺得有些后悔,若是當初他順理章的娶花清錦進門,如今的形勢恐怕就不會有這麼復雜了,他和花清錦兩人若是聯手,誰都沒法從他們的計劃中。
可惜,自己當初答應了那個人提出來的,莫名其妙的要求。
褚辰景的心緒忽然間飄到了花想容的上,一時間只覺得恍如隔世。
濟世醫館已經被他查了個清清楚楚,外界傳言中的容掌柜的確如他所想,正是醫舉世無雙的花想容。
當初他們的曾經談天說地,他說他對政局紛爭毫無興趣,一心只想經商賺錢,做一個舉世無雙的商人。
花想容說想開設一家醫館,這樣每逢瘟疫發之時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命喪黃泉了。
Advertisement
過了這麼久,他的初心早已改變,政局如今已經是他半步都不想讓的棋盤,而花想容當真還如當初一樣,一心一意的開起了的醫館,懸壺濟世。
人啊,終究是要選一條路走下去的,不是每個曾經親近的人最終都會走向同樣的終點。
褚辰景嘆了一口氣,將飄飛出去不知多遠的心思收了回來,他還有很多事要做,現在不是多愁善的時候。
文遠侯府。
花想容將文遠侯的飲食仔仔細細的排查了一遍,得出的結果令脊背發涼。
寧愿相信是疏忽了沒有抓住蛛馬跡,也不愿意相信真相真的如同現在所看到的這般。
如果文遠侯府的下人真的都沒有問題,那有問題的那個人……就真的是皇上了。
花想容將桌上的紙張打,讓它們如同自己的心緒一般作一團。
于書文猜對了,的確沒有什麼人做的到謀害文遠侯的事,除了當朝皇上。
其實花想容可以理解皇上為何下手,只是不愿意輕易接罷了。
“你怎麼了?”這時,于書文推門進屋,正看到了花想容愁眉苦臉的模樣。
花想容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于書文走近看了看的桌案,頓時明白了幾分,面沉了下去,“我說對了,是麼?”
事到如今花想容也不能再否認什麼,只是面發白,啞聲說道,“是。”
于書文冷笑了一聲,“過河拆橋,這就是皇上做出來的好事!”
文遠侯居高位自然不是空來風,他雖然晚年時不怎麼參與朝堂紛爭,但年輕時也算是肱骨之臣,當年的皇上能夠順利即位,文遠侯也是出了力的。
“皇上不信他了。”花想容輕聲說道,“就像當初的柳家。”的聲音中滿是苦。
一個多疑的君王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禍患,當初在柳芙毓上已經見過一次,沒想到如今連堂堂文遠侯也沒能幸免。
文遠侯這些年算是功退,可皇上卻對他并不放心,他覺得這個年輕時野心的侯爺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開手中的權勢,現在的低調一定是在暗中謀著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986 章

農門有喜無良夫君俏媳婦
東臨九公主天人之姿,才華驚艷,年僅十歲,盛名遠揚,東臨帝後視若珠寶,甚有傳位之意。東臨太子深感危機,趁著其十歲壽辰,逼宮造反弒君奪位。帝女臨危受命,帶先帝遺詔跟玉璽獨身逃亡,不料昏迷後被人販子以二兩價格賣給洛家當童養媳。聽聞她那位不曾謀麵的夫君,長得是兇神惡煞,可止小孩夜啼。本想卷鋪蓋逃路,誰知半路殺出個冷閻王說是她的相公,天天將她困在身旁,美其名曰,培養夫妻感情。很久以後,村中童謠這樣唱月雲兮哭唧唧,洛郎纔是小公舉。小農妻不可欺,夫婦二人永結心。
173.1萬字8.18 37020 -
完結237 章
重生后王妃咸魚了
沈妝兒前世得嫁當朝七皇子朱謙,朱謙英華內斂,氣度威赫,為京城姑娘的夢中郎君,沈妝兒一顆心撲在他身上,整日戰戰兢兢討好,小心翼翼伺候。不成想,朱謙忍辱負重娶出身小門小戶的她,只為避開鋒芒,韜光養晦,待一朝登基,便處心積慮將心愛的青梅竹馬接入皇宮為貴妃。沈妝兒熬得油盡燈枯死去。一朝睜眼,重生回來,她恰恰將朱謙的心尖尖青梅竹馬給“推”下看臺,朱謙一怒之下,禁了她的足。沈妝
37.5萬字8 18649 -
完結91 章
念卿卿(重生)
別名:攬嬌 梁知舟一生沉浮,越過尸山血海,最后大仇得報成了一手遮天的國公爺。人人敬著他,人人又畏懼他,搜羅大批美人送入國公府,卻無一人被留下。都說他冷心冷情不知情愛,卻沒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漫長的夜里,是如何肖想自己弟弟的夫人,如癡如狂,無法自拔。他最后…
32.2萬字8 2844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80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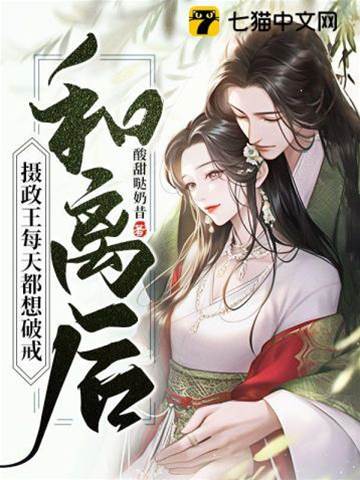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