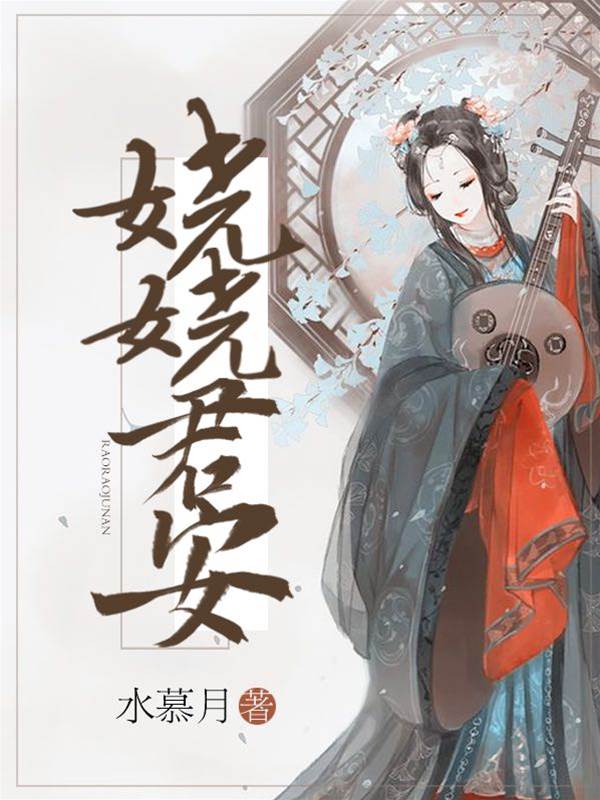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嫁給權臣以後》 [嫁給權臣以後] - 狹路
時氣臨近暑,悶了整個夏日的暑熱漸漸消退。昨晚連著兩場雷雨,半夜裡霹靂雷聲將無數人驚醒,瓢潑大雨傾盆而下時,天地間盡是雨點砸在簷頭晚上的的劈啪聲,吵得人難以眠。待清晨推窗,卻是滿目碧翠,清涼撲面而來。
院裡積著未排盡的雨水,葉上水珠滴滴答答。
悶熱散去,總算有了夏日走到尾聲的味道。
魏鸞自朗州回來後,除了去敬國公府看娘家長輩外,便日日留在曲園裡,莫說去城外消暑閒遊,便是街市都沒踏足半步。如此閉門許久,加之天氣炎熱懶得彈,難免煩躁無趣,上這場雨,倒有了遊園散步的興致。
一圈逛回來,北朱閣外卻候了個盧珣。
魏鸞還當是盛煜出事了,心裡猛地一跳,忙詢問緣故,卻見那位恭敬拱手,道:“主君遞了家書回來,命屬下給夫人。”而後行禮告退,前微不可察地瞥了眼站在魏鸞後的染冬,可惜染冬低頭瞧著腳尖,似不太想理他。
盧珣面不更,大步離去。
魏鸞見他神如常,也沒轉達旁的話,那顆微懸的心也悄然落穩。拆開信上蠟封,裡面裝著折好的紙箋,上面銀鉤鐵劃,是盛煜的筆跡不日將歸,等我。
極簡短的言辭,沒半個多餘的字。
然而魏鸞拿在手裡時,卻仍忍不住微笑。
從前關乎盛煜行程的消息,魏鸞幾乎都是從盧珣口中得知,而今,盛煜卻會拿書信徑直告訴,而非假他人之口。雖說兩者都是用玄鏡司的快馬送曲園,再來到跟前,但中間細微的差別,細想起來,卻仍令人歡喜。
魏鸞收好書信,仰頭遠,但覺長空湛藍如洗,滿園花木繁蔭。
Advertisement
分別太久,有點想盛煜了。
甚至,哪怕心底為盛煜言辭裡的些微自負而哂笑,但末尾那兩個字,確實讓忍不住生出了等待的心思。夏盡秋至,夫妻倆婚近乎一載,卻始終聚離多,中秋佳節近在眼前,原以為會是兩地月的淒清,而今看來,是能曲園團聚,一道飲酒賞月了。
種種期待升騰而起,魏鸞開始掰著指頭數日子。
……
兩日後,幾騎快馬飛馳京。
盛煜上是趕路的青衫,來不及回府換裳,先宮復命。
巍峨的麟德殿裡,永穆帝等候已久。
庭州的事關乎斬除章氏的大計,亦關乎邊防要塞,舉足輕重。鎮國公卸了大都督之職後,仍有數万兵將各司其職,這其中有忠心捍衛邊塞百姓的,亦有不念皇恩,只為章氏效力之人,當中不乏負要職的猛將。
對庭州軍中的人事清洗,須慎之又慎。
京城與庭州相隔千里之遙,永穆帝雖派了心腹猛將前往,又讓盛煜親自去照應協助,卻始終不敢鬆懈。而今盛煜歸來,將當地的形詳細禀報,說狄肅雖消失數年,但在軍中的威仍在,被不舊日部將惦記,如今橫空出世,融得併不算艱難。
玄鏡司留了不人手暗中協助,撥反正指日可期。
永穆帝聽罷,總算放心。
在盛煜禀完事告退之前,卻招手示意他近前,將手裡挑出的一摞奏摺指給他看,緩聲道:“章孝恭雖在獄中,手卻沒閒著。此役章氏損兵折將,必不會善罷甘休,這還只是鋪墊,等你回京的消息傳出,彈劾的奏摺怕是能堆山。”
話音才落,忽而咳嗽起來,永穆帝不讓人擔心,竭力忍著,憋得臉上微紅。
Advertisement
盛煜顧不得那摞奏摺,目微。
“皇上為此事日夜勞,龍可還安好?”
“無妨。”永穆帝擺擺手,續道:“玄鏡司雖得朕重,經辦這些重案時,卻得罪了不人。章氏存心要斬朕的臂膀,要挑病也不難,京中若,對庭州那邊不利。與其讓章家追著玄鏡司深挖,不如遞把差不多的刀子過去,你先歇一陣,等時機合適,瞧著辦吧。”
說罷,抓了手邊的茶杯,匆忙喝水。
盛煜明白他的意思,拱手應命,目卻仍落在皇帝臉上。
一別兩月,他那邊有驚險也有喜悅,京城里永穆帝的境卻似乎不太好。至,盛煜離開時永穆帝雖稍疲態,氣卻還不錯,如今非但鬢邊大半都已銀白,臉上也消瘦不,眼窩都快凹進去了。
似這般連連咳嗽,卻不多見。
盛煜眼底見地浮起憂慮,顧不得君臣尊卑之別,道:“皇上聖當真無恙?時氣替,更須留意,若有棘手的事,皇上盡可吩咐微臣去做。朝堂勢迫,微臣無需休息。”說話間,恭敬垂首,目落在金磚鋪的地面,眉間擔憂卻無從掩藏。
永穆帝頗詫異地瞥了他一眼。
除了朝堂大事外,這沉默寡言的寵臣甚如此長篇大論地關懷他。
倒比從前懂得關懷冷暖了。
永穆帝角了,道:“無妨,京城的事不急在一時。”
既是如此,盛煜總不能再揪著聖安康不放,遂行禮告退。
誰知才出麟德殿沒多久,迎面又見了周令淵。
仇人相見,自是分外眼紅。
更何況是周令淵和盛煜這樣於公於私都有深仇大恨的。
周令淵雖無證據在手,卻很清楚當日將他強行擄走,囚在暗室的人是誰。更知道盛煜如此狂妄忤逆的舉,給章家帶來了怎樣沉重的一擊。原本健步如飛的步伐在瞧見走下丹陛的那人時霎時頓住,周令淵那張清秀溫和的臉上,難以克制地浮起憤怒。
Advertisement
盛煜雖腳步未停,卻也不自覺地放緩。
兩人相向而行,周令淵在駐足後死死盯著對面,袖中雙拳握。
盛煜則彷若無事,在兩步外駐足,拱手行禮道:“拜見太子殿下。”躬抱拳的姿勢維持了片刻,卻始終沒聽到對方的回應,他不由得抬目瞧去。這一瞧,便上了周令淵怒睜的雙目,像是被毒蛇舐過,鋒銳而刻毒,整個眼白幾乎都紅了。
盛煜目沉靜,只注視著他。
毒辣的日頭曬在頭頂,不遠有侍列隊走過。
周令淵似猛然驚醒,抬了抬手。
“聽聞盛統領離京兩月,公務繁重,手上又沾了許多人命。如此不辭勞苦地為父皇分憂,就不怕累死在途中?”他將累死二字咬得極重,便是宮城之中,也毫不掩飾敵意。想來那段時日的囚對他刺激不小,若此刻遞把刀過去,周令淵恐怕能把盛煜上的一刀刀剮下來。
這樣的刻骨恨意,便是盛煜都始料未及。
他不閃不避,沉聲道:“為皇上分憂,何須畏首畏尾。當日鏡台寺遇刺後重傷昏迷,往鬼門關走了一遭還能撐過來,可見微臣留在世上,還有未盡之事。”
如此態度,是毫不在乎威脅。
真以為有永穆帝寵信,玄鏡司就能千秋萬代地尊榮下去?
周令淵冷笑了聲,拂袖而去。
盛煜垂眸,目不斜視地往宮門口走。
其實方才乍然見,除了仇人見的那種微妙外,他在走向周令淵時,也曾想過,是否提醒一句永穆帝欠安的事,讓為嫡子的東宮留意。而今看來,是大可不必了。換在從前父子融洽時,周令淵或許還有點良心,如今這位太子心裡恐怕只剩仇恨與慾。
Advertisement
父子親在章氏的裹挾下,不堪一擊。
盛煜想著永穆帝花白的鬢髮,想起從前皇帝對太子的諄諄教誨、教導栽培,暗自嘆息。
而後疾步出宮,直奔曲園。
那裡有人在等他。
豔婉麗的眉眼浮腦海,如一抹春風拂過,令盛煜冷沉的心緒融化了許多。腳步不自覺地加快,在走過架在護城河上的拱橋後,翻上馬,迫不及待。
……
魏鸞此刻卻在樂壽堂裡。
雕細鏤的長案上擺著瓜果點心,還有新熬好的梨湯,拿海棠花碗裝著,兩溜擺開。魏鸞坐在婆母遊氏的下首,對面時長房的慕氏婆媳,最上首則是盛老夫人,旁邊的管事侍拿了紙筆,正慢慢記下眾人議定的事。
眷齊聚,是在商議盛月容的婚事。
盛家兩房男兒各有所長,卻唯有盛月容這一位孫,加之要嫁的是伯府,婚事更是馬虎不得。嫁妝等由慕氏來籌備,婚宴等須邀請賓客的事卻是老夫人親自坐鎮,因怕屆時事有手忙腳,便早早地商議起來,盡快籌備。
魏鸞來這裡,自是當參謀的。
的親兄長魏知非雖尚未娶妻,堂兄卻是早就家了的。敬國公府本就是先帝親封的爵位,彼時又極得后宮和東宮親近,論起在京城的排場,僅遜於鎮、定兩座公府。魏知謙當日的那場婚事辦得讓人津津樂道,方的禮數也不辱門楣。
盛家就算未必有那排面,照著學學禮數,也免得被伯府看扁。
事一件件地商議,甜的梨湯,也頗適意。
在快要議定時,院中忽有聲音約傳來。
聽著像是男人的。
魏鸞自接了那封不日將歸的信箋後,便時時翹首等待,而今聽見這靜,不由得豎起耳朵細聽。那聲音迅速靠近,亦愈發清晰分明,魏鸞聽出那是盛煜在說話,腔猛跳,心思立馬飄出了敞廳,若不是長輩妯娌在場,怕是能立時迎出去。
好在盛煜長步快,不過片刻便到了跟前。
門口擺著的繡仙鶴紗屏後面人影一閃,天青的角微晃,男人拔頎長的姿如同旋風,轉瞬間便到了案前。長途跋涉後風塵僕僕,他甚至未來得及換裳,便奔祖母來,朝長輩問安過後,深炯的目便落到了魏鸞上。
兩人眼神匯,眼底的欣喜清晰可見。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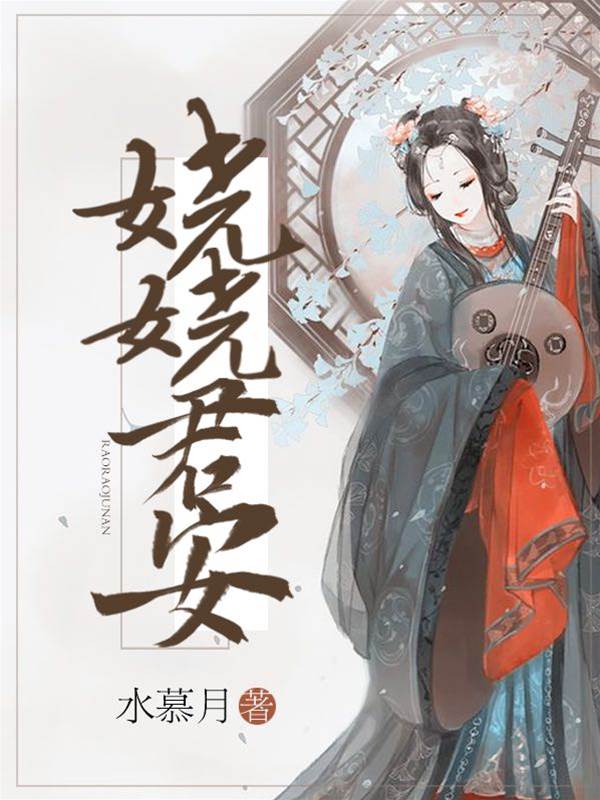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