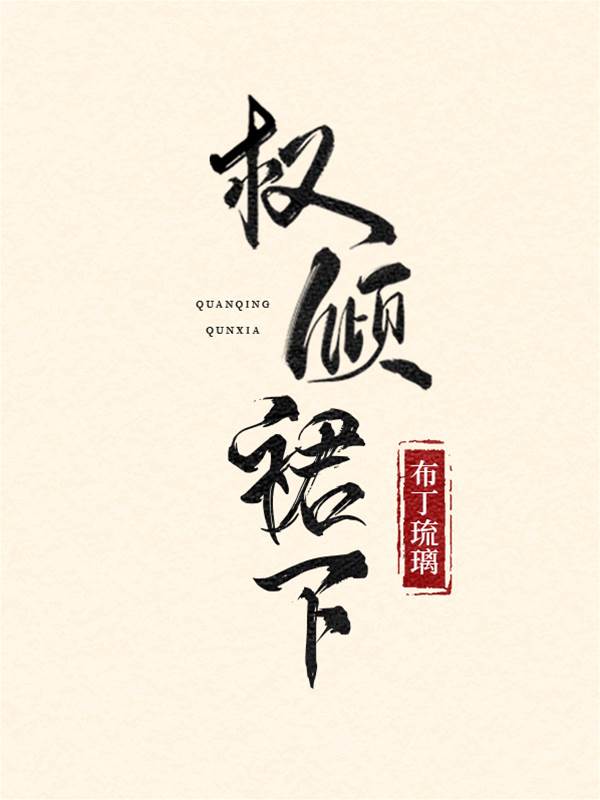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我妻薄情》 第 165 章 碎瓶人
m.kelexsw.com
新婚第四天。
冬天給柳氏請安的時間是七點鐘,程丹若六點起來,洗漱穿,就著熱茶吃爐上熱過的糕餅墊。
謝玄英有穿道袍,反倒穿了窄袖襖和,干練利索。
瞧了他幾眼。
“今天該晨練了。”謝玄英說著,手住的茶杯,覺到燙才放下,轉而吩咐竹枝,“帳換了。”
程丹若吃點心的作一頓。
竹枝應下,請示道:“換哪頂?”
他程丹若。
程丹若:“梅花?”
謝玄英白了眼:“正月才用梅花,這才十月,還是用吧。”
程丹若點點頭,咽下口中的糕點,去和柳氏請安。
打卡上班后,回去吃早點。
謝玄英回來了,重新臉換服,再到東次間和一道用膳。
“多吃點。”他督促,連連給夾菜,恨不得把喜歡的全塞碗里。
程丹若瞥他兩眼,在他臉上不到任何痕跡,好像昨晚說了以后,他就完全消氣了,一點都有賭氣的意思。
真是個好人,……垂下眼眸,咬了里的腌蘿卜,卻嘗不出一點味道。
飯畢,謝玄英和說:“我要出去見個朋友。”
程丹若點點頭:“好。”
然后他就出去了。
天氣很好,站在窗邊發了會兒呆,隨后來喜鵲,開了東廂房的庫房。
觀察了一下環境,人挪箱,把嫁妝里容易損傷的布匹、箱櫥、書畫挪到另外兩間,只留下金銀玉。
而后用一個大石『』屏隔斷,辟出半間通風明亮的空間,拿兩張條案拼了,湊出一個拐角桌臺。
又搬出嫁妝里的博古架,把香、酒、『藥』和茶擺好。
瑪瑙問:“夫人這是要做香,還是釀酒?”
Advertisement
程丹若:“做『藥』。”
香、酒、『藥』、茶的工都不,一樣樣都別致巧,除了個別實驗需要另行燒制,其他完全可以替代。
置完實驗室,程丹若就寫了“大蒜素”三個字,在墻上鼓勵自己。
在古代做麼都不容易,怕浪費,提前寫好實驗步驟,揣兩遍才工。
第一步:做培養基。
大蒜素提取出來有有效果,總得培養點細菌。
做培養基的主要原材料,主要是牛和瓊脂,聽著簡單,可中『藥』的瓊脂膏是用鹿角熬制,并不是后世的瓊脂。
瑪瑙去大廚房,找做點心的人問,有有一種從海草里熬出來的膠,半明的樣。
侯府不愧是侯府,做點心的老師傅一聽,就知道是石花膠。
不愧是大公司。
程丹若多了兩分信心,讓喜鵲拿了瓊膠,大半留著第一次實驗,剩下的給陪嫁來的一夫『婦』,讓他們去買,以備失敗后再次嘗試。
牛也是從廚房要來的,熬湯,加剪碎的瓊脂,趁熱用紗布過濾,得出一瓶溶『』。
培養皿是香盒,燒得絕倫,用來培養細菌,有那麼一點暴殄天,獨它有蓋,能閉,只能忍痛用了。
先高溫消毒,再倒溶『』,閉。
當然,這也有辦法保證無菌,可考慮到細菌培養出來也難以篩檢,只能算了。
這步簡單,做得倒也功,很快結出一層固培養基。
細菌也好辦,上完廁所摁兩下,過兩日,便養出了一些不知名的菌落。
假如在實驗室里,現在就該用革蘭氏染『』法尋找合適的菌落,可程丹若有這個條件,培養出來就算。
下一步,搗蒜,加蒸餾瓶,點火蒸餾,而后再冷卻,提取油。
Advertisement
火折點燃炭火。
火苗竄起,『』舐著玻璃瓶,加熱蒜末。
“咔嚓”。
麼聲音?
程丹若繃心弦,立即檢查,卻發現蒸餾瓶上出現了一道裂紋。
愣住了,眼睜睜著半明的琉璃瓶碎掉,在桌上裂一片片碎渣,還有不飛濺到地上。
瓶碎了。
剛點火都不到五分鐘,怎麼就碎了呢?
趕蹲下來去撿,心里卻納悶:怎麼剛開始就搞砸了?
為麼這麼簡單的蒸餾,都能搞砸呢。
就好像結婚。
結婚不是很簡單的事嗎?很多人都會結婚,在古代,幾乎每個人都結婚。
婚后,無非是孝順公婆,友丈夫,而想要的更多,要與他一道經營事業,從而獲取想要的東西。
怎麼就搞砸了呢?
手指緩緩收攏,尖銳的琉璃碎片扎手指,卻恍然不覺。
平淡地將碎片收攏,放到桌上,心里還在思考。
可大腦不復平日的迅捷,有些空白和混『』,好像過低的無法運行最新的件。
程丹若想不明白,為麼莫名其妙就搞砸了呢。
我有麼地方做得不嗎?反思。
柳氏,很恭敬,妯娌,堅決和柳氏站在一起,立場鮮明。柳氏不方便和兒媳置氣,卻可以爭鋒相。
家事,任用柳氏新給的瑪瑙,一舉按住了晏家和謝家的丫鬟,目前霜『』院運行良好。
陳家,維持原先的恭敬,既不落人口舌,說攀高枝后不起親戚,又讓陳家無法拿。
這些事和婚前的預計一模一樣。
為麼……為麼才第四天,就出現了問題?
程丹若拾起地上的碎片,一片片放在掌心,深深凝視。
在山東的時候,謝玄英愿意冒著危險去救,毫無疑問是信任他的。他當初月下的剖白,也真切地打了。
Advertisement
選擇婚姻,與方是謝玄英不無關系。
好像結了婚,一切都變了。
有多和預想不同的事。
以為房時,自己能夠平靜地,人的已經過多了,事到臨頭還是張。
以為相時,自己能游刃有余,就好像陳老,洪尚宮,宮里的其他人。結果就變現在,莫名其妙就不勁了。
假如說,在晏家書房的事只是意外,昨天的異常卻著實令心驚。
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明明智知道,不該說傷人的話,可以好好商量,卻一意孤行,以最大的力度反擊方。
更可怕的是,當他氣的時候,當獨自睡到炕上的時候,反而到了一安寧。
程丹若用帕包好碎片,手掌在桌上按,尋找更細微的碎渣。
有幾粒硌到了皮,尖銳細的刺痛。
輕輕剝落黏在手心的碎片,思緒未曾斷裂,依舊盤桓在昨夜。
為麼婚姻和想的不一樣呢?
忽略了麼?
人。
是人啊。
再怎麼類比,婚姻終究不是開一家公司,也不是尋找一個合伙人,婆媳、家務、事業,全都不是最關鍵的東西。
婚姻是兩個人組合了一個家庭。
這就意味著,他名正言順地將拉進自己的活,合并的活,食住行,每件小事都有方的影。
在宿舍,好歹簾一拉,小小的床上就是私人空間。
婚姻卻迫使一個人,必須接另一個人加自己的活。兩人相親,呼吸相聞,一道吃、一道穿,榮辱與共,親無間。
程丹若扶著椅坐下,怔怔出神。
能做到嗎?
難了,無法因為他是“丈夫”,就所應當地相信他,接他。
潘姨娘有名分,一樣丈夫轉賣;墨姨娘有寵,照樣轉頭就忘;黃夫人賢惠大度,耽誤丈夫納妾。
Advertisement
們也有丈夫。
把他當做親人呢?
堂兄和脈相連,為帶過街上的花鼓,給吃過難得的麥芽糖,可關鍵時刻,還是毫不猶豫地拋棄了。
父親好不容易同意教醫,卻只肯教皮『』,和祖母說,姑娘早晚要嫁出去,終歸是外人,醫教的本事,還得傳給兒。
母親不是有噓寒問暖過,懷孕后,順章地忽視了的病。半夜發燒,自己倒了殘茶,咽下『藥』片,在床角渾發抖,冷汗止都止不住。
父親不是父親,母親不是母親,親人不是親人。
可以改變這一切嗎?
不,不能。
當,陳老真的嘔心瀝,端茶倒水,噓寒問暖,老咳嗽一聲,夢里都會驚醒。
為把屎把『尿』,倒痰盂,做了能做的所有事。
結果呢。
唯一值得慶幸的,大概就是從未有過期待,所以不傷心,也不流淚。
程丹若慢慢蹲下,蹲到桌底下,無聲闔眼。
原來,十五的人,已經悄無聲息地摧毀了的一分。
失去了與人建立親關系的能力。
他越靠近,越拒絕。
我犯了一個大錯。痛苦地想,我貪心了,我高估了自己,我以為我可以,其實,今日所有的就,不是在于有多麼強大,而是足夠幸運。
幸運不會一直眷顧的。
終于為自己的魯莽,付出了代價。
而這條路……不可能回頭,也有辦法回頭。
“夫人。”門外傳來瑪瑙的聲音,“茶好了。”
程丹若瞬時睜開眼,五歸位,安靜起:“進來吧。”
瑪瑙捧著托盤,見一帕的碎片,不焦急:“瓶碎了,我們來收拾就是,夫人怎麼自己手了?”
“不要。”程丹若笑道,“我自己撿才知道在哪里。了,你幫我把香爐拿過來,里一蒜味兒。”
一說,一打開窗戶,讓冷風灌室。
風吹過紙張,嘩嘩作響,如聽松濤。
瑪瑙取來爐瓶三事。
程丹若道:“我自己來。”
丫鬟將香爐放到旁邊的圓幾上。
程丹若放進一塊炭,蓋上香灰,鋪平,再放上銀葉,夾進香餅。
熱力烘烤下,清苦的香氣徐徐升起。
依稀悉。
默默地著冉冉升起的香煙,擺正椅,重新坐下。
鋪平紙,擰開墨囊,『』『』筆尖,開始勾勒蒸餾瓶的樣。
瓶碎了就碎了,再燒一個就是。
墨跡勾勒出琉璃瓶的廓,專心致志,好像方才短暫的崩潰,從未出現過。
一刻鐘后。
畫好圖紙,在窗前等待墨跡晾干。
微風拂,香氣襲人。
混沌的思緒中,一個名字涌上腦海。
趙清獻公香。記起來了。
程丹若陷了沉默。
片刻后,轉翻找箱籠。
一個黑漆螺鈿盒中,藏著做完的扇套。雖然過程艱辛,在宮里諸多好心人的幫助下,仍舊完了繡活。
程丹若拿起它,心想,我不能認輸。
現代的父母給過無微不至的,現代的朋友曾與惺惺相惜。見過人世間好的一,就不該忘記。
不要痛苦打敗。
可以不他,至,不應該傷害他。
*
傍晚,謝玄英收到了程丹若的荷包,這才意識到事和他想的不一樣。
他早就不氣了。
不過是句無心之言,既然還愿意和他親近,又有麼好計較的呢?夫妻之間還要慎重其事道歉,也疏了。
“我不要。”他把荷包推回去。
程丹若自己的荷包,再他腰上掛的,嘆口氣:“好吧。”
拿扇套改荷包,好像是有點敷衍了。
正要收回來,他卻一把握住的手:“為麼要賠禮道歉?”
“我說了很過分的話。”道,“人總要是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的。”
謝玄英板起臉:“我是你丈夫。”
程丹若不解,他為麼總要強調這一點?丈夫這個份,意味著“權威”和“控制”,每次提起,都讓不舒服。
“你在外做錯事,我會替你承擔,你在家里做錯事,我也會包容你。”謝玄英說著,又有一點點心虛,“再說昨天……”
他別過臉,“是我嚇到你了吧?我也不是有意的,我以為……算了,你也原諒我吧。”
程丹若沉默了。
許久,慢慢道:“下次我請求你離開的時候,你能馬上照做嗎?”
謝玄英想答應,忍住,費解地追問:“又不是見過,為麼沐浴不準我進來?”
程丹若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私人空間,蹙眉想了好一會兒,才說:“沐浴是很私的事,和更如廁一樣。我不介意人的糞便,你愿意嗎?”
謝玄英的表凍結了。
“我知道了。”他艱難開口,“我答應你。”
程丹若如釋重負,覺得又能呼吸了。
謝玄英反倒不安起來,猶覺寒『』直豎:“快把這事忘了,不許再說。”
程丹若:“便便。”
他:“閉!”
。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本文齁甜,雙潔,雙強,雙寵,雙黑)世間有三不可:不可見木蘭芳尊執劍,不可聞太華魔君撫琴,不可直麵勝楚衣的笑。很多年前,木蘭芳尊最後一次執劍,半座神都就冇了。很多年前,太華魔君陣前撫琴,偌大的上邪王朝就冇了。很多年後,有個人見了勝楚衣的笑,她的魂就冇了。——朔方王朝九皇子蕭憐,號雲極,女扮男裝位至儲君。乃京城的紈絝之首,旁人口中的九爺,眼中的祖宗,心中的閻王。這一世,她隻想帶著府中的成群妻妾,過著殺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奢侈糜爛生活,做朵安靜的黑心蓮,順便將甜膩膩的小包子拉扯大。可冇想到竟然被那來路不明的妖魔國師給盯上了。搶她也就罷了,竟敢還搶她包子!蕭憐端著腮幫子琢磨,勝楚衣跟大劍聖木蘭芳尊是親戚,跟東煌帝國的太華魔君還是親戚。都怪她當年見
118.2萬字8 18555 -
完結310 章

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李泠瑯同江琮琴瑟和鳴,至少她自己這麼覺得。二人成婚幾個月,雖不說如膠似漆,也算平淡溫馨。她處處細致體貼,小意呵護,給足了作為新婚妻子該給的體面。江琮雖身有沉疴、體虛孱弱,但生得頗為清俊,待她也溫柔有禮。泠瑯以為就能這麼安逸地過著。直到某個月…
47萬字8 684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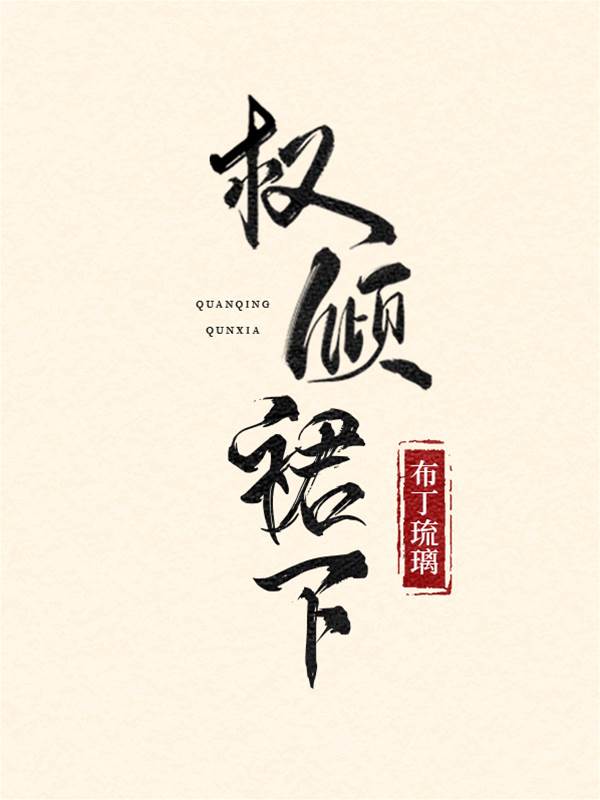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019 章

攝政王今天又在哄王妃
穿成了被繼母虐待被繼妹搶婚的懦弱伯府大小姐。云嫵踹掉渣男虐廢小三,攪得伯府天翻地覆。接著一道圣旨將她賜給了攝政王。攝政王權傾朝野,卻冷血無情,虐殺成性。人人都以為云嫵必死無疑,仇人們更是舉杯相慶等看好戲,豈料……在外冷血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卻天天柔聲哄著她:“寶貝,今天想虐哪個仇人。”
184.8萬字8 38042 -
完結183 章

誤酒
朝和小郡主黎梨,自幼榮華嬌寵,樂識春風與桃花,萬般皆順遂。 平日裏僅有的不痛快,全都來源於她的死對頭——將府嫡子,雲諫。 那人桀驁恣肆,打小與她勢同水火,二人見面就能掐。 然而,一壺誤酒,一夜荒唐。 待惺忪轉醒,向來張揚的少年赧然別開了臉:“今日!今日我就請父親上門提親!” 黎梨不敢置信:“……你竟是這樣的老古板?” * 長公主姨母說了,男人是塊寶,囤得越多就越好。 黎梨果斷拒了雲諫送上門的長街紅聘,轉身就與新科探花郎打得火熱。 沒承想,那酒藥還會猝然復發。 先是在三鄉改政的山野。 雲諫一身是血,拼死將她帶出狼窩。 二人跌入山洞茅堆,黎梨驚詫於他臂上的淋漓刀傷,少年卻緊緊圈她入懷,晦暗眼底盡是抑制不住的戾氣與委屈。 “與我中的藥,難不成你真的想讓他解?” …… 後來,是在上元節的翌日。 雲諫跳下她院中的高牆,他親手扎的花燈猶掛層檐。 沒心沒肺的小郡主蜷縮在梨花樹下,身旁是繡了一半的香囊,還有羌搖小可汗的定情彎刀。 他自嘲般一笑,上前將她抱起:“昨日才說喜歡我……朝和郡主真是襟懷曠達,見一個就能愛一個。” * 雲諫出身將府高門,鮮衣怒馬,意氣風發,是長安城裏最奪目的天驕。 少年不知愁緒,但知曉兩樣酸楚。 一則,是自幼心儀的姑娘將自己看作死對頭。 另一則,是她不肯嫁。
27.1萬字8 8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