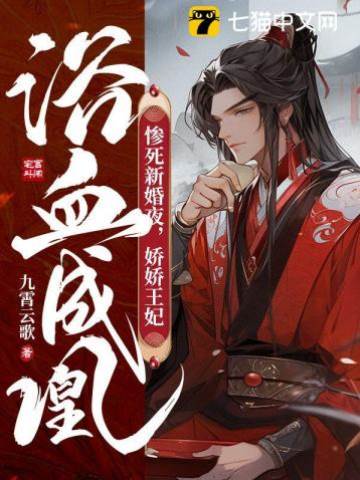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我妻薄情》 第 252 章 樂新年
m.kelexsw.com
臘月的生活忙碌又充實。
程丹若照舊為衙門的吏員安排年貨,遵循名單寫帖子,并額外為他們提供了五斤線,算作員工福利,回家讓人織裳,這個冬天就不怕凍了。
吏員們自是恩戴德,紛紛回禮。
這家送了一籃棗子,那家送點腌菜,還有人今年養的鴨吃得正,專程送來熏好的鴨。
程丹若收到一大堆土儀,自家吃也吃不完,急打包,送去京城給晏家。
晏鴻之接著年禮,大為驚喜,立馬下帖子邀請二三好友賞雪小酌。
他的朋友分別是禮部尚書王厚文、詹事府詹事余有田、國子監司業艾世年,不是他當年的故友舊,就是后來認識的文壇好友。
除了王尚書,都是清水衙門,職也不高,一向只談風月八卦,不提政事(才怪了)。
今天,晏鴻之就準備了熏鴨脯,得意地說:“嘗嘗,是我兒從大同寄過來的。”
王尚書嘗了口,沒吭聲。
余詹事是個實誠人,吃完就說:“口味平平,侄的手藝有待進啊。”
晏鴻之卻道:“這可不是親手做的,是當地百姓送的,還有什麼鴨鵝蛋,腌菜糖蒜,說送的人家太多,自己吃不了,送來給我和義母嘗嘗。”
艾司業滿臉愕然:“百姓送的?”
“可不是。”晏鴻之說,“三郎的是做得好,可不及得民心啊。”
王尚書就知道有貓膩,此時方說:“功在千秋,也難怪。”他有點憤憤,“明明是我看上的孫媳,你偏要從中作梗。”
晏鴻之語重心長:“你家小六也沒看上啊。三郎看得準。”
王尚書多有點慨:“姻緣之事,真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Advertisement
王六已經中了進士,二甲三十六,以他的年紀,說句年英才不過分。他爹娘早就好了媳婦,是年祭酒家的大姑娘。
這位也曾是柳氏相看過的兒媳,樣貌秀麗溫婉,才學過人,據說在家時就負責給弟弟啟蒙。
和王絮娘擅長詩文不同,這位年姑娘通經史,為人低調,鮮出風頭,是典型的書香門第的姑娘,清貴典雅。
王六本不愿,可先前在寺中遇見,聽見和弟弟講解佛偈,忽然就樂意了。
余詹事見王尚書語氣憾,不由問:“怎麼,子真家的姑娘就這麼好?”
晏鴻之出淡淡的微笑。
“各家有各家的好。”都定了親,王尚書傻了才會說他家壞話,“年家姑娘也懂事孝順——我這不是想和子真當回親家麼。”
這也是真心話,年家姑娘知書達理,王尚書不是不喜歡,然而,朝廷風云變幻莫測,小五尚郡主,小六年輕,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就是下一個許繼之。
風雨來,年家姑娘能陪著小六隨波沉浮,卻不能幫他掌舵。
“不說了。”王尚書又嘗了口鴨脯,覺得下酒不錯,“吃酒、吃酒。”
晏鴻之剛舉起酒杯。
墨點:“老爺!”
他一哆嗦。
“太太說了,您不能再喝酒了。”墨點苦口婆心,“您忘了嗎?姑娘把藥包都寄過來了,您再喝酒,就得每天喝藥調理了。”
晏鴻之一聽,腳趾就約劇痛,趕放下酒杯:“我不喝,不喝還不行嗎?”
王、余、艾三人出大聲的嘲笑,空氣中充滿了愉快的氣氛。
--
臘月中,程丹若收到了洪夫人寄來的年禮。
比起靖海侯府的大手筆,晏家的東西并不多。晏鴻之準備了些書和筆墨,洪夫人送來一套江南的面脂、口脂,都是家常實用的東西。
Advertisement
當然,不了家信。晏鴻之提起前些日子的聚會,王六的婚事之外,余詹事是在詹事府工作,這是為太子服務的部門,如今負責為幾位候選人教書。
他說,皇帝依舊每月檢查諸位藩王的功課,比起其他對手,郡王好學聰明,謙遜有禮,說鶴立群一點都不夸張。
有史上疏,請求早立皇嗣,將其余藩王打出京,因為這不合祖宗規矩。
這份奏折送上去,石沉大海,毫無反應。
然后,艾司業提供了王五的態。他和王尚書說,王五自從進國子監后,讀書倒也算認真,有了不朋友。
王尚書一點都沒表態。
“義父的朋友……”程丹若斟詞酌句,“都有特。”
謝玄英道:“世兄在戶部為,老師難免上心,免得卷紛爭。”
“這麼看,許尚書致仕,確實是個聰明的做法。”程丹若道,“我看著信,都覺得心驚跳。”
謝玄英蹙眉思索:“我覺得,陛下似乎……”
“嗯?”
“說不好,陛下的做法有點奇怪。”謝玄英難以描述心中的怪異,“總之,過繼一事,你我絕不能牽扯。”
程丹若點點頭,道:“我只盼陛下康健,越久越好。”
他們還太弱了,不了帝王的恩寵和扶持。假如皇帝有個萬一,新君上位,誰知道是什麼樣的景象。
“明年是任上的最后一年。”程丹若拍拍他的膛,“我們好好做,爭取早日升。”
謝玄英握住的手,點點頭。
--
年節的氣氛越來越濃,門口好對聯,門楣上掛了金銀泊紙,全都剪人或吉利的圖案,窗戶上各紙畫,什麼人花草,樣樣不同。
程丹若寫了一堆的“酉”字,倒在上,據說可以招財避災。
Advertisement
親自剪柏樹枝,穿過柿餅,扎進底下襯托的橘子,是為百事大吉。這個被慎重地擺在三堂的供桌最中央。
左邊的位置,是一個放大柿子的白瓷盤,周圍撒了一圈花生,右邊是一個大橘子和一個大凍梨。
謝玄英瞧了半天,只瞧出一個百事大吉,問:“旁邊兩個是什麼?”
程丹若說:“好事(柿)生(花生),大吉(橘)大利(梨)”
謝玄英擰眉,抬手把凍梨拿走,換了栗子。
“怎麼能用梨呢?”他教訓,“梨不祥。”
程丹若:“……”迷信。
凍梨,已經塌塌的,直接剝皮吃掉。
除夕當日,衙門外頭架起了一個鐵盆,底下是二十四條松柴,故又“松盆”。這東西也沒有別的用,燒得火熱后過,就能除晦氣。
這是吏書的建議,他說今年遇到蝗神,大家心里都不太舒服,為了祈求明年風調雨順,今年最好祭祀一下。
程丹若已經意識到,在民智未開的古代,多搞祭祀和合理的迷信活,有利民眾心。
但祭祀費錢,大冬天讓謝玄英在外面吹幾個時辰的冷風,也覺得沒必要,于是就想了火盆的法子。
而且,專門把火盆放在大門外,照壁的地方。
這有個專門的名稱,“宣化坊”,是父母教化百姓之地,有時候張榜通知事項,也專門在宣化坊的墻邊。
擺在這里,意思也很明顯,與民同樂。
為安全著想,松盆上罩著鐵,而且用竹木搭了一個矮橋,免得火星燎人,還能防風雪熄滅火堆。
竹橋西面進,東面出,終點掛了一面銅鑼,過去就敲一下,驚走小人惡鬼。
很簡單的設施,老百姓卻很興趣,一大早就有人在火盆敲鑼。咚——咚——咚。
Advertisement
清脆的鑼鼓聲響徹天際,今年秋天蝗災帶來的霾,好像也因此消失了。
謝玄英十分佩服妻子安穩民心的本事:“你是怎麼想到的?”
程丹若如實道:“這樣省錢又暖和。”
他懂了:“你心里有百姓。”
天漸暗,街上行人漸漸稀,大家都回家過年了。
和去年除夕一樣,程丹若和謝玄英先吃年夜飯,酒足飯飽,就打丫頭去西花廳玩耍,兩人則鉆進次間,坐在炕上打牌。
燭火通明,炕邊的矮桌上擺著屠蘇酒、冰糖果子、堅果拼盤。
堅果必須是有嚼頭的,什麼栗子,榛子、銀杏、炒蠶豆,或者骨、蟹鰲之類的東西,這“畢剝”,和竹一個用意,必須吃起來有響頭才好。
程丹若額外烤了一盤薯片,撒上胡椒當零食。
謝玄英就著的手嘗了,道:“紅薯和土豆都是良種,吃法多且飽腹,真是一等一的好。”
“還有苞米。”程丹若清脆地咬斷薯片,“這也是海外之,與它們是一個地方,耐旱耐寒,可以榨油。”
謝玄英:“長什麼樣?”
程丹若道:“改天給你畫。”
他說:“總龍子化替我們尋,不是個辦法,不若明年末,我們尋個機會,調到兩廣去,如何?”
道:“能去自然最好,可這些作反倒不適宜兩廣悶熱的氣候。它們原本是長在海外國度的北方。”
謝玄英看過買來的世界地圖,對地球的疆域已有了解:“也是在北地,那里也一樣冷旱嗎?”
程丹若:“……這就要說到太和大地的關系了。”
“你說吧,我聽。”
程丹若看看手里的牌,十分狐疑:“你是不是要輸了,故意岔開話題?”
謝玄英把牌給看。
快贏了。
抿住角。
謝玄英扔掉牙牌,佯嘆口氣:“我就是故意岔開的,什麼都瞞不過你。”
“你不是快贏了?”才不信。
“可我想你贏。”謝玄英坐到邊,擁懷,“我舍不得你輸。”
程丹若繃不住了:“一兩銀子我還是輸得起的。”
去錢袋子,他收攏臂膀,不讓。
“放開。”推他的。
謝玄英任由,始終不肯松手。
程丹若改捶他肩膀。無果。
再掐兩把手臂。未。
調戲完了,也累了,后仰靠在他懷里:“還打嗎?”
“想抱你一會兒。”他道,“丹娘,今年是第三年了。”
程丹若“嗯”了聲。
“最近我一直在想,人有太多做不到的事。但和你一起守歲,我做到了。”謝玄英闔上眼,以的溫度,頸間的脈搏,“我們這樣到老,好不好?”
程丹若問:“你不會厭倦嗎?”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有人喜新厭舊。”他道,“人又不是件,件會過時變舊,人卻無時無刻不在變
。你我是同在江上泛舟的人,彼此依靠支撐,若剩我一個人,不免孤寂又畏懼。”
程丹若低下頭,他的手指搭在的上,修長白皙,手背淌過青的河流,靜默無聲。
輕輕按住他的靜脈,忽然說:“佳人拾翠春相問。”
“仙同舟晚更移。”他接上后半句,倏地記起舊事,“你可記得,當初大宗伯帶王五去老師家,我們聯詩。”
程丹若:“……記得。”
絞盡腦想牡丹,想的懷疑人生。
然而,謝玄英牢記的卻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是另一事:“你朝王五笑了多次,對我視若無睹。”
程丹若扭頭,懷疑耳朵:“我朝王五笑?對你視若無睹?”
他吐字清晰:“是。”
“有嗎?”滿心迷茫,完全不記得這一茬了。
謝玄英道:“你不看我。”
:“呃。”
“我一直在幫你,你眼里卻只有別人。”
程丹若有點相信了,和王五相親的時候,確實打量過對方:“我就隨便看看。”
謝玄英:“為何不看我?”
只好轉過,面對面瞧著他:“看你,我現在就看你。”
再說下去,一會兒吃餛飩,都不用蘸醋了。
但看他似乎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今夜守歲,燭燈點得格外明亮,燭火暈朦朧,他斜靠在長條枕上,白的中外頭,只穿一件薄羊絨,面容和得不可思議。
不自地手,他的臉龐。
他現在,可真像一個男朋友啊。
窗外,竹聲響,新歲又至。
泰平二十二年,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063 章

亡後歸來
重重波瀾詭秘,步步陰謀毒計。她,獨一無二的狠辣亡後,發誓要這天下易主,江山改姓;他,腹黑妖孽的傾世宦官,揹負驚天秘密,陪卿覆手乾坤。她問:“玉璿璣,我要的天下你敢給嗎?”他回:“蘇緋色,你敢覬覦,本督就敢成全。”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縱觀天下,捨我其誰!
396.7萬字8 13509 -
完結503 章

重生之請妻入甕
聽聞鎮國將軍府,老將軍年老多病,小將軍頑疾纏身。作為一個不受待見的公主燕卿卿,兩眼發亮,風風火火的主動請求下嫁。本是抱著耗死老的,熬死小的,當個坐擁家財萬貫的富貴婆的遠大理想出嫁。不曾想,那傳聞中奄奄一息的裴殊小將軍化身閻王爺。百般***還…
77.7萬字8 29843 -
完結315 章

女扮男裝的男主她玩脫了
祁懿美穿成了最近看的一部權謀文中的……男主。 哦,還是女扮男裝的 眼看劇情要按權謀主線發展,為了讓自己這個權謀小白好好的茍到大結局,祁懿美果斷決定逃離主線,卻機緣巧合成了病美人六皇子的伴讀 從此她便和他綁定了,還被人們編成了CP,被滿京城
51.7萬字8.18 4709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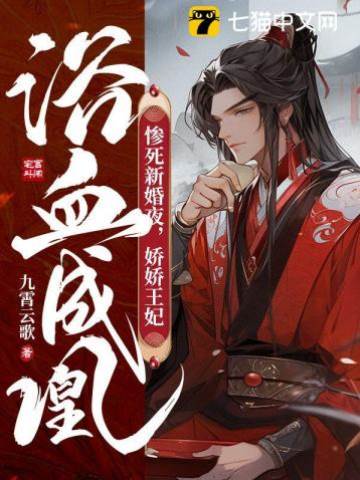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