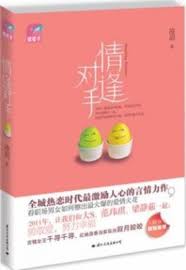《無人區玫瑰 (老白兔)》 第077章
他去臉上的淚,解開安全帶,彎腰把抱出來。
白瀅本來就發著燒,這麼一哭上的溫度更燙了。
醫生開了退燒藥片,叮囑白瀅好好休息,也別有這麼大的心浮。
裴晉知道是自己錯了,白瀅從小就哭,膽子也小,他又不是不知道。當時那些緒不由自主的竄上來,他沒忍住,是自己心境不夠。他無意嚇著,更不忍心把弄哭,總之以后不會了。
白瀅臥在床上不停咳嗦,燒還沒退,渾熱得出汗。
裴晉進來的時候,兩條胳膊都耷拉在被子外面,口一起一伏,呼吸有些。
測了測溫,還是老樣子。
裴晉今晚不打算睡了,白瀅要是還不見好,只能去醫院做個全面檢查。
他把在外面的兩條胳膊放進被子,白瀅皺皺眉,立刻又了出來,不滿地嘟囔:“好熱……”
白瀅現在滿是汗,覺睡都了,難的不得了。
裴晉著聲音安:“發熱出汗說明發燒癥狀正在緩解,一會兒起來喝點溫水,讓汗繼續排出來。”
聽到他的聲音,白瀅微微睜開眼。
裴晉就坐在床頭邊,俯著子給汗。
白瀅撇開了臉:“別靠我太近,我怕把冒傳染給你。”
裴晉抿不語,只是繼續默默照顧著。
白瀅沒力氣再跟他說話,閉著眼睛半昏半醒,周圍靜得無聲,時間也淌得很慢。
Advertisement
凌晨五點。
裴晉再次給白瀅測了溫,三十六度八。
燒退了。
他離開房間,倒了杯水,站在窗口著還陷在黑夜中的城市。
白瀅輟學那天也發燒了,他記得見到時,也在哭,眼睛和臉頰都紅紅的。
他帶去了醫院,深夜的輸室里人還是很多,就在小小的角落,一直低著頭流眼淚。
那次,是因為段博煬。這次,是因為江月笙。
好像總是為別的男人傷心,他好像又總是只能這樣看著難過。
他點了煙,心里有些煩。
第二天,白瀅醒來時覺好多了。
傭端了杯溫水進來,扶著先去衛生間洗漱。
回來的時候,發現裴晉的手機在床頭柜上。
傭說:“應該是裴先生不小心落下的,裴先生昨晚一直在這兒守著。”
白瀅喝了口溫水潤,若有所思。
其實裴晉實在不必這樣親自照顧的,甚至覺得,裴晉的界線……有些過了。
且不說他們已經有幾年沒見面,就算他們是表兄妹,那也只是明面上的。當年舅媽嫁給舅舅的時候邊就已經帶著他,所以白瀅跟他是親戚,卻沒有實質的緣關系。有心把他當作哥哥,可這幾天的相,尤其是昨晚,還是覺得不太應該。
白瀅還是打算走了,等不到裴晉從公司回來,只是簡單的讓傭幫忙轉告一下。
Advertisement
沒想到剛出門沒幾步,裴晉就從外面回來了。
車橫在白瀅面前,他從車里出來,冷冷的目盯著:“你要去哪兒?”
他是回來拿手機的,沒想到恰巧到了這一遭。
只離開別墅,除了要走,還能是什麼。
白瀅看到他,心里怔了怔。
老實說,還是怕的。一是沒那麼悉,二是他那張臉雖然好看但也生得冷厲。
每次見著他,都會不自覺的油然生畏。
“表哥,打擾你兩天了,我該走了。”
白瀅聲音輕輕的,眼神不敢一直看著他,只是快速的掠過。
裴晉邁開長向走近,站立在跟前,居高臨下的瞧著那張病態憔悴的臉。
他沉默了許久,問:“白瀅,你討厭我麼?”
白瀅愣了一下,他怎麼會突然這麼說。
老實回答:“當然沒有,怎麼會討厭呢。”
裴晉又問:“那你為什麼見到我,總是那麼疏離。”
白瀅抿了抿,這要怎麼說,其中夾雜的東西那麼多,一時半會兒也說不清楚。
思索間,裴晉手握上的胳膊,將帶回別墅:“你昨天發燒,也有我的緣故。我不該在你病還沒好的況下,帶你去吹風。醫生很快就過來了,你還是別跑了。”
白瀅猶豫:“我一直住在這兒,終歸不好。”裴晉:“自家哥哥怕什麼。”
白瀅看著走在前面的裴晉,著他的背影,揣他的那句話。
Advertisement
所以……他也只是把當作妹妹,在做認為哥哥應該做的事,是吧?
也許真是自己想多了,這樣的,怎麼會是裴晉的菜。
白瀅這下輕松多了。
裴晉等醫生來,親眼盯著白瀅掛上點滴,這才放心離開。
白瀅退燒之后,今天沒有復發,只是嚨還腫的難,也咳得厲害。
下午,吃過藥后迷迷糊糊在房里睡著,忽然聽到有人上樓的聲音。
不是傭,也不是裴晉,是人踩著高跟鞋的腳步聲。
半醒過來,聽到有人打開了房間,但是沒進來,之后又關上了。瞇著眼,眼皮沉得厲害,最后又睡過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撩人幾許不自知
【霸總忠犬vs清冷醋壇,酥甜撩人,先婚后愛】 商界合伙人夫婦,表面舉案齊眉,背地里各玩各的。 你有你的白月光,我有我的舊情人。 總裁被爆八卦緋聞,夫人熱情提供高清側臉照。 總裁找上門求打架,夫人沉迷事業甩手閉門羹。 雙向暗戀,卻一朝夢碎,兩人在深愛上對方的時候簽下離婚協議。 夫人另嫁他人做新娘,大婚當日,陰謀揭露。 江映月:你是來復仇的嗎? 沈聽瀾:我是來搶親的。 江映月:我們已經離婚了。 沈聽瀾:我把心都給你,只要你繼續愛我。
43.9萬字8 10653 -
完結2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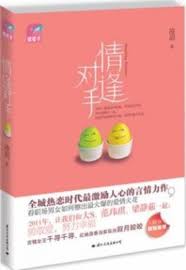
情逢對手
我們兩個,始終沒有愛的一樣深,等等我,讓我努力追上你
55.5萬字8.18 4086 -
完結99 章

天鵝頸
南城歌劇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舞臺上的今兮吸引—— 女生腰肢纖細,身材曲線窈窕,聚光燈照在她的臉上,眼波流轉之間,瀲灩生姿。 她美到連身上穿着的一襲紅裙都黯然失色。 容貌無法複製,但穿着可以,於是有人問今兮,那天的裙子是在哪裏買的。 今兮搖頭:“抱歉,我不知道。” 她轉身離開,到家後,看着垃圾桶裏被撕碎的裙子,以及始作俑者。 今兮:“你賠我裙子。” 話音落下,賀司珩俯身過來,聲線沉沉:“你的裙子不都是我買的?” 她笑:“也都是你撕壞的。” —— 賀司珩清心寡慾,沒什麼想要的,遇到今兮後,他想做兩件事—— 1.看她臉紅。 2.讓她眼紅。 到後來,他抱着她,吻過她雪白的天鵝頸,看她臉紅又眼紅,他終於還是得償所願。
31.2萬字8.18 32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