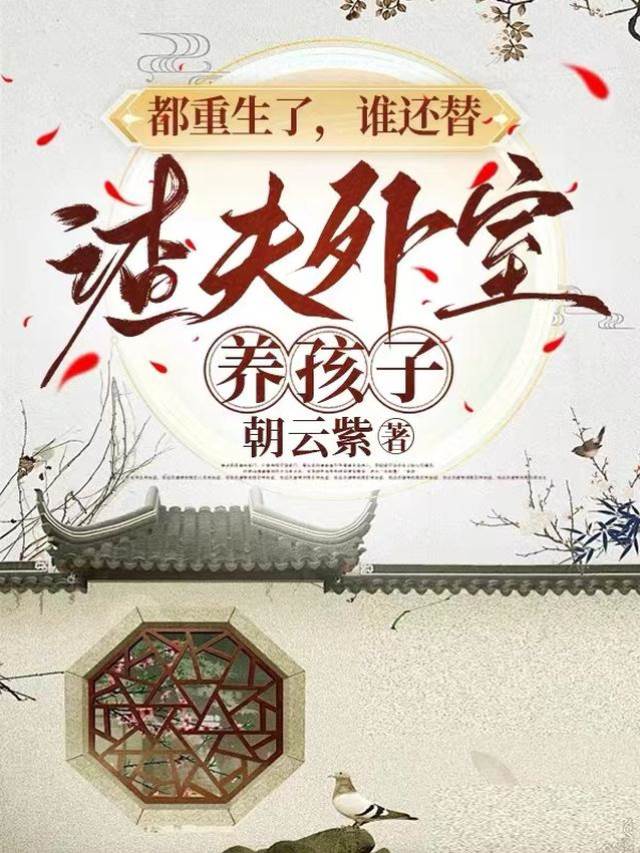《將軍榻上》 第192章 我要帶她回家
卿言第一個罵出聲來:“放什麽狗屁!”
煬卻了解謝柬之的手段,所謂火燒大菩提寺,當然是假話,但這可以被做真事。
說到底正史都由勝者書寫,隻要把知道真相的人都殺,想怎麽說就怎麽說。
他擰了眉:“謝柬之,都城之你都敢玩這一套?”
謝柬之直視他,冷靜道:“都城之,我敢玩這一套。”
煬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
他轉向卿言,“嶽母,這事兒有陛下默許。”
聽他這話,卿言思緒流轉。
當年北征,所率軍隊原是勢如破竹,直到關鍵一戰,呼延氏鐵騎卻事先知悉戰略部署。
那一戰正是因此敗退。
後撤時,有個將士策馬向靠近。
原本以為此人隻是想要活命,直到那將士向揮起了長劍。
這個將士,是梁帝引薦的。
那一瞬卿言難以置信。
後來在北方消磨了太多歲月,如此漫長,幾乎淡忘了這些細節。
回到綏都之後,又漸漸地意識到,梁帝對當真是心存芥。
隻是不論如何都想不到,梁帝會做到這一步。
啐了一聲:“當初就不該扶持他做皇帝。要我的命,好歹也自己現,和我說明白。隻敢玩這些把戲和手段,真像隻臭水裏的老鼠。”
“你們總歸要死,隻是早晚罷了。”胡平伯咳了一聲,道。
謝柬之接上,道:“北上議和使臣今日已回到都城,他帶回了呼延王的要求。你們活不。”
卿言皺了一下眉頭。
卿令儀和煬對視了眼。
“不多廢話了。”謝柬之耐心不多,也覺得拖得越久越多變數。
他看了一眼謝弗。
謝弗會意,舉起手中兵,“所有人,聽我號令!”
這邊,卿言提起了十二分的神,頭也不轉對煬道:“你保護好嗯嗯,其他我都能理好。”
Advertisement
“明白。”煬握住了卿令儀的手。
卿令儀不自覺地上小腹。
許廉、吳量等人拔出了各自的兵。
雙方劍拔弩張,殺氣愈演愈濃。天邊黑雲翻卷,悶雷聲響更近,仿佛就在頭頂往下。
卿令儀歎氣,今日這場鬧劇什麽時候能結束呢。
謝弗高聲:“上!格殺勿論!”
“且慢!”
淩空傳來更為響亮的聲音。
謝弗一愣,扭頭看去,“匡大人?”
匡金雪正策馬趕來。
謝柬之不顧一切,直接道:“不必管他,手!”
他先行作,拔出旁邊將士腰上佩劍,刺向煬所在方向。
“小心!”卿令儀驚呼一聲,下意識地要為他擋這一劍。
“別怕。”煬嗓音低沉,帶著令人心安的力量。
他輕攬過卿令儀的腰肢,將輕輕往後一帶,又說:“等我一下。”
言罷,他向前踏出一步,足尖踢中劍刃,強力將劍震開,連帶著謝柬之的手臂也歪了。
而他短暫鬆開卿令儀,扣住謝柬之手腕,握住劍柄搶奪,調轉劍尖,對準了謝柬之的嚨。
謝柬之定住。
煬挑了眉:“家裏棺材備好了,迫不及待想用上?”
匡金雪終於趕到,急聲道:“陛下有令,不可妄!”
看來,梁帝這是放棄了對煬、卿言的圍剿。
“陛下究竟是什麽意思?”謝柬之不甘心問。
“使臣已宮,”匡金雪道,“陛下即刻便要召見將軍、卿將軍,以及夫人。”
三人一同側目。
“轟隆!”
雷聲滾滾。
匡金雪道:“正好要下雨了,請隨我宮去吧。”
煬沒,也沒回話。
直到卿言冷哼一聲,道:“那就去一趟。”
煬這才收了劍。
這劍一般,手很差。煬嫌棄地丟開,轉去牽卿令儀。
乖乖地留在原地,向他的所在。
Advertisement
煬心中一片。
他剛走近,眼角餘忽地瞥見一道影,正靠近卿令儀,著的是右衛軍裝,手中握著的卻是一把匕首。
“謝嫻!”
煬認出,發出怒喝。
謝嫻卻不回頭,反而加兩步,匕首正對著卿令儀突進,同時兇狠詛咒:“你去死吧!”
煬、卿言,以及吳量、司汝劍、許廉、陸……都立刻奔向卿令儀。
卿令儀也很快反應過來,警惕地轉後退。
“轟隆!”
雷聲再至,這回伴著閃電劈下。
亮過於刺目,卿令儀閉了閉眼。
待再睜開,謝嫻已倒在地上,渾軍裝焦黑,仍彌漫著一黑氣。臉上戴的麵裂作兩半,出了那張猙獰、醜陋的麵孔。
但離那麽近的卿令儀卻安然無恙,甚至連擺都沒染上一塵埃。
“小嫻!”
謝柬之淒慘喚聲,撲了上去。
沒人阻攔他。
他終於親眼見到了自己的兒,也明白過來,卿言真的沒有殺。
·
大菩提寺。
烏勒宗挈與法藏大師並肩而立,將這一幕盡收眼底。
烏勒宗挈一派自豪,“這個,我侄。”
法藏大師須發盡白,年邁滄桑,此刻雙手合十,發出長歎:“老衲雖曾天命召,得知有祥瑞之降世。今日終得見真了。”
“這麽些年,你一直相信祥瑞之這種話?”烏勒宗挈笑了。
“堅信不疑,”法藏道,“得此祥瑞之,可保國運百年昌盛。”
他轉過頭,“施主,你來綏都,便是為了這祥瑞之罷?”
烏勒宗挈卻搖頭,“我們不信這個。我來,隻是因為是我親侄。我要帶回家。”
·
明德殿。
梁帝很多年沒有這麽張心虛,他坐在書桌前,心口跳得很快。他拿起奏章,卻發現手指得厲害。
Advertisement
梁帝閉上眼睛,迫使自己鎮定下來。
他是皇帝,他可是皇帝!
“陛下。”
匡金雪的聲音。
梁帝忙睜眼,匡金雪稟報:“將軍、卿大將軍,還有夫人,都到了。”
梁帝向三人。
煬牽著卿令儀的手,懶洋洋的。卿言臉不善,明顯按捺著怒火。
梁帝清下嚨,道:“匡金雪,去搬椅子來。”
已有好些年,大梁的臣子在皇帝麵前隻能站著。這是罕見的禮遇。
煬扶著卿令儀坐下。
卿言卻仍站著,直截了當道:“究竟什麽事,陛下還是直說吧。”
梁帝幹笑兩聲,道:“言妹,這些年大梁與民生息,百姓好容易有了如今安生日子,我是為百姓考慮,才不願打仗。”
卿言敷衍地點頭,“我明白,我都明白。”
“我派去北方的使臣已回來了,”梁帝看了一眼卿令儀,試探道,“呼延王提了要求。”
卿言沒好氣道,“他想我去北方,待在他邊,是吧?”
梁帝頓了一下。
他撓了撓頭,“其實……他說的是……讓令儀去北方。”
卿言:?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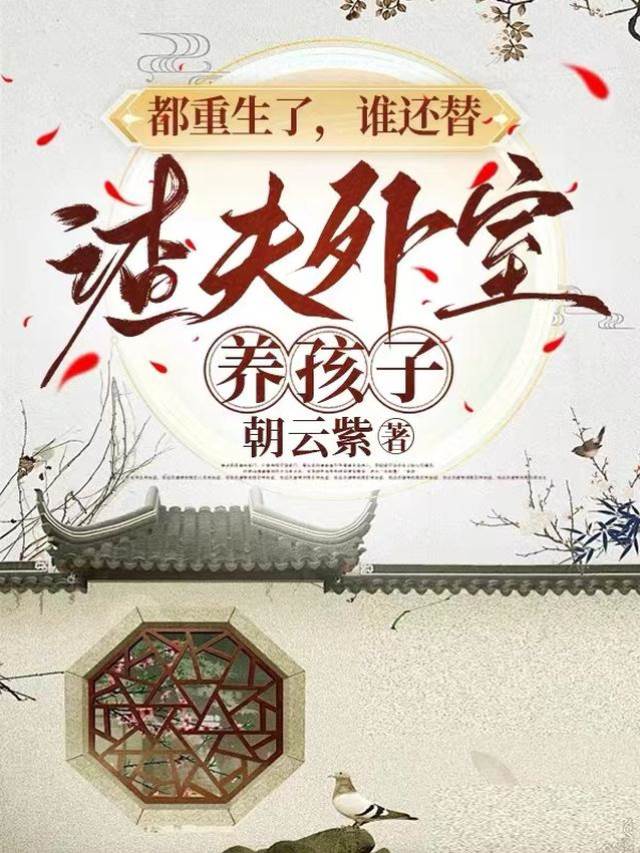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