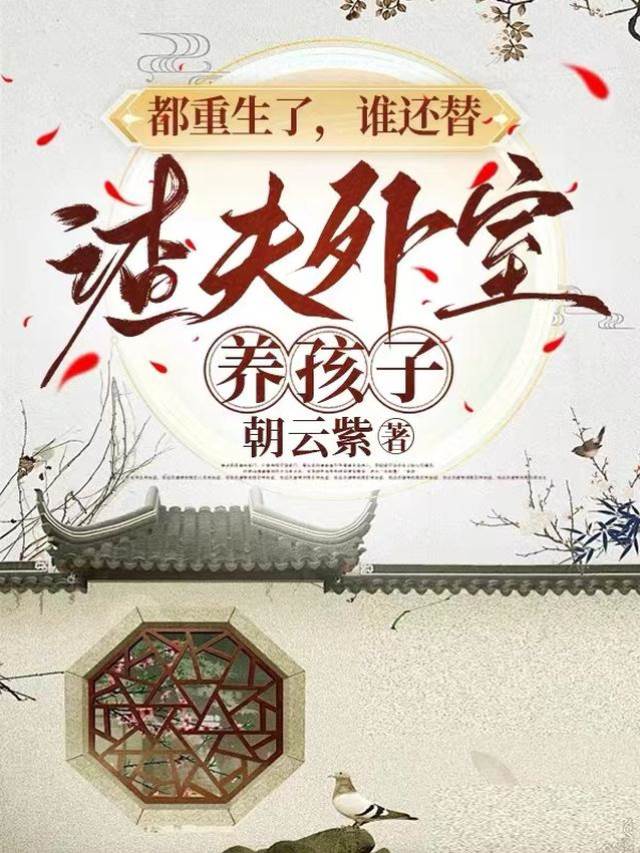《夫人讀心術失靈,小侯爺日日邀寵》 第136章 他氣狠了她
奚挽君抓上藤蔓,往上爬,可袖子料被鱷魚死死咬住,鱷魚猛地一甩頭,奚挽君被輕而易舉拽回了鱷魚池,手臂流出的蔓延開來。
“挽君!”趙明詩四搜尋有無稱手的東西,其餘幾個黑人見在岸邊徘徊,又要將推回池塘裏。
方才被奚挽君帶下來的黑人很快被啃得隻剩下半邊,幾隻鱷魚嗅到了新鮮的,擺著尾朝奚挽君飛速遊過來。
奚挽君本避讓不開,撲麵一道極腥的臭味襲過來,鱷魚銳利的尖牙下一刻好似要粘到的皮。
“砰——”
一棵樹幹倏然倒下,正中幾隻鱷魚的頭頂,水麵激起一大波水花漣漪,奚挽君生生嗆了數口水,眼看就要往下沉。
又是一道水花聲,腰上一沉,有人攔腰將從池底撈了上來。
吐出一口水來,眼眶又酸又漲,恍若方才的腥臭味還縈繞在周圍,下意識幹嘔了兩下。
扶著後背的手掌微頓,轉而輕輕拍了兩下。
“先生!”
年人的嗓音將的意識逐漸拉了回來。
眼前的鐵皮麵轉了過去,隔著麵都能到此人上的冷桀之氣。
“先生,我……”
免先生將奚挽君扶了起來,幾個黑人連忙扯住年,“主子,快走,東宮的親兵來了。”
免先生瓣微,“走。”
年頷首,“先生也快跟上。”
奚挽君被男人扶著,忍不住去觀察這個人,臉上雖然戴了麵,鬆散的襟顯現出鎖骨上一顆極淡的小紅痣。
“阿遠,人在這兒!”
趙亦寒從林外跑了進來,見奚挽君被人挾持,高喝了一聲:“你是誰!快鬆開!”
桑渡遠飛快跑了進來,上沾滿了泥濘,風塵仆仆,見奚挽君被一個男人半扶半抱著,漆黑的瞳孔裏全是冷意看,拔出長劍便急速劈了過來。
Advertisement
奚挽君覺腰上一道推力,自己還來不及反應,就已經摔了出去。
桑渡遠拔出的劍刃急轉方向,接下了撲過來的子。
他視線再抬,奚挽君後的人踩過樹幹,躍到了鱷魚池對麵,影飛快匿在林。
“阿遠……”奚挽君力被幹,一不盯著突然出現的桑渡遠,心裏不由有些恐慌。
“……”
桑渡遠卻沒說話,掃了一眼,滿臉疏冷,毫無溫度地將抱了起來,往林外大步走去。
李逢生也正好跑了過來,看了眼桑渡遠和,隨即朝趙明詩的方向跑了過去,“沒事吧?”
趙明詩捂著屁,指著方才免先生離開的方向,急忙道:“方才就是那個人抓了我們,他背後好像還有個什麽主子,是個年,一夥人都往那邊逃了。”
李逢生見渾狼狽,先拽起檢查了一番,“這件事不用你管,底下的人會去查,有哪兒傷了嗎?”
趙明詩搖頭,又往桑渡遠離開的方向看了過去,“我倒是沒有傷,就是不知道弟妹怎麽樣。”
另一邊,奚挽君還在同桑渡遠說方才的年人和免先生上的疑點,對方一言不發將放在了馬車上,轉就要離開。
“阿遠。”
奚挽君察覺他緒不對,“阿遠,怎麽了?”
桑渡遠麵上表很淡,“我去查方才那夥人。”
“那、那我呢?”奚挽君心裏有些張,這才意識到他生氣了。
“你不是很習慣獨立獨行嗎?待會兒自己回去。”他掀開馬車簾就要下車。
一把扯住他,“阿遠,我…我……”
他冷冷掃了眼,“鬆手。”
的聲音很小:“我傷了。”
他眉心皺了起來,目凝在上打量了個遍,看到將手藏在了後,一把扯了過來。
Advertisement
“嘶。”疼得氣了聲,桑渡遠將的袖子一把掀開,白的手臂底下約莫劃開了一指長的口子,約出一小截白翻了出來,看上去目驚心。
桑渡遠眸極沉,聲音驟然放大,帶著怒意:“傷了怎麽不說?”
被嚇了一跳,往後了下,“我…我方才怕你生氣,我才……”
他咬牙關,對外喝道:“回桑家。”
車夫忙駛馬車,快速往城奔過去,一路上風塵卷軸,車外景一個個從奚挽君眼前飛快閃,心底越發不安。
【他這一次,是真的生氣了。】
【要怎麽跟他解釋才好……】
【要麽說我不是故意的呢?他肯定不相信。】
桑渡遠的麵部繃得很,一不盯著窗外,沒有回頭看一眼。
【一眼都不看我,他一定是氣瘋了……】
【怎麽辦啊……】
【這件事的確是我做錯了,讓他擔心了。】
【可是我也傷了…好痛哇……】
【他怎麽都不問問我難不難。】
【平常他肯定要關心我,這一次什麽話都不跟我說了。】
“阿遠……”試探地開口,哪知馬車正好停下,桑渡遠開簾子就往外走,連忙起追上去。
“阿遠。”
剛出馬車,就發現桑渡遠還站在原地,睨著,一把攬過的腰打橫抱起往春歸院裏走。
汪媽媽和北晞見回來了,本想要進來,但桑渡遠上散發出的氣場實在嚇人,們也隻好站在了屋外等候。
剛屋,奚挽君就被桑渡遠扔在床上,作冰冷,毫沒有往日的關切。
他開的袖子,目又定在了傷口上片刻,直到大焱端來的藥和紗布,他才恢複了作,用剪子把袖子剪開,毫不猶疑將藥灑在了傷口上。
Advertisement
“嘶。”
“好痛……”
奚挽君委屈地抬起眼,哪知對方本不與對視,撒完藥後,將紗布一層層卷到的傷口上包裹住。
“阿遠,你怎麽不說話……”
“……”
桑渡遠冷著臉,一個字都沒說。
大焱見狀也不敢開口,看了眼奚挽君後,飛快退出去。
“阿遠,你上有點髒了,要不我讓北晞們去燒水,讓你洗洗吧。”
瞧他麵龐上沾滿泥濘,上也髒兮兮的,一看就是為了尋找才狼狽這樣,心疼地從一邊拿過幹淨的帕子往他臉上。
哪知桑渡遠剛到帕子就將臉冷漠地別開,好似比臉上的泥還要更讓人嫌棄。
“阿遠,我沒事的,這傷口是不小心跌進那池子裏弄的,隻是看著嚇人,很快就好了的。”忍著痛,小心地討好他。
可這人包紮完傷口也不停留,將髒了的袍子在架上,重新換上一幹淨裳,就往門外走出去。
急得連忙道:“桑渡遠!”
他的腳步頓了下,沒有回過頭。
“我傷了,你要去哪兒?”
“去查人。”他餘微,毫沒有流出容,“等會兒會有大夫過來,我留在這兒對你的傷勢沒有幫助,
反正對你而言,我不是可有可無的嗎?”
“……”
整個人都怔了下,張了好幾次都說不出話來。
桑渡遠沒有聽到屋還有聲音傳來,腳步一邁又離開了春歸院。
奚挽君失神地盯著自己手上的傷口,恍若還到他掌心傷口時的微微發。
“夫人!”汪媽媽一進來就瞧見的傷口,驚慌失措地對北晞道:“快去大夫。”
“不用。”大焱連忙道:“大夫已經在趕來的路上了。”
奚挽君緩了緩,掉眼角的意,對二人道:“先燒水吧,我現在太狼狽了,還是沐浴過後再見人,免得等會兒大夫來了見著不好。”
Advertisement
現在好歹是桑家掌事的,代表的是桑家的臉麵,讓人看到難堪的模樣,傳出去指不定會又興起什麽流言蜚語。
……
大夫看過傷口,開了藥方,叮囑奚挽君按時服藥,以免傷口發炎,正好卿扶和老夫人來了,詢問起奚挽君是怎麽傷的。
奚挽君朝二人笑了下,“沒什麽事。”
轉而,又吩咐汪媽媽將大夫送了出去。
老夫人見狀猜出了況不對勁,追究底道:“怎麽了挽君?是不是遇到什麽事了?”
卿扶也正道:“挽君你遇到什麽事了?不用怕,母親幫你解決,我現在就去那臭小子回來。”
“不用了母親。”奚挽君不能讓兩位長輩擔憂,忙道:“也不是什麽大事,隻是我與明詩郡主約著出去遊玩時起了口角,我不慎摔了一跟頭,手才劃了這樣。
方才我讓汪媽媽將大夫送出去,也是覺得這事兒說出來醜人,影響咱們桑家的形象。”
這番說辭倒是沒什麽問題,老夫人也半信半疑,隻能叮囑:“你若到了什麽事兒一定要同我們說,就算是天塌下來了,還有祖母這把老骨頭頂著。”
奚挽君鼻頭有些發酸,笑了笑:“能有什麽事兒,不過是姐妹出遊起了點口角,同你們說出來,我都覺得有些害臊。
隻是過兩日便是二叔和孫家姑娘的喜宴,帖子都還沒送出去,我這了傷,恐怕要害得祖母和母親替我分憂了。”
“你不用擔心這個。”卿扶了下的腦袋,端著的手臂看了一會兒,心疼地歎了口氣:“家裏的事,有我們勞,你正好歇一歇。”
送走兩位長輩,奚挽君找來北晞了解了今日去找桑渡遠後發生的狀況。
知道桑渡遠是為了找急壞了,方才這人扔下那句話就離開,應當隻是賭氣之舉。
他心裏是氣狠了。
可如今桑渡遠出去了,也隻能煎熬地等待這人回來再給他賠禮道歉。
哪知道一等,竟然等到了深夜。
“夫人,姑爺回來了。”
北晞見到男人往春歸院這邊過來,連忙進屋向奚挽君稟報。
連忙從床上坐了起來,隻是等了半晌,卻沒等到桑渡遠進屋。
北晞察覺不對,連忙又出去打探況,又過了片刻,才一臉複雜回了屋。
猜你喜歡
-
完結232 章
腹黑郡王妃
一覺睡醒,狡詐,腹黑的沈璃雪莫名其妙魂穿成相府千金.嫡女?不受寵?無妨,她向來隨遇而安.可週圍的親人居然個個心狠手辣,時時暗算她. 她向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自動送上門來討打,休怪她手下不留人:姨娘狠毒刁難,送她去逛黃泉.繼母心狠手辣,讓她腦袋開花.庶妹設計陷害,讓她沒臉見人.嫡妹要搶未婚夫,妙計讓她成怨婦.這廂處理著敵人,那廂又冒出事情煩心.昔日的花花公子對天許諾,願捨棄大片森林,溺水三千,只取她這一瓢飲.往日的敵人表白,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心,她纔是他最愛的人…
155.2萬字5 59507 -
完結752 章

盛世凰歌
擁有精神力異能的末世神醫鳳青梧,一朝穿越亂葬崗。 開局一根針,存活全靠拼。 欺她癡傻要她命,孩子喂狗薄席裹屍?鳳青梧雙眸微瞇,左手金針右手異能,勢要將這天踏破! 風華絕代、步步生蓮,曾經的傻子一朝翻身,天下都要為她而傾倒。 從棺材里鑽出來的男人懷抱乖巧奶娃,倚牆邪魅一笑:「王妃救人我遞針,王妃坑人我挖坑,王妃殺人我埋屍」 「你要什麼?」 「我要你」
132.9萬字8 10928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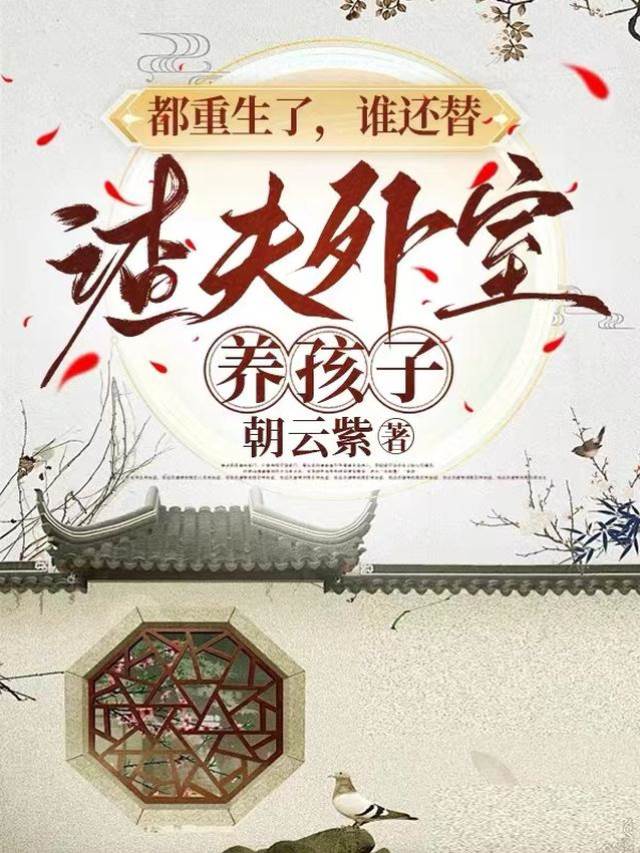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