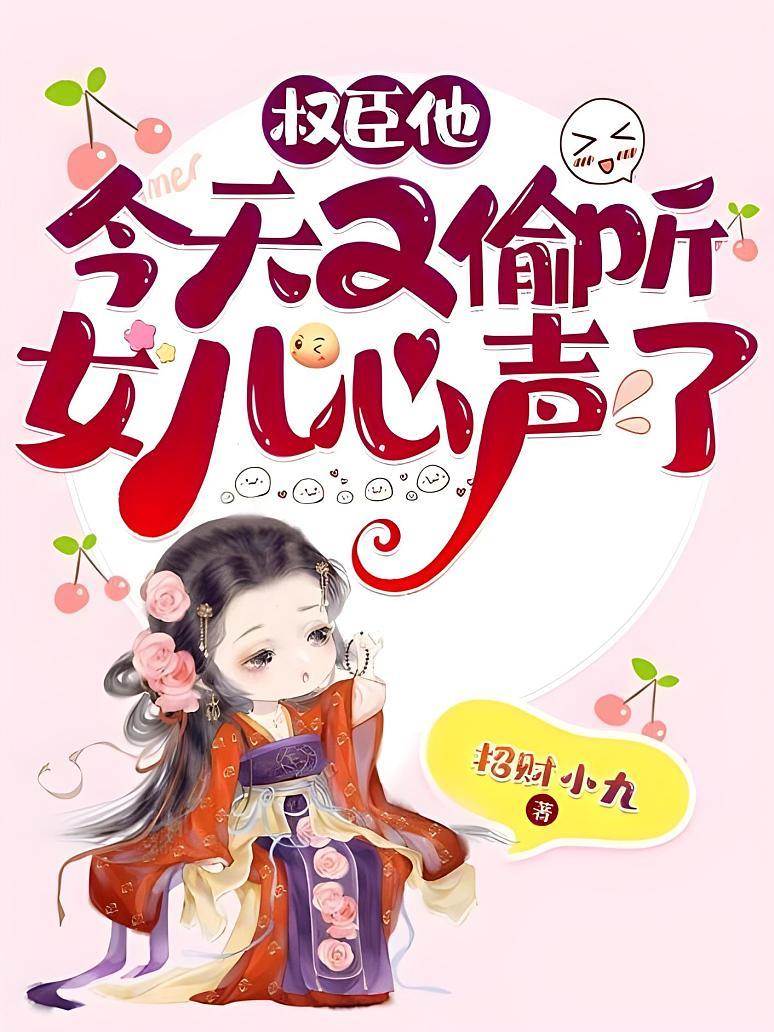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夫人讀心術失靈,小侯爺日日邀寵》 第192章 他不會輸
奚挽君咽了咽唾沫,不讓自己掉桑渡遠的陷阱,“不如,咱們玩個更有意思的?”
桑渡遠挑眉,笑得意味深長:“寶寶,你現在都會別的玩法了?”
臉熱道:“還真有個不同的玩法。”
“……”
“……”
“……”
“你說的新玩法,就是下棋?”
桑渡遠著奚挽君擺好的棋盤,久久無法回過神。
“下棋可以靜心。”
奚挽君頷首,一臉期待道:“而且咱們婚這麽久,也還沒有下過棋。”
桑渡遠看著子眨眨眼,想要欺負又於心不忍了,隻好生生咽下這口氣。
“好吧,勉強陪你下一局。”
奚挽君彎起,執黑子落於盤中心,桑渡遠執白子,也隨其後。
“原來你會下棋,我之前都以為你不會呢。”
桑渡遠險些白一眼,“我之前隻是個紈絝子,又不是個什麽都不懂的廢。”
奚挽君莞爾一笑,邊下邊道:“你想好了嗎?若是廣順王不應,該如何是好?”
“不應又如何。”桑渡遠神專注,“咱們雖然是去搬救兵,但也不代表全依仗著廣順王了。
就算他不出援手,我和趙亦寒也會背水一戰。”
奚挽君輕輕嗯了聲:“那你有沒有想過,燕王和韓王一直都不對付,上一次卻聯手起來對付太子,這一次,若是他們聯手了該如何是好?”
桑渡遠指尖一頓,緩緩看向,“阿奚的意思是,擔心燕王和韓王聯手將太子先滅了,再一決高低?”
奚挽君沒有急著回答,語氣溫和:“倒不是說,燕王和韓王一定會聯手,隻是人行事前,總要預料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
爭皇位是這樣,打仗也是這樣,咱們不能等別人羽翼滿了,再未雨綢繆,那就已然是沒有還手的餘地了。”
Advertisement
見桑渡遠沉默下來,執起黑子繼續道:“阿遠,你知不知道,為什麽我在奚家這麽多年都謹小慎微,嫁到了桑家後,我可以與他們正麵較量,甚至讓他們不敢欺辱我半分。”
桑渡遠靜靜地看著,連手中的棋都忘了下。
“世人都以為奚家大姑娘溫懦弱,沒有自己的主見,但這並不是我真正的子。”
條理清晰,一點點將這其中的道理剝,說與他聽:“我忍辱負重這些年,是因為我手裏的籌碼不夠,所以我不敢也不能有自己的主見。
其一嫁給了你,是你和桑家給了我這份底氣,你讓我手上有了籌碼。
其二,我有了絕英閣,生意越來越好,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底氣和籌碼。
手裏有了籌碼,我自然就強起來了,對方看到我強,自然也不敢踩在我頭上。
就比如藺羨之先前一直覬覦我手裏的絕英閣,但是後來我嫁進了桑家,他知道無,便轉頭尋了鬱家這座靠山。”
桑渡遠聽得很認真,“你的意思是,一定得讓咱們手裏有籌碼,燕王和韓王才不能來犯。”
“不。”
“阿遠,如今的狀況不同了,就算咱們手裏沒有籌碼,也一定得裝作有籌碼的樣子。”
奚挽君將最後一顆棋子落下,抬起臉來,嚴肅道:“一定不能讓燕王和韓王一條心,否則咱們絕對沒有翻的餘地,亦會讓百姓們遭殃,生靈塗炭。
盡可能地讓他們離心,這樣咱們才有可趁之機。”
桑渡遠眉心一,“讓他們離心?”
“是,這也是你們現在需要著手準備的。”
桑渡遠垂下眼,視線落在棋盤上,頓了頓,“我輸了。”
他手腕忽然一。
奚挽君著他,一字一頓:“你不會輸。”
……
Advertisement
日落西山,馬車經停雲夢澤,眾人都疲乏了,便在周圍紮了營,休息片刻。
桑渡遠下車的時候便找趙亦寒說話,想來是傳遞奚挽君的意思。
趙明詩下車氣,喊上了奚挽君和孫由來湖邊看景。
“坐在車上可太悶了。”
趙明詩吐出一口氣,“還是看風景好。”
“你不喜歡和你的李校尉待在一起?”孫由調侃。
“待在一起是好,但是看得見,不著,怪饞人的。”趙明詩托著臉,滿臉笑意。
孫由嘖了兩聲:“的酸臭味都快熏死我了。”
奚挽君飽含深意看了看孫由,“這位姑娘,我聽說你本來是跟曹姑娘一個車,後來怎麽換了表兄了?”
孫由誒了聲,“可別把帽子扣到我頭上,又不是我想跟你們太子爺坐,是曹姑娘說你舅舅來潭州車馬勞累,騎馬有損力,所以才把我趕下去了,讓你舅坐上來。
那我總得找個人收留我吧,你們這一對對的,難不我還來找你們。”
奚挽君聞言眉心一,餘好像看見曹允南朝莊采黠的帳子去了。
“公子,喝些茶水吧。”
曹允南端著茶遞給莊采黠,默默坐在了他邊,“現在這個時節還要生火嗎?”
莊采黠坐在帳子外,一健碩的被玄勾勒得飽滿有致,火星子頻頻跳,臉龐被映襯得更為英俊,“如今夏末快秋了,早晚溫差大,便生了篝火,避野也能取暖。”
曹允南角微微陷進去,姣好的麵容被火烤的紅潤恬靜,聲:“公子常年征戰,見識多,允南在閨中待了許多年,倒讓公子見笑了。”
莊采黠連忙擺手,“我沒這個意思。”
曹允南看他如年郎一般驚慌失措,忍不住笑道:“我知道公子沒這個意思。”
Advertisement
莊采黠撓了下後腦勺,好奇道:“不過,曹姑娘,你為什麽要跟著我們一塊去江陵府?”
曹允南被問的一下忘了怎麽回答。
“我聽人說,哦不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是聽別人說。”莊采黠語氣小心:“你是不是喜歡桑渡遠啊?”
曹允南表一愣,想了想,坦誠道:“以前喜歡的。”
莊采黠沉了一聲,思考道:“曹姑娘,這幾日相下來,我覺得你人好的,又有學識,生的也…也漂亮。
桑渡遠和挽君親了,他這個人我多還是了解些,他不是三心二意的人,你若是將心思放在他上,大抵要白費神了。
我說這話沒別的意思,我是挽君的舅舅,談不上私心,但是你的年紀與挽君應當相仿,我也是將你看作侄一般,希你能將眼打開,世上的好男兒多了去了,何必在桑渡遠上浪費力。”
曹允南靜靜地聽他說話,打斷道:“公子,你誤會了,我前些日子過傷,你應該聽挽君說過吧?”
莊采黠木訥地點了下頭,注意力一下就岔開了,“你現在還難嗎?我這次來,也帶了個曾經用過的軍醫,要不讓他給你看看?”
“……”
曹允南歎了口氣:“公子,我在傷之前,就已經斷了對桑小侯爺的心思了,您不必因為擔心挽君而勸我。”
莊采黠:“噢……”
曹允南盯著他看了一會兒,又歎了口氣,起轉過去,又道:“我……”
“你?你咋了?”莊采黠不解。
曹允南咬著,餘瞥了眼反應力極慢的莊采黠,“我年紀比挽君大,擔不了你一聲侄。”
說著,便一個轉,正好撞上走過來的奚挽君。
“曹姑娘,你們在聊什麽呢?這麽出神,連我的腳步聲都沒聽見。”奚挽君的目落在了麵頰稍燙的曹允南上,不遠的莊采黠也是一臉懵。
Advertisement
“……”曹允南回頭看了眼莊采黠,言又止。
“喲!”
趙亦寒剛好從帳子裏出來,指著曹允南道:“曹姑娘,你今日這胭脂好看的。”
曹允南聞言,將臉別開了些。
趙亦寒好奇追問道:“你這是在絕英閣買的胭脂嗎?”
“問這麽多幹什麽?你改變了喜好?喜歡塗胭脂了?”孫由抱著手,戲謔道:“沒想到你還有做姐妹的潛質啊。”
趙亦寒瞪著,“我買胭脂,關你什麽事。”
“當然不關我事了,又不是買給我的,有病。”孫由翻了個白眼。
曹允南實在待不下去了,對奚挽君道:“方才烤火烤熱了,我去湖邊走走。”
莊采黠誒了聲,提醒:“曹姑娘,那湖可深了啊,夜太晚,你當心著點,別掉了。”
奚挽君似笑非笑盯著自家舅舅。
“你笑什麽?大半夜的,怪瘮人的。”莊采黠攬了攬自己的雙臂,專心致誌烤火。
“我隻是覺得,你在這個年紀還沒婚,也是事出有因的。”奚挽君麵帶笑意,跟上了曹允南的步伐。
“事出有因?”莊采黠愣了下,不著頭腦。
“百因必有果——”
孫由朝莊采黠笑得賤兮兮,“你的報應就是…哎呦我去!”
“你他娘有病啊!”
孫由將裏的破布扯出來,臭烘烘的,對趙亦寒罵道:“這什麽玩意兒,你拿來泡陳年老醋了?”
“猜對了~”趙亦寒俏皮一笑:“這是李逢生的足。”
孫由拔出莊采黠的佩劍,“老娘今天就要幹死你——”
“別別別,別把我劍弄髒了。”莊采黠在後頭追。
曹允南收回目,看向了麵前寂靜無漣漪的湖麵,深深歎了口氣。
“曹姑娘這是在愁什麽呢?”
奚挽君的聲音從後傳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566 章

來人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啥? 身為王牌軍醫的我穿越了, 但是要馬上跟著王爺一起下葬? 還封棺兩次? 你們咋不上天呢! 司夜雲掀開棺材板,拳拳到肉乾翻反派們。 躺在棺材板裡的軒轅靖敲敲棺材蓋: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282.6萬字8.18 227621 -
連載1841 章

重生後我嫁了未婚夫的皇叔
前世,她是貴門嫡女,為了他鋪平道路成為太子,卻慘遭背叛,冠上謀逆之名,滿門無一倖免。一朝重生回十七歲,鬼手神醫,天生靈體,明明是罵名滿天下的醜女,卻一朝轉變,萬人驚。未婚夫後悔癡纏?她直接嫁給未婚夫權勢滔天的皇叔,讓他高攀不起!冇想到這聲名赫赫冷血鐵麵的皇叔竟然是個寵妻狂魔?“我夫人醫術卓絕。”“我夫人廚藝精湛。”“我夫人貌比天仙。”從皇城第一醜女到風靡天下的偶像,皇叔直接捧上天!
331.1萬字8 71759 -
完結332 章

首輔寵妻錄
侯府嫡女沈沅生得芙蓉面,凝脂肌,是揚州府的第一美人。她與康平伯陸諶定下婚約後,便做了個夢。 夢中她被夫君冷落,只因陸諶娶她的緣由是她同她庶妹容貌肖似,待失蹤的庶妹歸來後,沈沅很快便悽慘離世。 而陸諶的五叔——權傾朝野,鐵腕狠辣的當朝首輔,兼鎮國公陸之昀。每月卻會獨自來她墳前,靜默陪伴。 彼時沈沅已故多年。 卻沒成想,陸之昀一直未娶,最後親登侯府,娶了她的靈牌。 重生後,沈沅不願重蹈覆轍,便將目標瞄準了這位冷肅權臣。 韶園宴上,年過而立的男人成熟英俊,身着緋袍公服,佩革帶樑冠,氣度鎮重威嚴。 待他即從她身旁而過時,沈沅故意將手中軟帕落地,想借此靠近試探。 陸之昀不近女色,平生最厭惡脂粉味,衆人都在靜看沈沅的笑話。誰料,一貫冷心冷面的首輔竟幫沈沅拾起了帕子。 男人神情淡漠,只低聲道:“拿好。” 無人知曉,他惦念了這個美人整整兩世。
53.2萬字8.33 6779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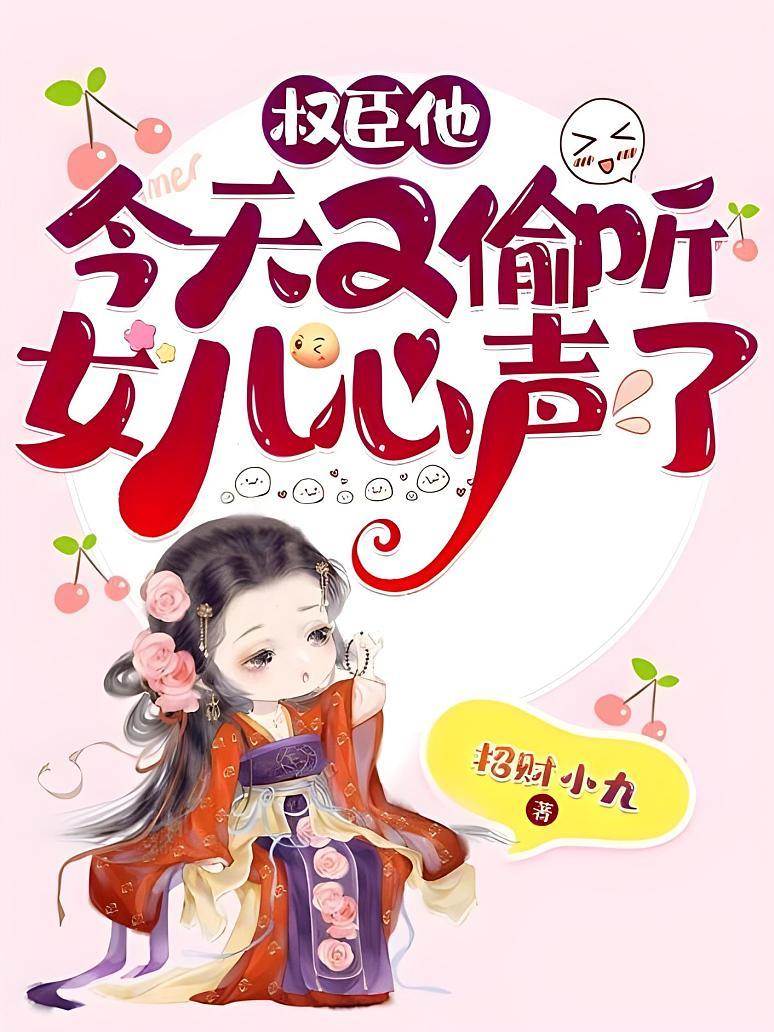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