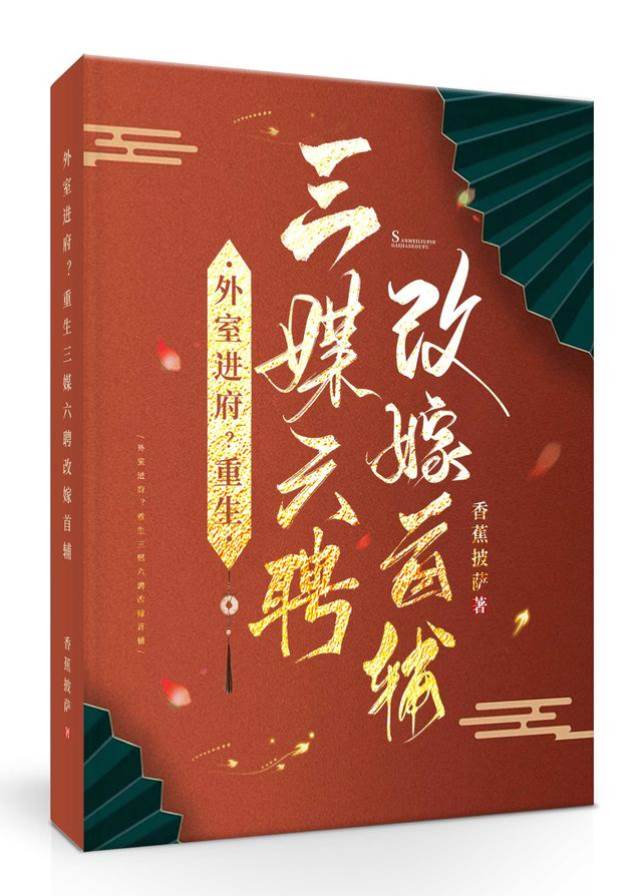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替嫁流放,世子妃種出北大倉》 第807章 她倆是聯手把人已經打死了嗎?
陳允準確接收徐璈的暗示,非常機靈地跑過去扶住了親爹的胳膊:“爹,我就說不用的。”
“徐大哥平日裏揍我的時候也從不手下留,都是一視同仁的,這頭要是磕了我可太沒麵子了。”
陳泰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的瞪陳允:“還渾。”
“你得世叔。”
“我不。”
陳允巧妙閃躲避開陳泰要摁自己腦袋的手,朝著徐璈後一躲就喊:“打人了打人了!”
“救救我!”
“快來人救救我!”
陳家夫婦本來是揣著滿腔的激,決心哪怕三跪三叩首也要謝徐璈夫婦的大恩。
誰知被陳允這麽一打岔,再複雜難言的緒都被衝了個一幹二淨。
陳泰最後也沒逮住上躥下跳的陳允,徐三叔代為手,在陳允的屁上象征地踹了一腳表了個意思。
陳允被踹了一腳,心滿意足地去帶著徐明煦和徐錦惜玩兒了。
中途試圖手去搶糯糯和元寶,被徐璈大手一揮送了個滾蛋,麻溜一抓擺就滾了。
劉清芳早已習慣了這般形,跟桑枝夏說著話就去了小院裏。
陳泰卻是頭一回見。
陳泰被徐璈和徐三叔請著進了會客的地方,坐下後難掩慨地說:“小兒頑劣,這幾年多虧諸位費心了。”
“倒也沒費什麽心。”
徐璈接住糯糯從頭上拆解下來的發冠抓在手裏,任由一頭潑墨似的長發被閨兒子折騰在腦後,淡淡地說:“他自己機靈。”
“這幾年武藝長進不多,挨的罰卻不,這方麵我的確是沒手下留。”
陳允習武開蒙晚,再加上天賦一般,跟桑延佑是同時開始的,進展卻稍顯緩慢。
Advertisement
但陳允腦子靈,壞水也是串地咕嘟往外冒。
往日但凡不得空就罷了,一旦得空幾個小子湊頭在一起,陳允和徐明煦就是出壞主意的軍師,徐明輝和桑延佑就是純純的打手。
一人惹禍集遭殃,徐璈下手收拾的時候從不管這孩子是不是姓徐,實行的都是連坐製度。
人家親爹都不見得下過狠手,徐璈說起來也不見半點心虛。
陳泰被徐璈的話弄得發笑:“不訓不才,如此極好。”
“若不是有此等緣分,這孩子隻怕不會有今日的出挑。”
徐璈笑了笑沒接話,站在他腦後的糯糯催促道:“爹爹,梳子給我嘛。”
徐璈臉上罕見浮現出幾分頭疼的神,從糯糯帶來的小盒子裏拿出特製的小梳子遞給,縱容道:“糯糯,爹爹和叔叔說正事兒呢,一會兒再打扮好不好?”
“不好。”
糯糯拿著小梳子較真得很,小手認真梳理著徐璈的長發,聲氣地說:“曾祖說叔叔不是外人,不用見外的。”
“對對對。”
元寶正在專心給姐姐打下手,想也不想地補充說:“見外人都要換裳,要注重儀態,但陳叔叔不是外人,所以不用。”
徐璈一口氣沒上得來,糯糯就煞有其事地說:“對哇。”
“爹爹你不要調皮,我們都要聽曾祖父的話。”
元寶鄭重點頭:“對,聽話。”
徐璈:“……”
徐璈尚留了一點在人前的麵子不願放,但又屬實不忍辜負孩子的熱,掙紮不過一剎,徐璈心複雜地說:“那你們想怎麽弄?”
“編小辮子!”
Advertisement
元寶驕傲地指著自己頭頂歪歪扭扭的幾小辮,滿眼崇拜地著糯糯說:“姐姐編的哦。”
“爹爹和元寶要一樣的!”
徐璈看著兒子的小辮兒深深吸氣。
遭過磋磨的徐三叔滿臉不忍直視,嘖嘖幾聲忍著笑歪過了頭。
陳泰佯裝喝茶遮住了眼底的戲謔。
等徐璈調整了個姿勢方便後的小家夥們手了,陳泰才溫聲說:“照理說將軍今日才歸,我本該等將軍多休整幾日再來叨擾。”
“隻是想及近來在王城中聽到的一些風聲有些坐不住,這才急急過來,想請將軍點撥一二。”
徐璈胳膊搭在椅子邊上護住了兩個小家夥,聞聲要笑不笑地彎起了眼:“王城中的風聲?”
“是什麽?”
花廳說話的聲音被逐漸放低,小院裏劉清芳拉著桑枝夏的手,忍著慨連著說了好幾句不容易。
誰都知道江南水患來勢洶洶,也都知道在那裏直麵的是生死一線。
可旁人隻是道聽途說都覺驚險萬分,了困局還可全而退的就顯得更是難得。
話過慨,劉清芳湊近了些小聲說:“嫣然此次是與你一道同去的,也都安穩回來了?”
桑枝夏沒太懂突然問起徐嫣然的意思,愣了下點頭道:“同去同歸,怎麽了?”
劉清芳像是有些為難,斟酌了好一會兒才輕輕地說:“外頭的人都是渾說的瞎話,一個字都當不得真,隻是這道理你知道,我也明白,落在別人的裏就不見得是那麽回事兒了。”
對上桑枝夏越發迷茫的眼神,劉清芳用隻有桑枝夏能聽到的聲音說:“王城中的貴婦圈子裏近來起了一則傳聞,是關於嫣然的婚事。”
Advertisement
徐嫣然正是花骨朵一般的好年紀。
又出自徐家這樣的世,三房唯一的脈,論起尊貴不比誰差。
去年開始就有人來探徐家的口風,也有人想走南家的門路與徐家結親,隻可惜都被擋了回去。
徐三叔夫婦心切,再加上徐嫣然自己無意早早婚,還想多學幾年醫治病救人,都說是暫時不急。
不想話傳著就逐漸變了味兒。
劉清芳不拿桑枝夏當外人,帶著散不開的擔心說:“你們不在家的這段時日,家裏也有登門探口風的人,無一都被拒了。”
“但後來不知怎地,逐漸就傳出了徐家有意出一個王妃的瞎話,就連你帶著嫣然去滁州,也都被說了是假借探驃騎將軍的名義,帶去小王爺的麵前臉。”
這瞎話已經傳了許久,但徐家的人的確是暫不知。
劉清芳無奈道:“你婆母和娘忙著在家照看孩兒,不耐煩去應付外頭的人,一貫是很見客。”
“你二嬸和三嬸都忙於打理外頭的買賣,也沒時間去聽這些婦人嚼舌碎語,但諸如此類的話,我在外聽過不下三次了。”
劉清芳甚出門,也不多與徐家之外的人來往。
話都傳到的耳朵裏了,可見外頭到底傳了什麽樣兒。
劉清芳知道徐家人的為人,也知道桑枝夏絕對不會為了攀附小王爺的富貴,拿徐嫣然的名聲做戲。
今日聽說桑枝夏回來了,氣兒都沒顧得上就趕了過來。
劉清芳苦笑道:“我也想過跟三嬸或是二嬸提,家裏總該要有一個知道的。”
“可這兩位連日來忙得不見蹤影,我請了好幾次都沒見到人,趕巧你回來了,就隻能是來找你了。”
桑枝夏的臉沉了下去:“這話都是從何起的,你最先是從誰的裏聽到的?”
劉清芳說了個人名,還沒來得及往下解釋,點翠就快步走過來說:“東家,出事兒了。”
桑枝夏錯愕道:“怎麽?”
“剛才來人傳話,南小姐和田姑娘本來是結伴出去閑逛,在咱家的脂鋪子裏見了郭家的姑娘,不知怎麽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
桑枝夏:“……”
桑枝夏想了想南微微和田穎兒可怕的戰力,遲疑道:“所以,倆是聯手把人已經打死了嗎?”
“我去收???”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連載162 章

東宮美人
宋懷宴是東宮太子,品行如玉,郎艷獨絕,乃是世人口中宛若謫仙般的存在。南殊是東宮里最低下的宮女。她遮住身段,掩蓋容貌,卑微的猶如墻角下的殘雪,無人在意。誰也未曾想到,太子殿下的恩寵會落在她身上。冊封那日,南殊一襲素裙緩緩上前,滿屋子的人都帶著…
51.2萬字8 8875 -
完結919 章
娘子很剽悍
前世她不甘寂寞違抗父命丟下婚約與那人私奔,本以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幸福生活那知沒兩年天下大亂,為了一口吃的她被那人賣給了土匪。重生后為了能待在山窩窩里過這一生,她捋起袖子拳打勾引她男人的情敵,坐斗見不得她好的婆婆,可這個她打架他遞棍,她斗婆婆他端茶的男人是怎回事?這是不嫌事大啊!
85.9萬字8 2980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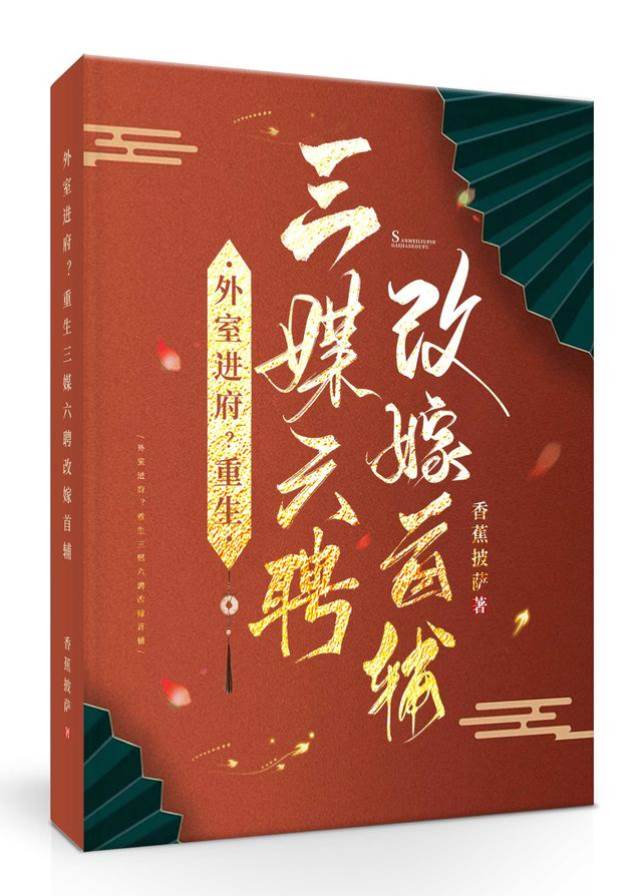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
完結239 章

寵妾滅妻奪嫁妝?廢你滿府嫁皇家
前世,謝錦雲管理後宅,悉心教養庶子庶女,保住侯府滿門榮華。最後卻落得一杯毒酒,和遺臭萬年的惡毒後母的名聲。死後,她那不近女色的夫君,風光迎娶新人。大婚之日,他更是一臉深情望着新人道:“嬌兒,我終於將孩子們真正的母親娶回來了,侯府只有你配當這個女主人。”謝錦雲看到這裏,一陣昏厥。再次醒來,重回前世。這一次,她徹底擺爛,不再教養狼心狗肺之人。逆子逆女們若敢惹她,她當場打斷他們的腿!狗男女還想吸血,風風光光一輩子?做夢!只是,她本打算做個惡婦,一輩子在侯府作威作福。沒想到,當朝太子莫名伸手,先讓她成爲了下堂婦,後又欽點她爲太子妃?她還沒恍過神呢,發現一直仇恨她的庶子庶女們,一個個直呼後悔,說她纔是親孃。昔日瞧不起她的夫看,更是跪在她面前,求她再給一次機會?
44.2萬字8.18 36260 -
完結185 章

小娘,你也不想王府絕後吧
西南王季燁出殯那天,失蹤三年的長子季寒舟回來了。爭名,奪利,掌權,一氣嗬成。人人都說,季寒舟是回來繼承西南王府的,隻有雲姝知道,他是回來複仇的。他是無間地獄回來的惡鬼,而雲姝就是那個背叛他,推他下地獄的人。她欠他命,欠他情,還欠他愛。靈堂裏,雲姝被逼至絕境,男人聲音帶著刻骨的仇恨與癲狂“雲姝,別來無恙。”“我回來了,回來繼承父王的一切,權勢,地位,財富……”“當然也包括你,我的小娘。”
27.5萬字8.33 87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