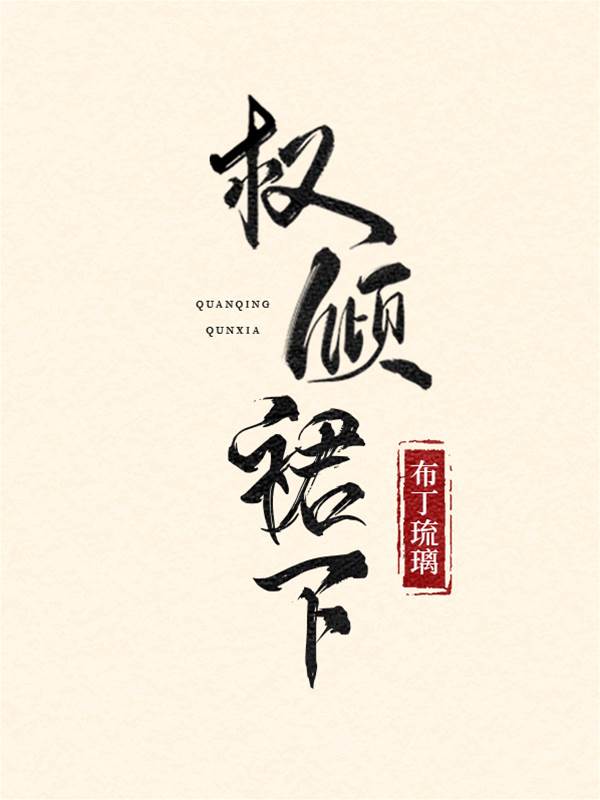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千山青黛》 第 70 章(《盂蘭盆經》裏,有一則關...)
《盂蘭盆經》裏,有一則關於目連救母的傳說。目連見亡母困於地獄,如倒懸,苦海難,悲傷不已,遂求佛救度。釋迦指一解法,在僧眾的安居終了之日供養十方僧眾。便是因此,興起了盂蘭盆會。到這一天,各大寺院紛紛舉辦誦經法會和水陸道場,善男信則施齋供僧,放燈於水,以此寄托哀思,為亡故親人追福。
在長安,從老聖人一朝開始,為弘揚孝道,盂蘭盆日也為了一年當中除元宵之外的唯一一個宵解除日。到這一夜,各坊門戶不閉,坊民自由出,紛紛聚向東西兩市。那裏,各有一個連通漕河的放生池,池麵廣闊,民眾皆可前來隨水放燈,以應節禮。
又不知何時開始,放燈漸漸也變長安富貴人家競誇奢豪的一種方式。他們不再滿足於簡單的普通蓮燈,往往提前多日便請來能工巧匠為自家製作各種形狀的水上花燈,燈也做得越來越大,有最大者,如同寶塔,到了盂蘭盆日,天黑之後,隨船紛紛放於池麵,燦爛如星,爭奇鬥豔,引無數人紛至遝來,競相觀。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天黑之後,西市的放生池邊圍滿了來自全城各坊的善男信,坊各家商鋪抓住這難得的機會通宵亮燈,招攬客人,街市到都是人,笑語喧聲,一派繁華的太平景象。
裴蕭元登上了一條放燈船。
這條船的外觀起來和今夜於放生池上的眾多船隻一樣,船頭船尾,皆懸蓮燈,毫也不起眼。但是,便可見有圍屏,圍屏裏是兩張筵席,一左一右,相對設座。此外空空,別無它。此刻,圍屏之中,立著李延。
Advertisement
他一襲白,若非麵門之上還有一道被利刃所破而留的淡淡傷痕,去,就和長安今夜無數正在街頭遊走著太平夜市的尋常士子無甚兩樣。
“多謝你肯來見我。請座。”
他的麵上出笑容,朝著裴蕭元點頭說道。
裴蕭元徑直坐到了其中一張筵席之後,隨即,打量他一眼。
“你的膽子不小。”他說道。
今夜為維持秩序,在東西兩市的各個街口,皆有多於白天一倍的金吾衛士通宵執勤。
李延自己也坐到另張筵席之後,沉默了一下。
"見笑了撲-兒文=~學)。實不相瞞,我也害怕。為這一麵躊躇過許久,但最後還是決定冒險,再賭一堵我的運道。"
"隻要能見到裴郎君的麵,任何代價,某都願意去賭。"
裴蕭元的目掠過李延麵門上殘留的那一道劍痕,笑了撲-兒文=~學)笑:"裴某何德何能,豈敢當如此之言。你何事?"
李廷斟酒一杯,向他端起。
"這應當是我與裴郎君見的第三麵了。說起來,上次在金風樓,全是仰仗你手下留,我方逃過一劫。恩一直銘記在心,早就想向裴郎君道謝。今夜總算得到機會能夠麵謝。我先飲為敬。"
他說完,一飲而盡。
裴蕭元並未隨他斟飲回禮,隻冷冷道:"你我各自都知,今夜我來,不是為了聽你說這些。"
"裴郎君爽快,我便也不作態了。我約你見麵,目的隻有一個,那便是請你助我。"
"我要為父複仇,拿回長安。此間一切,原本就是屬於我的,你知道的。"
Advertisement
裴蕭元平靜地著他,如早已預知他說出的這一番話。
李延繼續道:"請賢助力,自然不能空手而來。我也知道,裴郎君你非俗世那些蠅營狗茍之輩可比,若是許以旁人趨之若鶩的富貴榮華,非但不能說於你,反而如同辱於你。我更不想自取其辱,不說這些。我如今唯一能拿來向裴郎君表我心意的,便是助力裴郎君複仇!"
他說完,地注視著對麵之人,等待他的回應。
"你雖曾份殊顯,然而早已是時過境遷。當今聖人是否賢明君主,或待將來史辯說,但他至絕非無為庸碌之主。"
裴蕭元終於開口,語氣尋常。
"恕我直言,你想在他手下翻,恐怕就是癡人說夢了,談何助我複仇?"
"何況,我若想複仇,自有手腳,又何須借助於你?"
他的話絕無譏嘲或是輕蔑,但字字如刀,無毫委婉之意。
李延的神卻未改變,聞言反而笑了撲-兒文=~學)起來,點頭。
"是,我知我螳臂當車不自量力,裴郎君更是才智卓絕,心誌堅韌,更有翻江攪海之能,區區複仇之事,確實己力足夠,但--"
他頓了一下,地盯著裴蕭元。
"若你仇人,是當今那位被稱作聖人的人呢?"
裴蕭元慢慢抬目,對上了李延的兩道目,片刻後,角微微扭曲,牽了一下。
"你有證據?"
李延搖頭,隨即立刻又道:"我固然如今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我不信,以裴郎君你的智慧,從未懷疑過如今紫雲宮裏的那個人。"
"當年北淵一事,我敢肯定,西蕃軍之所以敢大舉侵犯,必是我朝有人傳訊,好阻止神虎大將軍歸京,更是要借機將他除去,以絕後患。"
Advertisement
"此事牽涉之廣,影響之大,可謂變之後朝堂的又一巨變。那可是關係到皇位和神虎軍十萬將士的天大之事!當今皇帝,他當年能在眾皇子裏穎而出,因勢上位,他怎麽可能會是置事外的無辜之人?他不是惡首,誰是?"
裴蕭元的麵此時變得如鑄鐵一般凝重,目也隨之轉為森冷。
"李延!"他忽然喝了一聲對麵之人的名字,自座上站起。
"在我麵前說這些蜚蓬無度的捕風捉影之言,你恐怕是打錯主意了!"
"裴郎君稍安,請再座,聽我解釋!"李延又道。
"今夜我膽敢將裴郎君請來相見,自然不止如此。裴郎君如今所居的永寧宅,前主乃是幾年前因罪遭殺的宗親舊王陳王,此事裴郎君必然知悉。但裴郎君應當不知,當日北淵事變之前,陳王正好在晉州擔職,當時定王爭我父親的位,正在趕回長安的路上,路過晉州之時,就是落腳在他府裏的,故他見證了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事。"
"那天晚上,原州來了一個人,見定王。傳達何事,陳王不知,我自然也不敢妄加揣測。但在此前不久,柳策業便以聯絡軍為由,未得老聖人任命,自行去了原州。此事並非是我誣陷,如今朝堂裏的一些老人也都知道的。原州便是當年馮貞平的駐軍之地,與北淵相去不遠。"
"那個時候,他為何要去那裏?"
"不但如此!原州來的那個信使,裴郎君你知是何人嗎?便是如今太子妻兄韋居仁的父親!當日他還是我父景升東宮裏的人,居洗馬,我父親對他極是信任,因不放心馮貞平,對他委以重任,派他過去監督軍事。誰知他亦是無節小人,早早便被收買,投了定王。"
Advertisement
"是什麽重要的事,要他這樣的人,親自從原州趕來見定王?"
"陳王非定王心腹,自然不知,時至今日,我更是不敢斷言。但若允我猜測,他必是了柳策業的派遣,來與定王議那一場即將就要發生的北淵謀。"
李延的麵上漸漸出了激的神。
忽然此時,船外發出了一陣歡呼之聲,將他聲音吞沒。那是放生池畔的人們因到奇蓮燈而作出的反應。
"是!那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謀!"他隨著岸邊的歡呼,驟然提高聲音。
"這一場謀裏,我的父親失去了他最為信靠的神虎大將軍。當年我十五歲,被派出迎接大將軍。然而我等不到。沒了軍隊,為了自保,我的父親被迫在長安倉促應對,期能在他兄弟那一把屠刀砍下來之前得到老聖人的支持。他自然是失敗了,於是變作了可恥的謀逆者。而那個真正的謀逆之人,他在殺死神虎大將軍和百壯士之後,反而龍袍加,搖為了萬民稱頌的聖人!"
"不但如此,時至今日,柳策業、馮貞平,還有背叛了你父親、我父親的陳思達、韋家之流,他們全部富貴加!然而裴郎君,你的父親,他竟至今沒有得到一個正名!而他本是該立廟犧牲祭拜的忠烈英魂!"
岸邊的歡呼聲漸漸落低,片刻後,待緒慢慢平定,他再次向裴蕭元,聲也轉為平緩。
"裴郎君,我知近日乃令堂忌日。我如今不過一東躲西藏之人,不能見到天日,便是想去祭拜,也是枉然,隻能遙遙以抔土清香代祭,以寄敬意。"
"方才你問我證據,我確實沒有能拿得出來的確鑿之證。我方才轉的陳王之言,你也可以不信,畢竟,此人也非良善之輩。但三年前,那降來的西蕃貴族也莫名橫死大街,這難道不足以證明,當年北淵之戰另有謀?"
說到這裏,他抬手,輕一下麵上劍傷。
"在我年之時,我父親所聘,裴公也曾為我老師。雖然時日不久,他便辭出京,但裴公昔日對我的諄諄教誨,我至今牢記在心。一日為師,終為師。年初我去甘涼,本意便是想去拜裴公,然而再三考慮過後,想到他年事已高,終究還是不忍貿然再用我的這一點事去驚擾他老人家,故中途而返。與裴郎君你,更是不打不相識。無論你如何待我,在我這裏,你是個值得我李延冒任何風險也願結之人。"
"至於你的父親,更是我李延生平最為敬重之人。當年他若是拋卻後北淵,如期返京,有他在,我的父親或許便能化險為夷。
但那樣,大將軍便不是大將軍了!今夜我就在這裏,你可以殺了我,也可以將我獻給皇帝邀功,我既到來,便已做好最壞打算。"
"但是最後,我還是有一句話要說,裴郎君,如今的這個聖人,他才是當年北淵之變的元兇。你回朝做,他日,就算除掉其餘仇人,居高位,然而,你卻還要奉他為君,奉他那將來某日或也容不下你的某個兒子為君,你當真甘心嗎?"
李延一口氣將全部的話都說了出來,雙眼一眨不眨,凝視著對麵之人。
方才再次座之後,他便一句話也沒說過了,更不曾打斷李延的話,始終靜聽。待李延全部說完,他閉目,一不,麵容如蒙一層翳,去毫無表,不辨悲喜。
李延靜靜等待。
片刻後,隻見他睜目,起了,走到艙窗之前,推開了其中的一麵。
"你來。"他開口,喚道。
李延有些不解,遲疑了下,很快還是應喚,也走到他的畔,停在窗後。
他們的這條船正在放生池的中央,此刻,池上漂滿了各式各樣的蓮燈和放燈船。岸邊人頭攢,臨水的街市上,則布著鱗次櫛比的屋宇。
到都是璀璨的燈火,水邊還有放焰口的法事,夜遊人更是滿街市。
他半晌又不再說話了,目隻不停地巡遊過前方的街市。李延等待片刻,終還是忍不住,略疑地發問:"裴郎君何意?"
"你那裏。"裴蕭元抬臂,指著遠右前方十字路口的一間高屋。
"那是一波斯邸,是間專收寶的胡商鋪子。我來的時候,留意到鋪子的路口站著個人,帶著一袋沉重的東西。他去像個賣貨人,然而舉止又和周圍真正的賣貨人不同。隻在附近走來走去,避開路過的巡街衛士。"
"我經過的時候,故意撞了一下他的口袋。他裝作若無其事,但我仍是了出來,他極是張。我也聽到了口袋發出的靜。裏麵裝的是銅錢。"
"不止這一,在坊其餘幾,東北方向張家藥行,東南方向典當行,西南方向的帛店,我都發現有類似的人。選的這些地點,很是湊巧,也都是路窄人多,最為熱鬧的十字路口。"
"我初職時,大略過一些金吾衛庫檔舊誌。老聖人朝,大約二十幾年前,一個元宵夜,西市便曾因意外發生行人踩踏的變故,當時死傷不下百人,包括幾名試圖維持秩序的金吾衛士--"
說到這裏,他關窗,轉向隨他講述麵微變的李延。
"李郎君,倘若我沒猜錯,那些都是接應你的人吧?你冒險約我見於此,口口聲聲,稱將安危係在我這裏,其實早也做好退路了。萬一遇到不測,他們隻要往人多的地方撒錢,很容易便能引發路人爭搶,繼而造通堵塞,乃至人員踩踏。如此,今夜附近的金吾衛顧此失彼,你便可以借機從容離去。"
李延一時默然,片刻後,麵微微尷尬之,接著,苦笑了撲-兒文=~學)起來。
"什麽都瞞不過裴郎君。"他喃喃地道。
"裴郎君見諒,我實是--"
"不必解釋。換是我,也會防備。"
裴蕭元淡淡截斷他話。
"當年北淵元兇是誰,我會查清。甘不甘心,也是我自己的事。"
"我隻告訴李郎君一聲,人子複仇,此固然天經地義,但日後行事,勿犯我準則,否則,他日即便我不出手,太過聰明之人,恐也會遭聰明反噬。"
他說完,命船靠岸,隨即登岸離去,影迅速沒在了熙熙攘攘的夜行路人當中。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本文齁甜,雙潔,雙強,雙寵,雙黑)世間有三不可:不可見木蘭芳尊執劍,不可聞太華魔君撫琴,不可直麵勝楚衣的笑。很多年前,木蘭芳尊最後一次執劍,半座神都就冇了。很多年前,太華魔君陣前撫琴,偌大的上邪王朝就冇了。很多年後,有個人見了勝楚衣的笑,她的魂就冇了。——朔方王朝九皇子蕭憐,號雲極,女扮男裝位至儲君。乃京城的紈絝之首,旁人口中的九爺,眼中的祖宗,心中的閻王。這一世,她隻想帶著府中的成群妻妾,過著殺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奢侈糜爛生活,做朵安靜的黑心蓮,順便將甜膩膩的小包子拉扯大。可冇想到竟然被那來路不明的妖魔國師給盯上了。搶她也就罷了,竟敢還搶她包子!蕭憐端著腮幫子琢磨,勝楚衣跟大劍聖木蘭芳尊是親戚,跟東煌帝國的太華魔君還是親戚。都怪她當年見
118.2萬字8 18555 -
完結310 章

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李泠瑯同江琮琴瑟和鳴,至少她自己這麼覺得。二人成婚幾個月,雖不說如膠似漆,也算平淡溫馨。她處處細致體貼,小意呵護,給足了作為新婚妻子該給的體面。江琮雖身有沉疴、體虛孱弱,但生得頗為清俊,待她也溫柔有禮。泠瑯以為就能這麼安逸地過著。直到某個月…
47萬字8 684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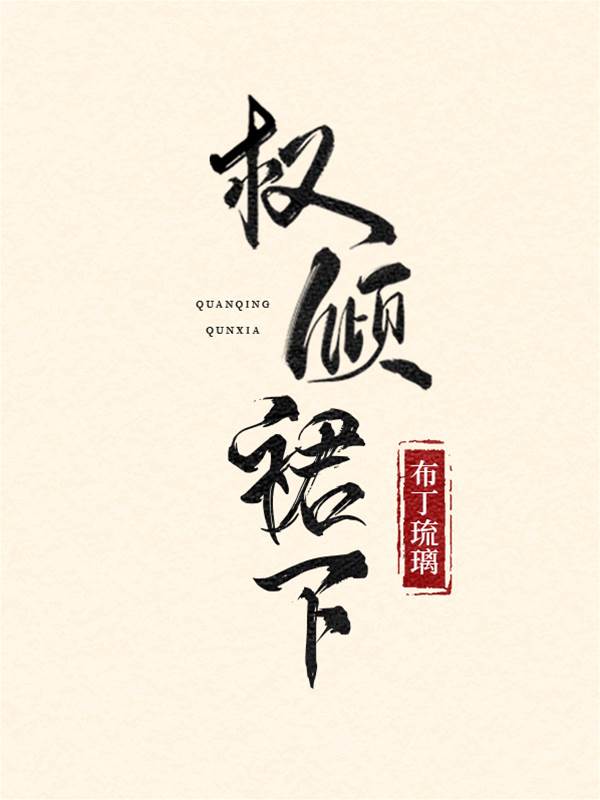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019 章

攝政王今天又在哄王妃
穿成了被繼母虐待被繼妹搶婚的懦弱伯府大小姐。云嫵踹掉渣男虐廢小三,攪得伯府天翻地覆。接著一道圣旨將她賜給了攝政王。攝政王權傾朝野,卻冷血無情,虐殺成性。人人都以為云嫵必死無疑,仇人們更是舉杯相慶等看好戲,豈料……在外冷血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卻天天柔聲哄著她:“寶貝,今天想虐哪個仇人。”
184.8萬字8 38042 -
完結183 章

誤酒
朝和小郡主黎梨,自幼榮華嬌寵,樂識春風與桃花,萬般皆順遂。 平日裏僅有的不痛快,全都來源於她的死對頭——將府嫡子,雲諫。 那人桀驁恣肆,打小與她勢同水火,二人見面就能掐。 然而,一壺誤酒,一夜荒唐。 待惺忪轉醒,向來張揚的少年赧然別開了臉:“今日!今日我就請父親上門提親!” 黎梨不敢置信:“……你竟是這樣的老古板?” * 長公主姨母說了,男人是塊寶,囤得越多就越好。 黎梨果斷拒了雲諫送上門的長街紅聘,轉身就與新科探花郎打得火熱。 沒承想,那酒藥還會猝然復發。 先是在三鄉改政的山野。 雲諫一身是血,拼死將她帶出狼窩。 二人跌入山洞茅堆,黎梨驚詫於他臂上的淋漓刀傷,少年卻緊緊圈她入懷,晦暗眼底盡是抑制不住的戾氣與委屈。 “與我中的藥,難不成你真的想讓他解?” …… 後來,是在上元節的翌日。 雲諫跳下她院中的高牆,他親手扎的花燈猶掛層檐。 沒心沒肺的小郡主蜷縮在梨花樹下,身旁是繡了一半的香囊,還有羌搖小可汗的定情彎刀。 他自嘲般一笑,上前將她抱起:“昨日才說喜歡我……朝和郡主真是襟懷曠達,見一個就能愛一個。” * 雲諫出身將府高門,鮮衣怒馬,意氣風發,是長安城裏最奪目的天驕。 少年不知愁緒,但知曉兩樣酸楚。 一則,是自幼心儀的姑娘將自己看作死對頭。 另一則,是她不肯嫁。
27.1萬字8 8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