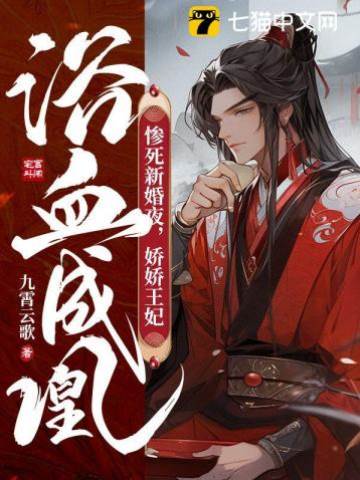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試婚丫鬟》 第174章 鎮北王絕后
“什麼?”朝堂之上,有人不顧儀態地驚出聲。
崔拙沒說話,卻是轉過渾濁的老眼,死死盯著顧剛則,連咳嗽聲都停了。
“怎會如此?”倒是鴻慶帝倒還震驚,他也一臉關心地看著顧剛則,“鎮北王世子怎麼會……遭此不測?”他雙眉蹙,極不忍一般看向崔拙,“崔世叔,你可要……節哀。”
顧剛則:“兩日前,臣接到鎮海關總兵八百里加急到京,說是那伙子匪人,與三日前在關外截殺了一隊行商打扮之人。
一共七人,各個斃命。”
他冷靜的聲音,一字一句傳來。
崔拙只站著,脊背得筆直。
顧剛則:“那一行人輕裝踐行,馬車上沒有任何的徽記。
總兵和臣,一開始都以為是普通行商。
不幸遭了那貨賊人毒手。
因是在鎮海關發生的慘劇,總兵自知有責,便想著聯系他們的家人,給與恤,立時便張榜查這幾人份。”
顧剛則頓了頓,接下來的話很難啟齒似的,“因這……人死后,與生前,容貌雖一般無二,可畢竟也往日不同。
這睜著眼睛的人,和閉著眼睛的人,相差很多。
榜單在南城墻上有一段日子,其中一個,才人給認了出來。”
說著,他從自己寬大華貴的暗紅袖里,掏出一卷邊角都破損了薄紙。
正是日常里州縣府用于張文書告示的那一種。
顧剛則把最外面的一張抖開,直直遞到崔拙面前,“鎮北王,您看看,這是不是王府里的副將,做陳士安的?” 那張紙上,畫著一個壯年男子,頭發蓬,五兇狠,脖頸上打著褐領結。
Advertisement
這畫,竟畫得十分真細致,連他脖頸上猙獰的傷口,和滿臉的跡,都纖毫不差地復原了出來。
仿佛真能人通過這一張薄薄的宣紙,看到那個做陳士安的中年人猙獰、不甘的死狀。
鎮北王鐵塔似的子,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他自然認出了追隨了自己半輩子的老部下。
陳士安脖頸上的褐巾,還是昔日在戰場上為了裹傷,他這個將軍,親自為他打的呢!那時,陳士安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為了炫耀,這褐巾他戴了一輩子…… 指尖在覆蓋到手背的輕甲下搐著攥,崔拙雪白的胡子抖了抖,沒有說話。
顧剛則眼底一憐憫轉瞬即逝,他又抖開了手中第二張紙,“您給認一認,這是不是府上管家崔贊?” 跟了他三十年的老管家,在畫上,死不瞑目。
崔贊這輩子,最引以為豪的,便是出最底層,被崔將軍收到麾下,學習讀書寫字,管調錢糧。
用他自己的話說,“老夫這雙手,養得跟貴人一樣!哪里看得出過過食不果腹的苦日子?” 現在,這雙手,也赫然出現在畫上。
顧剛則有些為難似的,“這位先生,不知為何,被人砍了頭,砍了手,十手指被那匪徒一一卸下。
怕是這群匪徒,妒忌讀書人吧?”他飛快地瞥了崔拙一眼,生怕他不住似的輕輕地道,“這崔先生死前,很是遭了一番非人的折磨。”
崔拙還是不說話。
所有人卻都看出來,他輕甲下的,已然在劇烈抖。
一張老臉,也在紅潤下,泛出青白來。
一側角控制不住似的,往下歪斜下去。
Advertisement
陪伴火回北疆的,都是他最忠誠干練的部下,也是相了大半輩子的老朋友。
他他們回去,原本是為他們覓得一條活路的。
誰想到…… 龍椅上,鴻慶帝手指有一下沒一下地把玩著扶手上的龍頭,饒有興味地看著顧剛則的表演,適時上一句,“崔世叔,還看嗎?” 他目落在顧剛則手里。
所有人都知道,顧剛則手中的最后一張紙上,畫的必是那鎮北王世子崔火。
他真的死了? 顧剛則緩緩地,把前六張紙都給崔拙看完。
還剩下最后一張,被他牢牢地扣在指間。
他臉上的表,是滿是不忍:“鎮北王,還……還認嗎?”他也是有獨子的人,對崔拙的覺,多多能同。
說來說去,還不都是怪著崔家貪王爵的風富貴? 若能……早點上繳那玉劍和皇上始終懸心惦記的兵符,何至于有今日?白發人送黑發人,承著世間最猛烈的傷子之痛? 這事從頭到尾都是顧剛則辦的,他嘆了口氣,輕聲提點,“要不,還是不看了吧?世子的……畫像,著實慘烈。”
崔拙一雙老眼,緩緩轉向顧剛則,仿佛剛剛認出眼前的這位,也是同自己并肩作戰了半輩子的老伙伴。
他胡子抖了抖,聲音嘶啞得厲害:“看!” “鎮北王……” “我說,看。”
崔拙眼中,迸發出,視著顧剛則。
顧剛則形一僵。
“呵,”龍椅上,似乎傳來一聲極輕極快的冷笑,“顧相,鎮北王老世叔執意如此,那便給他,給大伙看看吧。”
顧剛則手中,最后一張宣紙,在崔拙面前,緩緩展開。
Advertisement
紙上畫的崔火,滿臉鮮,狼狽不堪,臉似乎都因為被毆打而變了形,一道猙獰的刀口,從角直接割到太。
這張畫畫得比前面幾張,更為致,連那傷口翻開的皮,都畫得纖毫畢現,仿佛這人的尸,就在眼前。
崔拙終于不住,鐵塔似的子往后踉蹌了半步。
他的兒子,他唯一的兒子,原本的王位繼承人……就這樣死了? 崔家,絕后了? 他這副模樣,連顧剛則都有些不忍。
到底是并肩打過天下的同僚,民間畫本子里,都傳說鎮北王驍勇,還說沒有鎮北王,就沒有景家的天下。
就是這傳聞,和在手里的百萬玄甲軍,害了崔家! 早把兵符出來,不就沒事了? 雖然不忍,顧剛則倒還記著,鴻慶帝就高高地坐在上頭。
他深吸了口氣,“鎮北王,認出來了沒有?這是不是世子的……尸首?” 此言一出,大殿上針落可聞。
只有崔拙沉重的息聲,一聲接著一聲。
好像他口,有一臺陳年老風箱,每一次轉,都要耗盡全力。
好像下一刻,這風箱就要停擺。
崔拙后的武將,有些面不忍的,默默轉過臉去。
好半晌,崔拙:“這畫像……確是我兒火。”
他頓了頓,依舊是繃直了脊背,站直子,“可,也畢竟只是畫像。
一張紙而已,證明不了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2063 章

亡後歸來
重重波瀾詭秘,步步陰謀毒計。她,獨一無二的狠辣亡後,發誓要這天下易主,江山改姓;他,腹黑妖孽的傾世宦官,揹負驚天秘密,陪卿覆手乾坤。她問:“玉璿璣,我要的天下你敢給嗎?”他回:“蘇緋色,你敢覬覦,本督就敢成全。”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縱觀天下,捨我其誰!
396.7萬字8 13509 -
完結503 章

重生之請妻入甕
聽聞鎮國將軍府,老將軍年老多病,小將軍頑疾纏身。作為一個不受待見的公主燕卿卿,兩眼發亮,風風火火的主動請求下嫁。本是抱著耗死老的,熬死小的,當個坐擁家財萬貫的富貴婆的遠大理想出嫁。不曾想,那傳聞中奄奄一息的裴殊小將軍化身閻王爺。百般***還…
77.7萬字8 29843 -
完結315 章

女扮男裝的男主她玩脫了
祁懿美穿成了最近看的一部權謀文中的……男主。 哦,還是女扮男裝的 眼看劇情要按權謀主線發展,為了讓自己這個權謀小白好好的茍到大結局,祁懿美果斷決定逃離主線,卻機緣巧合成了病美人六皇子的伴讀 從此她便和他綁定了,還被人們編成了CP,被滿京城
51.7萬字8.18 4709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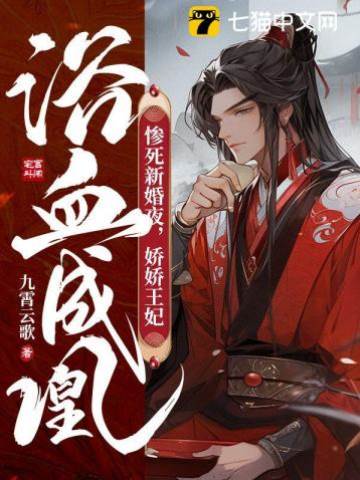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