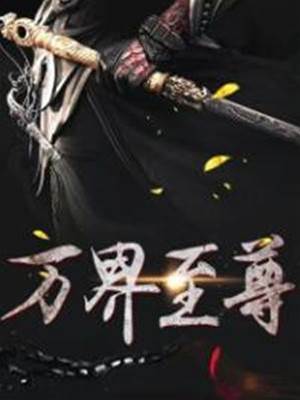《大魏讀書人》 第八十五章:朝堂之爭,激烈洶湧,三日明意,決定生死【為最單純大佬加更】
從宮門到太和殿,要經過幾道流程。
宮門到金橋,便有史言把守,臣子有任何不妥之,都會被一一記錄下來,甚至誰誰誰和誰誰誰走在一起,也會被記錄下來。
到了金橋之後,步行五百米,便能到太和殿殿下,等到太監開口,他們才能朝著太和殿走去。
而此時,宮門口。 (5,0);
百湧,看似一團,可卻無形中分了四勢力。
穿麒麟武袍的是一品國公,一個個龍行虎步,說話聲音偏大,不顧及什麼形象,只是大多數比較年邁,一些中年武則站在其後,是武將勢力。
以鎮國公為首。
而另外一批穿著底青白長袍的,則是儒,大魏王朝的職設立不同,分武將、文臣、。
因為有儒道的原因,所以文臣與儒是分開的,大魏儒,至要七品明意,若不明意,怎能為?
便是儒者。
為首的也皆是滿頭白髮,但神奕奕,從頭到尾都一語不發,自我檢點的很,顯得高風亮節,與一旁的武將完全形兩種畫風。
儒之首,以吏部尚書陳正儒為主。
還有一批人數最多,三五群,不斷竊竊私語,這是大魏文臣,也可以稱得上最備勢力的存在,國家大事辦,皆有他們出手。
只要武將儒同意,那麼施行就是他們來做。
武帝之前,朝中最大的勢力是他們,後來武帝登基,文臣的勢力下降了許多,但如今新皇上位,他們再一次凝聚。 (5,0);
原因無他,因國勢而出。
倘若沒有北伐之爭,基本上朝中大大小小的事,皆由他們負責,而北伐之爭,讓武將統一戰線,也讓儒們統一戰線,這兩勢力凝聚在一起。
Advertisement
那所有的事都得靠邊站了。
文臣之首,則為顧言,為大理寺寺卿。
同時戶部尚書,刑部尚書,這兩位尚書也是文臣之首,組建東明會,輔國諫言。
最後一勢力則有些尷尬,人數不多,六七人罷了,與三勢力形鮮明對比,有些孤寂,這勢力之首,為工部尚書李彥龍,主張休養生息。
沒有任何人支持他們,尤其是武將,更是看都不願意看他們一眼。
往往每次早朝,都會找他們一番麻煩,只要他們開口,武將第一時間就要開罵,儒和東明會員也不會有所幫忙,他們也不想直接得罪武將勢力。
沒有必要,除非涉及到自。
百上朝,所有人都知曉今日的早朝,會有大事發生。
「啟朝。」
待百抵達太和殿時,守在門口的太監頓時開口,尖銳的聲音響起,百稍稍加快了步伐。 (5,0);
換置鞋子,走進大殿之中。
太和殿空闊無比,十八雕龍畫的柱子立於周圍。
百站好屬於自己的位置,著龍椅上的大魏帝,而後異口同聲道。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洪亮的聲音響起,這是基本流程。
「眾卿平。」
帝之聲響起,下一刻百起,再次高呼。
「謝陛下。」
但流程並未結束。
六部依次開口,提出目前的國家大事,待一番商談結束後,基本流程這才算是結束。
不管有任何私事,或者是其他事,前半個時辰都是在商討國家大事。
百姓為先。
國家為先。
哪怕你聽聞誰誰誰做了窮兇極惡之事,你都不能直接開口,因為這些事都是小事,屬於個人問題,或者是地方問題。
Advertisement
國家大事說完,你才能去說這些東西。
終於,就在這一刻,儒當中有人出聲。 (5,0);
「陛下,臣,有本奏。」
隨著儒傳來聲音,滿朝文武皆然神一變,但很快又恢復常態,靜心聆聽。
「宣。」
帝的聲音依舊平靜。
「陛下,武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長平郡南豫府,發生一件駭人聽聞之事,狂生許清宵,因朋友難,乞求嚴磊大儒法外開恩,但遭到回絕,而後於南豫府樓宴之上,怒斥嚴磊大儒,貶低聖人,此等行為,目無王法,不尊皇權,不敬聖意,如禽一般。」
「甚至於樓宴中,對讀書人拳腳相,更是煽南豫府百姓,企圖製造民變。」
「臣,懇求陛下,以大不敬之罪,將狂生許清宵發配邊疆,再以文宮之力,削他才氣,剝他功名,以儆效尤。」
開口之人,是一位七品明意儒。
他一番話,說的犀利無比,是三點就足以讓許清宵死無葬之地。
不尊皇權!不敬聖意!煽民眾!
換做任何一人,被戴上任何一頂帽子,只怕這輩子就到頭了。
可謂是字字殺人。 (5,0);
而這種言辭,顯然不是一個七品明意儒生能說出來的話,背地裡自然是大魏文宮之人。
但讓他出面,而不讓大儒出面,原因很簡單,讓一名普通儒拋磚引玉,看看皇帝的態度,若是皇帝態度是隨他們怎麼置,那就按照這個來。
如果皇帝不認可,那這些大儒就可以出來說話了,不然開局就讓大儒出場,容易一下子把局面搞太僵。
儒的聲音響起。
大殿當中。
Advertisement
大魏帝掃了一眼對方,婉兒則將奏摺呈上。
接過奏摺,帝幾乎只是掃了一眼,便緩緩合上。
這件事,滿朝文武都知道,就沒必要假裝不知了。
「此事,朕於昨日便已知曉。」
「眾卿有何見解?」
大魏帝開口。
十分平靜。
沒有生氣,也沒有任何緒,只是詢問眾臣有何意見。
隨著此話一說。
當下文當中,緩緩走出一人。
「臣,軍機,趙巖,有不同見解。」 (5,0);
影出現,緩緩開口道。
帝沒有說話,只是看著對方。
而後者也立刻開口道。
「此事,臣於昨日也已知曉,不過臣也得到一些其他消息。」
「與王景王大人說的有些不符。」
「這許清宵並非是為朋友出面,而是為一些無辜百姓出面。」
「再者,怒斥大儒之事,據消息來報,是大儒嚴磊沒有做到無私之境,有錯在先,當然這許清宵也的確狂妄,的確有錯,可臣認為,此事雙方皆有過錯。」
「至於煽民意,更顯得無稽之談,無非是百姓不明,鬧出一場誤會罷了。」
軍機趙巖開口。
他主站出來為許清宵辯解,倒不是袒護許清宵,也不是鍾意許清宵。
原因很簡單,他是武,本就與儒如同水火。
朝堂上的事就是這樣,有了黨派勢力之後,管你是對是錯,反正你提出來的東西,我一定要彈劾一下,不可能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吧?
噁心也好,氣你也好,反正不可能讓你說了算。 (5,0);
只是此話一說,王景有些皺眉了。
「趙大人,此事證據確鑿,儒生斥大儒,怎麼在你口中,僅僅了一件小事?」
Advertisement
他開口,有些不悅,不過也知道對方存在就是在找自己麻煩。
這也正常,文武如水火,他們也經常找武麻煩,倒也是習慣。
「王大人,此事無論怎麼說,都只是一場誤會罷了。」
「陛下,臣覺得,許清宵乃為大才,倒不如小懲大誡,就如此算了。」
趙巖開口,為許清宵爭個從輕發落。
然而王景看向帝,繼續開口道。
「陛下,臣認為,此言差矣,嚴儒是否有錯,可以另說,即便他當真有錯,有律法懲之,但許清宵狂妄無比,斥大儒,不敬長輩,此乃不孝。」
「蔑聖人,不敬聖意,此乃不仁!目中無法,則為無視皇權,不敬帝王,此乃不忠,而百姓並非不明,而是被人引,故為不義。」
「此等,不忠,不仁,不義,不孝之人。」
「理應剝奪功名,削其才華,流放邊境,以儆效尤,還陛下明鑑。」 (5,0);
他繼續開口,大有一副不搞死許清宵不罷休的覺。
這不忠不仁不義不孝。
四大罪名,任何一個都能誅了許清宵,當真是狠啊。
然而,儒越是想要弄死的人,武則越是要力保,只要此人不涉嫌十惡不赦的大罪,他們就會出言,反正提出不同的意見肯定是好事。
最終決定權還在皇帝手上,若是聽了自己的意見,那是好事,噁心到了儒,如果不聽自己的意見,那也沒關係,自己又沒什麼損失。
至於惡?都水火不容了,還怕什麼惡啊?
「陛下,區區一件小事,便將如此大才流放邊境,此為不公。」
「再者,許清宵乃新朝府試第一。」
「按照王大人之說,他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是否在影什麼呢?」
趙巖開口,這一句話頓時讓王景臉大變。
「趙巖,你莫要在這裡含噴人,微臣絕無此意,只覺許清宵不敬聖意,不尊皇權。」
王景頓時大怒,這趙巖一句話,幾乎是要讓他死啊。
影什麼? (5,0);
影陛下?說陛下昏庸?瞎了眼提拔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為府試第一?
這天大的帽子,他不接,也不敢接。
只是這一刻。
帝只是緩緩開口道。
「的確,當朝府試第一,若真是這般不忠不義,不仁不孝之人,只怕天下都要恥笑朕吧?」
帝開口,語氣平靜無比。
可這一句話,卻嚇得滿朝文武齊齊開口。
「陛下息怒。」
這句話可不是開玩笑的,皇帝怎可能有錯?
即便是有錯,只要不是大錯,做臣子基本上都不能去說,當然不怕死的言可以。
畢竟承認皇帝有錯很難。
「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絕無此意,絕無此意。」
王景有些被嚇到了。
他哪裡知道趙巖居然如此犀利,直接將自己進死路。
一時之間,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只是就在這一刻。
一道聲音響起,比較洪亮。 (5,0);
「陛下,王景之言,絕無此意,臣認為,您選許清宵為府試第一,是因為絕世文章。」
「但絕世文章,與品無關,許清宵能作出絕世文章,卻不代表他有品。」
「趙大人也讀過書,自然明白這個道理,對吧?」
聲音響起。
是一位大儒。
孫靜安。
太文閣大學士,地位極高,也是最有希在十年晉升天地大儒之人。
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民間,都擁有極高的威。
他一開口,趙巖頓時不敢說什麼了。
「孫大儒所言極是。」
趙巖回應了一聲,而後不再說什麼。
倒不是真不敢,主要是連孫靜安都開口了,他自然不敢說什麼。
這是大儒。
其地位比嚴磊都高一些,對付王景他沒有任何問題,但大儒出來了,他必須要退避。
說不過,也懟不過。
這一刻,大殿再一次安靜下來。 (5,0);
帝之聲繼續響起。
「其他卿,對此事,有何見解?」
再次問道,由始至終都沒有參與鬥爭,只是簡單的詢問。
但這就是帝王之。
「老臣有些意見。」
也就在此時,一位老者開口。
站在武將行列第三位,是安國公。
國公之位,權傾朝野,幾乎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
與大儒相比,不分仲伯。
「陛下,老臣認為,這許清宵怒斥大儒,確有不尊,但文人儒道,尤其是立意之事,本便有爭議,不尊上,是錯,可倚老賣老,也是錯,許清宵狂是狂妄一些,可算不上不孝。」
「他為百姓冤,為無辜者冤,此事與嚴法有關,但有過錯,但理應諄諄教誨,而非嚴法置,也算不上不忠。」
「百姓民怨,當為各地員之責,老陳想問問孫儒,為何百姓寧可相信許清宵,也不相信堂堂之大儒?莫要說什麼許清宵蠱人心,一個區區儒生,拿什麼蠱人心?難道大儒說話還沒一個儒生說話有用?此為不義嗎?」 (5,0);
「至於聖意之說,朱聖有言,後世出才,難道說出不同的立意,就是不仁嗎?」
「天地一切,周而復始,朱聖也並非天下第一聖人,即便是聖人在世,也希見到更加有才華之人出世。」
「孫儒之言,王景之言,是否過於偏激?」
大殿,安國公的聲音很平靜,但卻將孫儒的進攻,化解的乾乾淨淨,為許清宵洗的乾乾淨淨。
儒皆然皺眉,一個趙巖出來攪局就算了,沒想到安國公也出來攪局,這幫武當真是手段卑鄙。
只是心裡不爽,朝堂上不能表現出來,只能老老實實等孫儒開口了。
片刻後,孫靜安之聲再次響起。
「安國公之言,老夫能夠理解。」
「但無論如何,頂撞大儒,不敬聖意,不尊皇權,還是無法改變。」
孫靜安再次開口,依舊是抓住這三點,堅持抨擊許清宵。
然而安國公卻搖了搖頭。
「不敬聖意有些言重。」
「他許清宵也是讀書人,若真不尊聖意,怎可能為讀書人?又如何寫出絕世文章?」 (5,0);
「若是孫大人不喜,大可讓陛下擬一道聖旨,待他來京城之後,去大魏文宮,為聖人燒香,也算是以正自。」
「至於頂撞大儒,再讓他親自去致歉,也算皆大歡喜,既留有大才,又能化干戈為玉帛,豈不哉?」
「陛下,您意下如何?」
安國公笑道。
他屢屢出言幫助許清宵,原因是三點。
其一,許清宵是大才,天機臺過消息,許清宵命掌兵伐,或許以後能武,算是種下善果。
其二,皇帝看樣子也不希鬧得太大,當然這只是自己猜想。
其三,噁心噁心這幫儒也是好事,這幾年北伐之事,被儒氣了多次,還歷歷在目。
所以他一直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這朝堂爭鬥,就是把一件事拿出來,各自拿出自己的想法,不想要解決,那就一直扯,扯到非要解決的地步再來解決。
想要解決很簡單,你退一步,我退一步,事就辦好了。
安國公也不是完全為許清宵開罪名。
方才所說,讓許清宵去找嚴磊致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0);
也算是沒有損儒家面子。
算是自己退了一步。
至於答不答應,就看孫靜安的意思了。
大魏帝沒有說話,只是將其目落在了孫靜安上。
若是他沒什麼異議,就按這個來。
若是他有異議,就聽聽看。
孫靜安緩緩搖了搖頭。
隨後看向帝道。
「陛下,安國公惜才,臣,明白,也敬重,只是道歉若有用的話,還需要律法作甚?」
「嚴儒已經被氣至臥病,再讓許清宵前去,豈不是加重病?」
「臣認為,此人必要嚴法,發配邊疆或許有些嚴酷,念在他大才,剝奪功名,牢獄十年。」
「陛下覺得如何?」
孫靜安開口,他思考一番,也算是退步。
至於安國公解決辦法,想草草了事,自然不行。
許清宵必須要到懲罰,而且是極為嚴重的懲罰。
只是此話一說。
安國公再次出聲。 (5,0);
「一場誤會,鬧得如此之大。」
「孫大儒,您覺得有必要嗎?」
「大魏北伐之後,人才缺失,只要不是犯了大錯,理應該得過且過。」
安國公如此說道。
可孫靜安卻緩緩道。
「安國公,一生征戰,老夫佩服,可文人之事,安國公還是不要手,不尊聖人,對我等來說,是天大的事,並非是國公口中的小事。」
孫靜安不想與安國公繼續扯皮了。
他話說的很絕,甚至帶著一些其他意思。
聲音響起。
安國公也不由冷笑。
「朝堂之上,就是朝堂的事,還分什麼文人不文人?」
「陛下,老臣認為,嚴法過於殘酷,實在不利於大魏發展,老臣建議,小懲大誡,以教誨為主,懲戒為輔。」
安國公開口。
既然不好好說話,那就繼續槓。
反正輸贏我都沒壞。
「陛下,此事涉及天下文人,若不嚴懲,難以安天下文人之心。」 (5,0);
「還陛下明鑑!」
「嚴懲許清宵。」
孫靜安直接開口,接著跪在地上,朝著帝一拜,態度堅決。
下一刻,幾乎一半的儒出列,跪在地上大聲道。
「還陛下明鑑。」
他們齊齊開口,懇求皇帝下令。
至於沒有出列的一半,倒不是說支持許清宵,而是朝堂上的規矩,任何事,都不能傾巢而出,萬一真惹上麻煩,至還有部分人能夠保留下來。
不至於全軍覆沒。
「陛下天下文人又不是全是朱聖門徒,再者許清宵也並無大錯,就這般嚴懲,反倒是會傷了天下文人之心,如今大魏,求賢若,非常時期,非常對待。」
「懇請陛下法外開恩,從輕發落。」
安國公脾氣也上來了,一番話說完,也跪在地上。
很快一大半的武也紛紛跪下,有模有樣地學著。
兩邊直接槓上了。
但這是常態,甚至武帝在世之時,還發生過雙方之事。
「侮辱聖人,在國公口中,竟不是大錯?」 (5,0);
孫靜安看向安國公,語氣冷冽道。
「聖人之意,的確不可辱,但許清宵並非是朱聖門徒,他即將要明意。」
「說句不好聽的話,若是許清宵明意功,而且的確不是朱聖之意,那就不存在任何有辱聖人之言。」
「至於頂撞大儒,更是無稽之談,非朱聖之意,頂撞就頂撞了,我雖不是儒生,但也閱覽聖書,貌似天下群書之中,哪怕是聖人自傳。」
「也沒有說過大儒之言,就一定是對的吧?」
安國公也是老狐貍一個。
瞬間從中找到破綻,給予回擊。
畢竟這件事,本就是雙方皆有過錯。
許清宵存在問題,嚴磊也存在問題。
無非就是許清宵沒有大儒品位,也顯得年,不尊長輩是錯。
但嚴磊倚老賣老也是錯。
我好聲好氣跟你說,你不聽是吧?
那行。
索,既然這件事上撕破了臉,反正互相看互相不順眼已經很久了。
那就直接攤開了說,不必這麼拐彎抹角。 (5,0);
你說許清宵不尊重聖人?不尊重大儒?
可若是許清宵不走朱聖之意,這個說法就不立。
那就沒有任何懲罰了。
此言一出。
孫靜安繼續開口。
「安國公所言極是,倘若許清宵明意非朱聖,立意也非朱聖,的確是空談。」
「可安國公又怎能知曉,許清宵不是立朱聖之意呢?」
孫靜安回擊道。
這話一說,安國公有些沉默了。
但很快,安國公繼續開口道。
「老夫聽聞許清宵說要三日明意,三日時間不長,不如等等看,看看許清宵是否能明意。」
安國公回答道。
只是孫靜安搖了搖頭道。
「他剛剛晉升八品,三日明意,本不可能,不過是一時胡話。」
孫靜安如此說道。
不認為許清宵能做到。
「那萬一呢?」
「這天下哪裡有什麼不可能的?孫大儒未免有些太自負了吧?」 (5,0);
安國公平靜道。
「你這已經是胡攪蠻纏了,不與你說。」
孫靜安不想搭理安國公,而是看向帝道。
「陛下,許清宵之惡,為窮兇極惡,若不嚴懲,天下文人皆然不服。」
「請陛下嚴懲。」
孫靜安依舊要求嚴懲許清宵。
無論如何都要嚴懲。
「陛下,老臣不認同,此事如老臣方才所說,只是一場誤會,退一萬步來說,當真不是誤會,那又如何?」
「他許清宵又非明朱聖之意,之前種種,也算不上什麼大錯。」
「臣建議,不如給許清宵三日時間,看看他能否明意,若是三日明意,此事就算了。」
「若是不能,到時再議,也不是不行。」
安國公如此說道,目也看向帝。
雙方勢力是徹底槓上。
但到底如何,還是要看皇帝抉擇。
「允!」
半響。
帝的聲音響起。 (5,0);
僅僅只是一個字,便決定了這件事。
「陛下,不可啊,此事......關乎天下文人,關乎聖人之威。」
「還陛下三思,若不大懲許清宵,臣等還有什麼面面對天下文人?面對朱聖門徒?」
「若如此,還不如告老還鄉,也免得被天下文人嗤笑。」
孫靜安開口。
到了此時,他直接放大招了。
用告老還鄉來皇帝。
這也是自古以來,所有儒最喜歡做的事。
「放肆。」
當下。
帝之聲響起。
簡簡單單兩個字,滿朝文武齊齊跪下,不敢出聲。
孫靜安太過於激進了。
拿這個來威脅皇帝,實在是有些激進。
「陛下!」
「臣,為的是天下文人,為的是大魏王朝,若有人辱聖人,不懲戒。」
「那禮樂崩壞啊!」
孫靜安大聲說道。 (5,0);
鐵了心要嚴懲許清宵。
大殿安靜。
帝沉默。
百也沉默。
過了半響。
帝的聲音緩緩響起。
「三日,看看許清宵能否明意。」
「若能明意,如安國公所說,許清宵並非是朱聖之意,此事到此為止!」
「若明意之後,是朱聖之意,則為辱聖,依法置。」
「若未能明意,三日之後,再來定奪。」
「退朝。」
帝開口,意簡言駭。
孫靜安想再說什麼,可也意識到,陛下開口,就不能在強求什麼了。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百高呼,隨後起退朝。
這一次爭鬥,沒有什麼結果,但眾人都知曉,天大的力落在了許清宵上,安國公為許清宵做了很多,可到底能不能幫到許清宵。
還是得看許清宵能否立意功。
也就在此時,百快離開殿門時,帝的聲音,又緩緩響起。 (5,0);
「若許清宵明意,並非朱聖之意,孫卿,的確可以考慮告老還鄉。」
聲音響起。
百一愣,眾儒臉皆變。
猜你喜歡
-
完結23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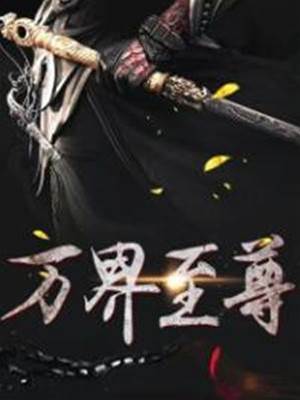
萬界至尊
一縷劍光鎖住八道絕世兇魂,窮奇、燭龍、鯤鵬、螣蛇……少年體內,為何隱藏著此等秘辛?封印鎖鏈,層層破碎。燭龍之目,窮奇之力,鯤鵬之翼,螣蛇魅影……帶給他一項項逆天神通。這一生,隻問今朝,不求來世。這一劍,刺碎淩霄,踏破九天!
677.5萬字8.18 162906 -
完結1440 章

玄幻,我能無限頓悟
蕭云的系統只會一個功能——頓悟!體質平凡?頓悟混沌體!功法難修?頓悟圓滿境界!神通難修?頓悟圓滿境界!沒有什麼是頓悟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頓悟十次,百次……
282.7萬字8 290835 -
完結1059 章

混沌天經
天蒙宇宙的七大絕世功法之中,唯獨混沌天經只有八層心法,其他的六大絕世功法都是有著九層完滿的心法。但是混度天經的威能卻足以和其他的六大功法相媲美,傳說,誰能夠創出混沌天經第九層心法,就能成為宇宙中的無上存在,可超脫宇宙,達到不死不滅之境界。
313.1萬字8 16949 -
完結496 章
史上最強輔助:幫人就變強
【靈氣復蘇+文風輕快熱血+系統+不后宮】沈天穿越到靈氣復蘇的藍星,發現自己竟然是個弱雞輔助。正當他對生活絕望之時,最強輔助系統激活,只要幫人,就能變強!從此,沈天走上了一條‘助人為樂’的道路。九天大圣:在我認識的人中,就屬沈天最為熱心,也最為低調!人屠將軍:如果遇到一個長得很帥,但只會躲在隊友身后的家伙,記住拔腿就跑!異族首領:誰敢無故招惹沈天,直接逐出族群!簡介無力,請移步正文…
90.1萬字8 294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