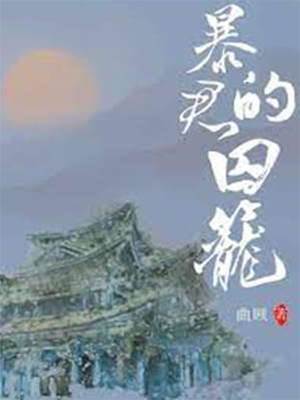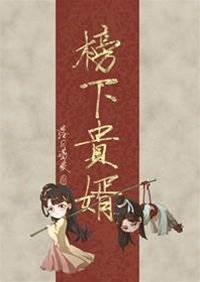《燈花笑》 第一百四十五章 天才醫官
“咳咳咳——”
手上茶水因劇烈咳嗽灑了一些出去,他手忙腳拭上茶漬,那張總是變不驚、遊刃有餘的笑臉終於有了裂,難得生起來。
陸曈覺得這畫面倒是順眼多了。
裴雲暎整理好周遭,適才看向陸曈,不可思議地開口:“你在說什麼?”
縱是醫者不分男,縱是陸曈此人從來也與、靦腆掛不上邊,但他好歹也是個青年男子,而一個年輕姑娘在屋裡同他如此直白說出此事,未免也太驚世駭俗了些。
陸曈覺得他這幅模樣倒有趣,遂奇道:“裴大人也不知道?看來真是了。”
“我當然不知道,”他狼狽地拂一下上茶渣,“你怎麼知道?”
陸曈不作聲。
“你……”
“我平日行診用針,”陸曈打斷他的話,敲敲桌上醫箱,“多看一針看一針沒什麼區別,裴大人不必出那副神。”
這話說得刻薄至極,如若金顯榮本人在此,只怕會被氣得一命嗚呼,偏說得一本正經。好像毫不覺得其中諷刺。
裴雲暎以手抵住前額:“別說了……”
見他如此,陸曈反倒覺得新鮮。這位指揮使大人看上去遊刃有餘,凡事舉重若輕,但原來聽不得這樣的話,白白浪費了一副俊秀皮囊。
真是人不可貌相。
裴雲暎靜了一會兒才開口,神有些複雜:“你真的……”
倒不是他對醫行診有什麼偏見,實在是金顯榮德行有虧,而陸曈又慣來不是一個逆來順之人,若說被金顯榮佔了便宜,似乎不大對勁。
“當然是假的。”陸曈道。
裴雲暎一怔。
陸曈不知他心中所想,只道:“裴大人也知道,對我來說,男子軀和死豬沒什麼區別,看不看不重要。再者他的病雖麻煩,但並不難治。裴大人也不必過於心。”說著把那隻猊狻鎮紙在方才寫好的藥方上:“方子在這裡,大人照我說得煎藥給他們服下就是,七日後我會再來。”
Advertisement
說到此,陸曈停了一停,又默默看向裴雲暎。
裴雲暎注意到的目,神一頓:“怎麼?”
陸曈頷首,語調坦然:“金大人之病癥,男子上了年紀多有此患。若是裴大人將來也有此麻煩,需要幫助,不妨找下。以我們二人,我也會替裴大人保守的。”
此話一出,屋中一片死寂。
有一瞬間,陸曈覺得他那張俊的臉是僵住了,彷彿在竭力維持雲淡風輕,良久,裴雲暎鎮定地開口:“多謝,但我不需要。”
“是麼?”陸曈便出一個惋惜的神,“真是憾。”
方說完,門外就傳來一個輕快聲音:“什麼事憾啊——”
段小宴從外頭探進個頭,見是陸曈也愣了一下:“陸大夫,你怎麼在這?”
陸曈不再多說,背上醫箱,只衝他二人淡聲道:“我先回去了。”
揹著醫箱徑自出去了,段小宴看著背影撓了撓頭,道:“奇怪,我怎麼覺得陸大夫今日比往日高興?是遇上什麼喜事了?”
他又轉過頭,似才想起方才看見的一幕,指著陸曈坐過的那張椅子激道:“不過哥,你居然讓坐你的椅子哎!你平日不是不讓人你的東西嗎?”
裴雲暎素有潔癖,最不喜旁人他事,那張椅子除了他自己誰也不敢坐,偏今日瞧見陸曈坐了,沒猜錯的話,陸曈還用了裴雲暎的紙筆。
嘖嘖嘖,對可真夠寬容的。
半晌無人回答。
段小宴轉過臉,瞧見裴雲暎坐在桌前,一手扶額,一副頭痛模樣。
年好奇心頓起,湊上前去:“你們剛剛在說什麼,陸大夫憾什麼?”
裴雲暎沒有抬頭,只手將他湊來的腦袋推到一邊,冷冷道:“閉。”
Advertisement
……
從殿帥府出來,陸曈沒再去別的地方,徑自回了醫院。
堂廳裡,醫正常進正囑咐別的醫奉值的事,見陸曈回來,三兩句打發了來人,走到陸曈面前詢問:“陸醫這是給金侍郎看過診了?”
陸曈點頭。
他打量一下陸曈:“沒出什麼事吧?”
陸曈道:“沒有。”
常進便鬆了口氣。
他是個老好人,當時春試,陸曈的考卷是他第一個批出來的完答卷,對陸曈總是存了幾分特別關注。崔岷要陸曈給金顯榮行診時,常進還擔心了好一陣,畢竟金顯榮那個德行……整個醫院就沒幾個人願意去行診。
他都已經做好陸曈哭哭啼啼回來、他腆著臉去求院使自己頂上差事的準備,誰知見陸曈舉止如常,神與尋常沒半分不同,實屬意外。
“陸醫,”常進道:“有件事得告訴你,曹槐突風寒,臥床不起,告了假,這些日子恐怕不能與你一同去金府了,”他覷著陸曈臉,“我會稟院使另外指派一名醫同你一起……”
不等他說完,陸曈就打斷他的話:“不用了。”
常進一頓。
“我今日瞧過金大人的病,並不嚴重,一人足以,多一人反而麻煩。不必為了我一人耽誤大家時日。”
常進想好的說辭霎時全堵在間:“……是嗎?”
就算不是金顯榮,尋常行診,多一人分擔也是好的,陸曈卻就這麼拒絕了他一片好意?
甚至看起來還有點嫌棄。
陸曈衝他點了點頭,又揹著醫箱進院裡去了。
常進站在原地,看著的背影半晌,喃喃開口:“不愧是春試紅榜第一,這驗狀科答得完的……”
“果然不是普通人。”
忽而又想起告假的那位,臉黑了下來。
Advertisement
“早不風寒晚不風寒,偏偏這時候臥床。”
拂袖而去。
……
“阿嚏——”
曹府裡,躺在床上的曹槐忽而打了個噴嚏。
屋裡小廝見狀,憂心忡忡開口:“爺不會真著涼了吧?”
“去去去,”曹槐面不耐:“來晦氣。”
今日一早,他沒有與陸曈一同去行診,回到醫院後就同崔岷告了假。春日氣候變化,醫院上風寒之人不,崔岷也沒心思去察他一個新醫究竟是不是裝病,於是順順利利回了府。
曹槐就是故意的。
他自小也不是什麼心寬廣之人,春試那日,陸曈當著貢院同窗前令他下不了臺,曹槐耿耿於懷了好久。崔岷當初點陸曈去南藥房時,他暗暗幸災樂禍,誰知陸曈不知走了什麼運道,竟被藥院院使邱合看中,兜兜轉轉又回來醫院。
崔岷不知是故意還是怎的,竟點他與陸曈一同去給金顯榮行診。老實說,金顯榮此人不僅子避之不及,男子見了也厭憎。他去給金顯榮行診的這一月,每日都被金顯榮冷嘲熱諷,挑刺,對方那腎囊癰又格外難治,眼見著沒有起,金顯榮耐心一日日消耗殆盡,沒想到這時候來了個冤大頭,恰好將這燙手山芋甩出去。
所以他毫不猶豫告了假。
這算是,既擺了難纏的差事,也給那陸曈添了堵,真可謂一舉兩得。
曹槐靠著床頭哼笑一聲,眼中滿是不屑。
陸曈裝出一副清高誰也不放在眼裡的模樣又如何,總歸是個沒有份背景的平人,說不準給金顯榮治上幾日,就如先前翰林醫院的那位醫,為金顯榮的又一房小妾,給人做了奴才。
這樣想著,心似也好了許多。曹槐雙手枕在腦後往後一仰,只看著頭頂的帳子,彷彿已看見陸曈跟在金顯榮後卑躬屈膝的模樣,滿意地喟嘆一聲。
Advertisement
小廝見狀,小心翼翼開口:“爺這回打算休養多久?”
“風寒嘛,可不得多養幾日。”曹槐一笑,“再等等吧。”
……
只是去金府上給金顯榮行診一趟,就引出各思量,不過其中波瀾暗流,陸曈並不知曉,也不太在意。
夜裡醫院人都睡了,陸曈和林丹青走在藥庫的長廊。
金顯榮的病癥雖已分明,但要治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不僅換藥方,陸曈還打算做味新藥。有些藥材需要藥院分撥,有一些尋常的,醫院的藥庫就有。
林丹青本還以為今日陸曈去金府,多半不太愉快,沒料著回來後見陸曈神如常,又追問幾句,適才漸漸放心。陸曈說要去藥庫拿材料,林丹青便自告勇與一同前去。
“姓金的多半是腎囊癰後吃了苦頭,才不那麼囂張了,我聽我爹說,他從前荒唐起來時,路過的雌犬都要兩把佔便宜。”說起此事,林丹青與咬耳朵,“恐怕是老天爺都看不過眼,才他得了這個病,說實話,要不是你是去給他治病的醫,我真不得他是得了不舉,一輩子不能禍害人才好。”
是言辭無忌,陸曈只笑笑,低頭從各藥櫃裡挑揀自己要用的藥草。
林丹青幫著一起撿,一面問:“不過陸妹妹,你今日還去了殿帥府,怎麼樣?”
陸曈:“什麼怎麼樣?”
“那裡的衛怎麼樣啊!”林丹青道:“聽說京營殿帥府的衛,當初都要經過重重選拔,不止看武功,還要看個頭長相的。說是全盛京的最英俊的男子都在京營殿帥府了,你看他們那位指揮使也能瞧出來端倪。你今日去了,看見了如何,是不是全都是男子,英武麼?”
陸曈合上藥屜:“你想去,我同常醫正說一聲,讓你替我的差事。”
一心想著戶部的戚玉臺,兩頭跑是浪費力,何況每次面對裴雲暎的試探也並不令人愉悅,倒不如將此事讓給林丹青,做個人之。
林丹青一愣:“你也太大方了。”想了想,又搖頭:“我家一位老祖宗說過,子多瞧瞧英俊男子也算是另一種保養之道,使人心開朗,順氣愉悅。你那頭看了金顯榮那張臉,了眼傷,另一頭瞧瞧殿帥府的男子修補一下,也算抵消傷害。”
“陸妹妹,為朋友,我是絕對不會搶你藥方的!”
陸曈:“……”
世上之事,果然甲之糖乙之砒霜,避之不及的,反而了別人裡的靈丹妙藥。
又說了幾句話,需要的藥材已全部撿進竹籃了,陸曈與林丹青出了藥庫,打算回宿院,才走到藥庫院門口,忽地聽見前方有腳步聲傳來。
接著,一個音兀地響起:“什麼人?”
二人循聲去。
就見石階遠,槐花樹下燈籠灑下的暈黃地裡,不知何時盛多了兩條漆黑長影。
一條短些,拖在一個青小藥的後。至於另一條……
是個姿清瘦的青年男子,眉眼清雅。穿一淡青織錦長袍,烏髮以一隻青竹簪綰髮髻,似雲中孤鶴,又如夜中一株蕭蕭青竹,自有一清遠雅正之氣,自遠慢慢朝陸曈二人行來。
行到院門口石階前便停步,林丹青似乎與這人認識,趁著燈籠看清了這人的臉,忙開口道:“紀醫。”
紀醫?
聽起來像是醫院中的醫,可他的袍又不是醫使的藍袍。
陸曈沒說話,只跟著低頭行禮。
青年目掠過陸曈手中竹籃:“這麼晚了,怎麼還撿藥材?”
林丹青笑道:“陸醫負責行診的病人病有些棘手,打算用這些藥材研製新方,看能不能做點新藥出來。”
翰林醫院的醫們從來求穩,所謂新藥極有人嘗試。聞言,“紀醫”的男子一怔,神意外地看向陸曈。
這一看就頓住了。
子站在藥庫院子的石階下,夜風吹水藍的角,那藍也是淡淡的一抹,如主人斂著的眉目般安靜。
他突然蹙了蹙眉。
陸曈能覺到對方審視的目落在臉上,若微涼晚風,接著,聽見對方的清冷的聲音傳來。
“我們是不是曾在哪裡見過?”
陸曈忽地一怔。
有什麼東西從心底漸漸浮起,像是藏在漆黑水底的一顆並不算麗的暗石,猝不及防下重見天日,平靜的水面也漾出淺淺波瀾。
微微攥指尖,抿著不說話。
男子又往前走近了一步。
陸曈子微僵。
對方微蹙著眉仔細盯著的臉,像是要將的五看個清楚分明。從眼前平視過去,能瞧見他領繡著的細緻花紋,以及清淡的苦藥香。
他盯得很久,久到連一邊的林丹青都覺出不對勁來,正要出聲打斷,一邊的小藥倒是不知想到什麼,眼睛一亮,出聲提醒:“公子,您與這位醫見過的,先前在雀兒街,那天下雨,您被人傘上雨水弄髒了服,還耽誤了筵席……當時弄溼您服的,就是這位醫嘛!”
此話一出,站著的兩人皆是一愣。
眼前人領的花紋也像是被夜氤氳得模糊,模糊著模糊著,便了雀兒街那場悽悽的秋雨。
那時候貢舉案剛過沒多久,劉鯤死了,王春芳瘋了,兩個兒子關在囚籠裡,看過了劉家的下場,卻在轉時被戚家馬車所驚,傘尖不小心到了側過路人。
陸曈還記得那時候對方上一雪白袍站在細雨中,遠得像是水墨畫上一個不真切的淡影,他從邊走過,在人群中漸漸瞧不見,如一場雨後溼的幻覺。
如今幻覺變了真實,在夜裡凝固更沉寂的影,
一時間,誰都沒有說話。
林丹青察覺出古怪的氛圍,忍了忍,終於還是忍不住扯了下陸曈的袖角,衝青年出個笑,道:“紀醫,天不早,沒什麼事的話,我們就先走了。”
對方適才回神,沒再說什麼,對二人淡淡點了點頭才帶著藥往石階上走去。
待他走後,林丹青才鬆了口氣。
陸曈狀若無意地問:“剛才那人是誰?”
“紀珣。”
“紀珣?”
林丹青詫然:“你沒有聽過紀珣的名字嗎?不應該啊。翰林醫院那幫老頭子們日把他名字掛在邊,什麼‘未及冠就已醫超群’‘縱然他家裡人不是學士,尋常人家也定能青囊致富’……這些話在太醫院進學時,聽得我耳朵都起繭了,”又嘆口氣,“好好一個翩翩公子,愣是讓我看見他的臉就覺得厭煩。”
陸曈問:“他家裡是學士?”
“可不是麼,他父親紀大人乃觀文殿學士,他祖父乃翰林學士,家兄是敷文閣直學士,一家子文,可是這位天才醫呢,偏偏醉心醫,不去如他爹一般從仕,反來禍害我們。”
“陸妹妹你不知道,從前不曾春試時,每年校驗,我都是太醫局第一,今年春試你出現了,我了第二,咱倆也算這醫院杏林雙驕吧,可人家呢,還未及冠就能被太后娘娘宣宮中奉值,在醫院掛了個虛職。”
“你我是答題的,他卻是出題的。今年太醫局春試那些看著就令人髮指的題目,可都是出自於這位紀醫之手。瞧瞧,長這麼一張似水的臉,怎麼心腸就這麼狠毒呢?”
一口氣說完一長串,也不覺累,又長嘆了口氣:“我聽說他前些日子出門去了,還以為要過段時日才回來,沒想到這麼早就回來了。這下可好,時不時出點奇奇怪怪的題目來考人,咱們這些新進醫的好日子,怕也快到頭了!”
自惆悵著,陸曈卻回過頭,往石階那看去,夜裡已瞧不見兩人影子,只有搖曳的槐樹花枝隨風微。
夜風脈脈吹著,一朵槐花便被風打落,搖搖晃晃打著璇兒飄至人前,又被青靴踩過。
行走的步子突然一滯。
“不對。”
走在前面的小藥一愣,下意識看向側人:“公子,哪裡不對?”
“地點不對。”
青年停下腳步,蹙眉道:“我第一次見的地方,不是雀兒街。”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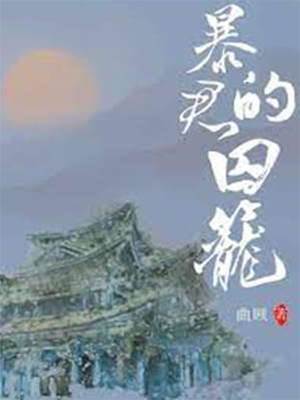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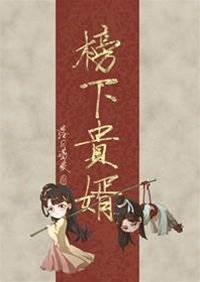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