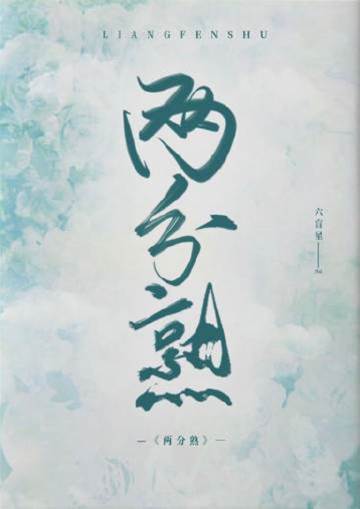《強撩!暗戀!總統閣下他溫柔低哄》 第138章 仿若神明,沾染汙穢
一句話。
男人像是頭暴怒獅子,瞬間就被順了。
人群熙攘。
可這一刻,他卻隻能聽見清淺溫的嗓音。
他緩緩地握住腰間的小手,溫和的應:“嗯。”
兩人牽著手上車。
金歐陸在眾人唏噓不已的視線中緩緩離去。
沈慕白看著那輛車離去的背影,踉蹌著站起,眼神冷,手背狠狠的拭角的跡。
旁邊有人關心的走上前,“沈先生,你沒事吧?要不還是先去醫院上點藥吧?”
沈慕白本不理會,一側眸,發現竟是一張肖似寧蘅的臉。
酒意,蠶食了他的神經。
他半是清醒,半是恍惚。
昏黃的燈下,眼底含著無限繾綣的意。
喬諾被這眼神看的臉紅心跳:“你喝多了酒不能開車,要不,我帶你去?”
……
Advertisement
金歐陸行駛在通幹道。
約莫四十分鍾後,才抵達銀河灣別墅樓下。
現在大概是晚上十點半。
別墅雖開著燈,但是傭人並未在客廳忙碌,傅瑾州停車後,子倚靠在椅背,眉眼間帶著一抹不同於往常的倦。
車廂很安靜。
良久。
寧蘅輕輕出了聲:“我們上去吧。”
傅瑾州側眸看向,聲線含著一沙啞:“嗯。”
兩人下車。
一前一後的進了客廳,上樓,進臥室。
到了臥室後,男人單手扯了扯頸間的領帶,丟在一邊,小姑娘忽然牽著他的手,帶著他走向浴室。
明明很輕的力氣。
傅瑾州卻甘之如飴,亦步亦趨乖巧的跟在後。
到了浴室,孩拿過巾,沾熱水,然後抬手,緩慢用巾拭他的臉頰。
Advertisement
男人的下頜,冷白的腕骨,甚至腕骨間的佛珠上,染了。
仿若高高在上的神明,沾染汙穢。
傅瑾州沒有說話。
漆黑幽深的眸就這麽灼灼的看著。
看著認真專注的拭過他的側臉,然後是脖頸,最後抬起他的手腕。
男人很乖很聽話。
出手任由著拭。
直到一切都拭幹淨了,寧蘅將巾擰幹淨,掛在一旁。
男人盯著的側臉,倏地掐著的腰,將抱到洗漱臺上。
寧蘅微怔。
男人俯,額頭抵著的眉心,黑沉沉的眼眸一瞬不舜的注視著,嗓音嘶啞:“阿蘅怕我嗎?”
怕?
寧蘅搖頭。
其實早就知道,他絕不像是表麵那樣的溫潤君子。
或許,剛才那才是他的真麵目。
但,即便是剛才親眼見證他失控,卻一點都不怕。
Advertisement
“真的?”
傅瑾州深眸的鎖住,呼出的熱氣吹拂在的臉頰,眸底迫切又擔憂。
“嗯。”
寧蘅很堅定的朝他點了下頭。
傅瑾州恍如得到救贖的旅人,心底幹涸猶如泉湧,他捧起的小臉,然後低頭吻了上去。
他生涼薄,殺伐決斷,滿手鮮,除了瑾硯和陸司兩家的混球,滿S國極有敢接近他的人,可他唯獨對小心翼翼,生怕會驚懼半分。
幸好。
幸好不怕。
寧蘅被吻的有點不過去,緩慢抬手,環住了男人的後腦勺。
這還是第一次主。
男人欣喜若狂。
直到將吻的臉頰通紅,男人一把將橫抱起來,大步向臥室方向走去……
落地窗外。
連綿的細雨,下個不停。
時而熱烈,時而溫和,雨水滴滴答答澆落在銀杏樹的枝椏之上,狂風暴雨淋了樹葉,許久也未曾停歇……
猜你喜歡
-
完結762 章

左少的深情秘妻
所有人都知道,許愿愛左占愛得死去活來。所有人都知道,左占不愛許愿,卻深愛另一個女人。直到幾年后,失蹤的許愿高調歸來。左占:許愿,我們還沒離婚,你是我的妻子。許愿笑得嬌媚:左先生,你是不是忘記,當年我們結婚領的是假證了?…
151.2萬字8.18 60403 -
完結183 章

強取豪奪:惹上狂野前夫
她本是豪門千金,卻因為愛上仇人的兒子,萬劫不復。他注定一代梟雄,竟放不下她糾纏不清。離婚之后,他設計讓她生下自己的骨肉,再威逼利用,讓她不許離開“安喬心,記住,不許離開!
50.1萬字8 3120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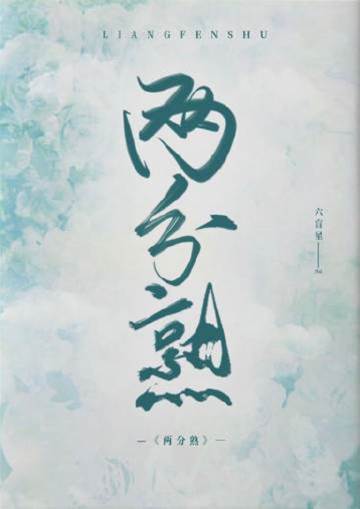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610 章

團寵小可愛:大叔,好好寵我
【馬甲+玄學+女強男強+團寵+娛樂圈】對女人過敏的大佬撿回來個女孩后將人寵翻天! “大叔,我喜歡這顆最大的全美方戒。” “全球鉆石礦脈都是你的。” “總裁,夫人把頂流女明星的下巴假體打斷了。” “她手疼不疼?還不多派幾個人幫她!” 墨冷淵:“我夫人是鄉下來的,誰都別欺負她。” 可眾人一層層扒小姑娘的馬甲,發現她是玄門大佬,拳皇,醫學泰斗,三金影后,…… 眾人瑟瑟發抖:這誰敢惹?
89.6萬字8.18 33866 -
完結211 章

夫人快復婚吧,總裁膝蓋跪爛了
五年愛戀,一年婚姻,她用盡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換不來他的另眼相看。后來她決定放過自己,選擇離婚。 回到豪門繼承家業。 白月光上門挑釁,她冷漠回擊。 將她和那個狗男人一起送上熱搜。 宋司珩這時才發現,那個只會在自己面前伏低做小的女人。 不僅是秦氏的大小姐,聞名世界的秦氏安保系統出自她手,世界頂級珠寶品牌的設計出自她手,第一個16歲世界賽車手冠軍居然也是她! “秦阮,你到底還隱藏了多少秘密。”男人將她比如墻角,對自己將她追回勢在必得。 她卻瀟灑將他推開,只留下一個瑰麗的背影。 “狗渣男,去死吧。”
39.2萬字8 1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