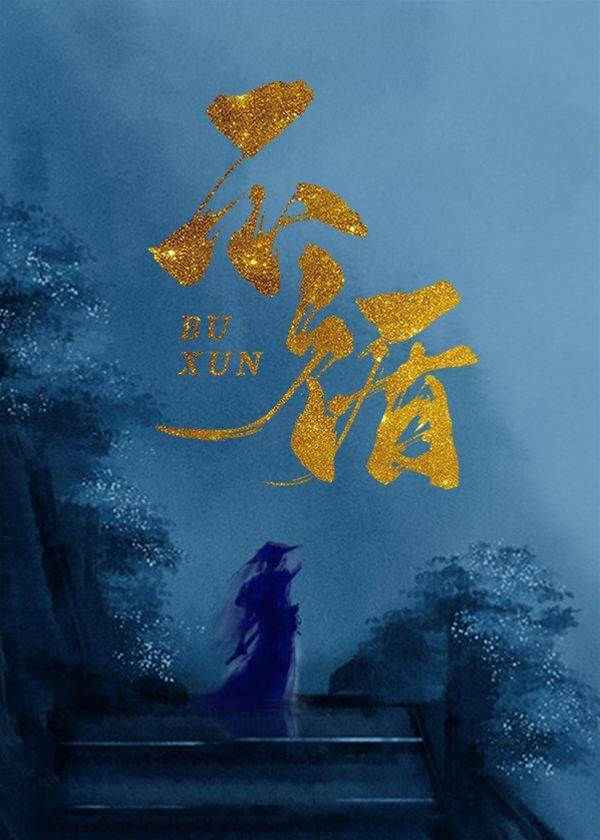《清宮熹妃傳》 第80章 風雨
淩若心頭一,子微微發涼,明明這一切都是年氏在幕後主使瓜爾佳氏所為,可現在年氏卻利用此事來挑起胤禛對的懷疑,且還質疑迷魂香的存在與功效,其用心不可謂不險惡。
年氏此人……機鋒暗藏且對胤禛子深為了解,遠比想像的更難對付。
胤禛略一思量後遲疑著道:“若兒,當時王保是你問的話,他緣何自盡你應該最清楚,既然素言有此疑問,你不妨說出來為悉疑。”
“是。”胤禛既然這麽問便表示他已起疑,淩若不敢遲疑起了好整以瑕的年氏一眼道:“王保固然是賭徒不錯,但也有家人,他對唯一的弟弟極好,為了弟弟可以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命。幕後之人正是抓住他這一弱點加以利用。”頓一頓又道:“若年福晉還有懷疑的話,那筐摻了迷魂香的銀炭還在,妾現在就可人取來當場驗證,看究竟是妾信口雌黃還是果有其事。”
“不必了。”說話的是那拉氏,隻見神溫和地道:“我相信淩福晉所言句句屬實,無須再驗,何況那迷魂香是徐太醫所驗,難道年妹妹還信不過徐太醫的話嗎?”
“徐太醫自是可信,妾就怕有些人連徐太醫都瞞過了。”年氏還待再說胤禛已抬手道:“行了,正如嫡福晉所言,此事一切明了無須再言,有那功夫,素言你倒不妨好好查查,府中究竟是何人先後要對兩位福晉不利。”
見胤禛已發話,年氏縱是百般不願也隻得怏怏作罷,在椅中欠道:“妾記下了。”
胤禛頷首之餘又緩了神道:“你不是總說兄長遠在杭州,一年也難得見上一麵嗎?此次亮工隨我回京,與皇阿瑪說起時皇阿瑪有意留他在京任職。”亮工是年羹堯的表字。
Advertisement
“當真?”年氏眼眸一亮,豔如花的臉上有無盡歡喜,自小隻得一位兄長,極佳。
“自然是真。”胤禛笑笑,正說話間狗兒走進來通稟說十三爺和徐太醫都到了,此刻正在書房等候。
“知道了,我這就過去。”胤禛說著站起來歉疚地看了那拉氏一眼道:“本還打算陪你一道用午膳,現在看來卻不行了。”
那拉氏是奉皇命所迎娶,雖從不是胤禛在意之人,但畢竟生兒育相經年,總是有幾分稀薄的在。
“正事要,何況貝勒爺已經回來難道還怕沒時間陪妾用膳嗎。”那拉氏永遠都是善解人意、寬容大度的,從不需要胤禛擔心,唯獨弘暉死去的那次,那拉氏失去所有理智,隻剩下撕心裂肺的痛。
胤禛點一點頭,大步往外走,眾人見狀忙起恭送其離去,在經過淩若邊時,胤禛含了幾許流笑意道:“老十三一早過來想是沒用過早膳,待會兒你下幾碗麵到書房來,上次在江南與十三爺說起你那放了桂花的長麵時老十三很是興趣,說回京後一定要親自嚐一嚐。”
“是。”淩若微笑答應,在胤禛離去後亦向那拉氏告辭離去,並未看到年氏邊的冷凝,但即使看到又如何,與年氏的嫌隙早已深到無法可化。
且說淩若回到淨思居後,親自去廚房下了麵然後又取了桂花灑在麵上,然後才仔細端了一道去書房,然進門時所見的況卻將嚇了一大跳,因為看到胤禛除下衫之後的背上竟然有一個長達數寸深可見骨的傷口,雖已經開始愈合,但看著仍然很可怕,在傷口附近甚至還有已經結痂的黑跡。容遠正仔細用溫水清洗傷口將那些跡拭去,然後往傷口上灑一些白藥,胤祥則不住地在一旁走來走去,神憤然。
Advertisement
胤禛竟然傷了?淩若被這件事驚得險些將端在手上的托盤給扔掉,匆忙放下快步來到胤禛邊急切地問道:“出什麽事了?為什麽四爺會傷?是什麽時候的事?”
“不礙事小傷而已,倒是沒料到你這麽快就過來,把你給嚇到了。”胤禛不在意地道,但下一刻胤祥已經氣衝衝地道:“什麽小傷,當時四哥你差點連命都沒了,要不是亮工他及時趕到咱們兄弟未必有命站在這裏,饒是這樣四哥你也休養了近一個月才能再趕路,那些不開眼的那些山賊,要不是跑得快我非要他們一個個人頭落地不可。”
那廂容遠已理好傷口換了幹淨的紗布重新紮好後道:“這毒並不利害,隻是當時治傷的人不知毒理沒有及時將毒去幹淨,貝勒爺隻要按微臣留下的方子及時服藥,不出半月當能將餘毒悉數去除,隻是這傷口要完全愈合卻要慢慢來了。”
“勞煩徐太醫了。”胤禛點點頭,示意狗兒送容遠出去,淩若幫著他將衫重新穿好後憂心忡忡地道:“四爺,還疼嗎?”原來胤禛上真的有恙,當時溫如言說胤禛坐姿有些怪異時,還笑言溫如言過於敏,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真是過於心了。
胤禛拍拍的手安道:“真的不礙事了,再說徐太醫不是也說無礙了嗎,難道你連他的話也信不過?”
淩若聞言稍稍安了心,想到胤祥適才的話道:“四爺之所以路上耽擱便是因為上這傷嗎?究竟是何方山賊如此大膽竟敢傷害四爺?”
“一說起這個我就來氣。”胤祥大聲嚷道:“明明去的時候一切都太平無事,可回來時卻在江浙邊境遇到一夥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賊,張口就要我們留下所有東西,還出言不遜,滿口汙穢。咱們本是想盡快回來向皇阿瑪覆命,所以輕車簡行不曾搞什麽儀仗,不曾想咱們堂堂兩個阿哥卻被人當羊給截了,這欽差聖旨令牌全在行囊怎能給他們,所以二話不說便打了起來。原以為是一群烏合之眾,可真打起來時卻發現一個個全是武中高手,刀刀下狠手,最可恨的是還在兵上淬了毒,我被他們在手上劃了一道,四哥更是了重傷,幸好晚我們一步出發的年羹堯與他的親隨及時趕到,打跑了那幫子人,否則小嫂子怕是見不到咱們了。”
Advertisement
胤祥不是說喪氣話,他至今還清晰記得四哥被砍倒在地的模樣,他當時整個人都快瘋了,拿了刀沒命地往山賊那裏衝,全然不顧自己命。
淩若聞言擰了長眉道:“妾聽聞山賊之中有一條不文的規矩,劫人隻為求財,若非萬不得已不可傷人命。這既是為避免已鷲傷之過甚,也是為免傷人太多引來府圍剿。且江南一帶素來治安甚好,怎會出現這樣一撥窮兇極惡的山賊,還在刀上淬毒,倒有點像……”後麵的揣測太過大膽,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不知是否該說出口。
“是否瞧著有點像借搶劫之名故意要我二人的命?”誰想胤禛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便張接過淩若的話,“我與老十三在路上時就曾想到過這個可能,可惜等老十三與江寧知府帶兵去圍剿的時候,那些山賊已經逃得一個不剩,像是早已料到會如此。”
“究竟是誰那麽大膽敢暗算我們,讓我知道非扭斷他的脖子不可!”胤祥咬牙切齒地道。
胤禛站起來沉沉道:“等著吧,總有那一天。”此次江南之行了太多人的利益,難免有人懷恨在心鋌而走險。有仇不報非君子,他胤禛從不是什麽善男信,既敢他就要有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
“罷了,先不說這個,吃麵吧。”胤禛擺一擺手,指了已經有些發漲的銀麵道:“這便是上回與你說起過的桂花麵。”
胤祥依言端起放了桂花的麵吃了一口,點頭道:“果然清甜可口又混有桂花的香氣,好吃得很。”在將自己與胤禛那碗麵都下了肚後方才抹一抹誇張地道:“小嫂子這麵可比宮裏廚做的還要好吃,讓人吃了還想吃。”
Advertisement
“十三爺若喜歡,往後多過來吃就是了,幾碗麵妾還不至於吝嗇。” 淩若抿一笑收起碗筷道: “四爺與十三爺慢慢談事,妾先告退了。
待淩若退下後,胤祥隨手拿起書案上的琉璃鎮紙把玩道:“四哥,昨個兒咱們麵聖的時候,皇阿瑪有意清理戶部欠銀,你說誰會接這個差事?”
“這又是一個得罪人的差事啊!”胤禛著後梳得齊整的辮子歎道:“依我看怕是沒一個會接這燙手山芋。對了,老八快回來了吧?”
琉璃鎮紙被胤祥拿在手裏拋上拋下,“嗯,也就這幾日的事吧,聽說他在河南賑災的差事做的不錯,那些個災民都被妥當安置了下來,且沒發疫,據我得來的消息,皇阿瑪有意封他為郡王,嗬,這下子他可就更得意了。”胤祥在諸阿哥中隻與胤禛親近,旁的皆隻是一般,說到此他略有些不屑地道:“他能有銀子賑災還不是靠咱們在江南剝那些鹽商的皮,險死還生好不容易回來了,可皇阿瑪什麽封賞都沒有,想想真是讓人氣不過。”
“咱們辦差又不是為了封賞,有什麽可氣的。何況……”胤禛著屋頂上描金畫銀的圖案道:“我相信皇阿瑪心中自有數,他不封賞自有他的理由。”
胤祥不在意地聳聳肩,他本就是無所謂之人,隻是替胤禛不值,頓了頓又鄭重道:“四哥,若是皇阿瑪讓你去追討欠銀你可萬萬不能接。”
“怎麽,拚命十三郎竟然也有怕得罪人的時候?”胤禛似笑非笑地看著胤祥。
胤祥把琉璃鎮紙往桌上一扔滿不在乎地道:“我怕什麽,橫豎就是一個人罷了,我隻是怕一旦四哥你接下,太子那邊不好待,不讓他還銀百不服,可讓他還,你覺得他會肯嗎?有這銀子還嗎?再者說了,憑什麽罵名全四哥你一個人背,而老八他們就得盡賢名。”
胤禛何嚐不知此理,他歎一口氣道:“若所有人都為怕得罪他人而不接,那這差事誰來辦?難道任由庫銀空虛下去?這一次黃河大水過了,那下一次呢?總是要解決的。”
“可這樣一來,背在四哥上的罵名隻怕更盛。”胤祥搖搖頭,始終不讚胤禛去接這差事。
“我不地獄誰地獄,隻要真能辦實事,縱背一世罵名又如何,相信千古之後自有公論。”
“千古之後嗎?”多年兄弟,胤祥知道胤禛心意已決,再勸亦無用,苦笑一聲拍著胤禛的肩膀道:“罷了,做兄弟的有今生無來世,若四哥當真要做這事,可千萬別把我老十三給拉下。”
“此生能得十三弟這個好兄弟,實乃我胤禛之福也!”胤禛長笑一聲,握住胤祥的手,所有言辭在這一刻皆不足以形容兩人的誼。
數日後胤禩回京,康熙為嘉獎其賑災之功,晉其為郡王,賜號廉,是為廉郡王。不知是否這兩月來過於勞累,胤禩一回京便抱病不起,雖有心追回戶部欠銀卻無能為力。
康熙當著滿朝文武的麵言稱哪個阿哥誰能追回欠銀便晉誰為親王,可依然無人敢應,最終還是胤禛接了下來,胤祥協同辦差,務求盡快追回欠銀填補國庫虧空,要知道戶部至今還欠著兵部一整年的糧餉,若真激起兵變,這個後果哪個都抗不起。
一場席卷整個京城的狂風暴雨即將來臨,文武百人人自危,擔心這場風雨何時會刮到自己頭上來。
這夜,淩若端了參湯去書房,見胤禛伏在桌案上打盹,知其必是連日辛苦,不曾好生休息,當下取過一旁的披風小心蓋在胤禛上,的作極輕但仍驚醒了胤禛,了把臉醒一醒神道:“你來了。”
淩若心疼地將參湯遞到他手裏道:“戶部沉屙已久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四爺縱急也無用,何況四爺上有傷實不宜過於勞累。”他傷一事府中眷裏唯淩若一人知曉,回京的那一夜他雖去了年氏那裏卻不曾過夜,之後亦不曾召過人侍寢。
胤禛抿了口參湯苦笑道:“國庫都快沒銀了,我如何能不急,早些將此差辦完也好早些了了這樁心事。這次我去江南,若兒你可知我看到了什麽?”
“妾不知。”淩若拔下頭上的銀簪剔亮燭芯,徐徐道:“但能看得出令四爺頗有。”
胤禛盯著沉沉點頭,“我在回京的路上經過一個名為江夏鎮的地方,那裏竟被人整個買下做了莊園,他為士紳無須納稅無須繳糧,整個江夏鎮的人都淪為那位劉老爺的家奴,我們整整走了三日才走出他的地界。這樣的豪富連我都是頭一次見。”幽幽的芒在眼底跳,“國家艱難至斯,可那些人卻依舊在那裏花天酒地,揮金如土,與之相比我掏走的那兩百萬兩於那些個人來說實在算不得。吏治已經到了不得不重整的時刻,皇阿瑪心裏也清楚,否則不會命我接手此事。”他忽地握住淩若的手,那樣用力,仿佛要將融,“若兒,這一趟也許我會遭無數人謾罵痛恨,你會一直陪在我邊嗎?”
那樣的決心令淩若深深為之容,縱被一世罵名也無怨無悔嗎?胤禛,其實你何須再問,不論你榮耀亦或者落魄,我都不會離你而去。
反握住他的手,回給他一個安寧卻堅韌的微笑,“不管前路艱難亦或者崎嶇,妾都會隨四爺一道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海枯石爛!”
星月錯的影從疏有致的雕花窗棱中,有沉靜的繾綣溫在其中,胤禛眼中有深切的,手將擁懷中,借那的軀除去最後一不安,“是,直至地老天荒,海枯石爛的那一天,我都要你在我邊。
然……在淩若不曾看到的暗,卻有憂傷劃過胤禛的眼眸,湄兒……湄兒……他一遍遍地在心底喚著,不論懷裏的子多麽溫暖,他的心都是冷的,若兒……你若是湄兒該有多好……
猜你喜歡
-
完結310 章

重生有喜:皇後孃娘撩又甜
前世,鄰居家竹馬婚前背叛,花萌看著他另娶長公主家的女兒後,選擇穿著繡了兩年的大紅嫁衣自縊結束生命。可死後靈魂漂浮在這世間二十年,她才知道,竹馬悔婚皆因他偶然聽說,聖上無子,欲過繼長公主之子為嗣子。......再次睜眼,花萌回到了被退婚的那一天。自縊?不存在的!聽聞聖上要選秀,而手握可解百毒靈泉,又有祖傳好孕體質的花萌:進宮!必須進宮!生兒子,一定要改變聖上無子命運,敲碎渣男賤女的白日夢!靖安帝:生個兒子,升次位份幾年後......已生四個兒子的花皇後:皇上,臣妾又有喜了覺得臭兒子已經夠多且無位可給皇後升的靖安帝心下一顫,語氣寵溺:朕覺得,皇後該生公主了
69.4萬字8.18 60887 -
完結436 章

秀色可餐:夫君請笑納
一窮二白冇有田,帶著空間好掙錢;膚白貌美,細腰長腿的胡蔓一朝穿越竟然變成醜陋呆傻小農女。替姐嫁給大齡獵戶,缺衣少糧吃不飽,剩下都是病弱老,還好夫君條順顏高體格好,還有空間做法寶。言而總之,這就是一個現代藥理專業大學生,穿越成醜女發家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
98.4萬字8 1680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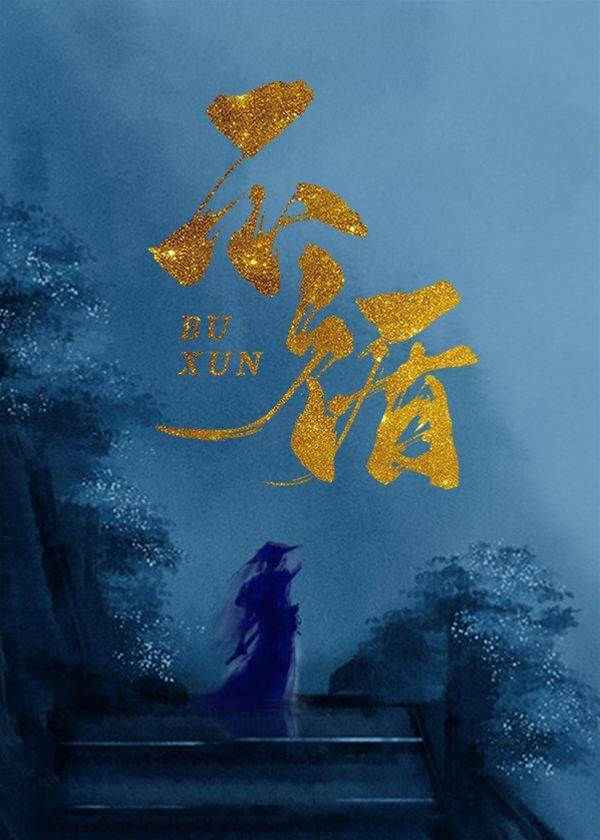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194 章

曾聽舊時雨
鎮北大將軍的幺女岑聽南,是上京城各色花枝中最明豔嬌縱那株。 以至於那位傳聞中冷情冷麪的左相大人求娶上門時,並未有人覺得不妥。 所有人都認定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 可岑聽南聽了卻笑,脆生生道:“世人都道他狠戾冷漠,不敢惹他。我卻只見得到他古板無趣,我纔不嫁。” 誰料後來父兄遭人陷害戰死沙場,她就這樣死在自己十八歲生辰前夕的流放路上。 再睜眼,岑聽南重回十六歲那年。 爲救滿門,她只能重新叩響左相高門。 去賭他真的爲她而來。 可過門後岑聽南才發現,什麼古板無趣,這人裝得這樣好! 她偏要撕下他的外殼,看看裏頭究竟什麼樣。 “我要再用一碗冰酥酪!現在就要!” “不可。”他拉長嗓,視線在戒尺與她身上逡巡,“手心癢了就直說。” “那我可以去外頭玩嗎?” “不可。”他散漫又玩味,“乖乖在府中等我下朝。” - 顧硯時從沒想過,那個嬌縱與豔絕之名同樣響徹上京的將軍幺女,會真的成爲他的妻子。 昔日求娶是爲分化兵權,如今各取所需,更是從未想過假戲真做。 迎娶她之前的顧硯時:平亂、百姓與民生。 迎娶她之後的顧硯時:教她、罰她……獎勵她。 他那明豔的小姑娘,勾着他的脖頸遞上戒尺向他討饒:“左相大人,我錯了,不如——你罰我?” 他握着戒尺嗤笑:“罰你?還是在獎勵你?” #如今父兄平安,天下安定。 她愛的人日日同她江南聽雨,再沒有比這更滿意的一生了。
29.9萬字8 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