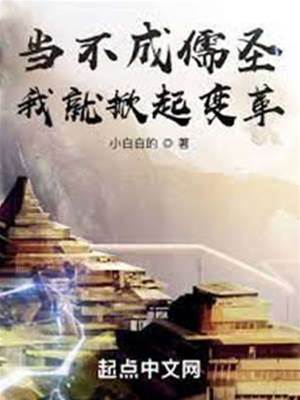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第162章 射鵰手?那是你沒遇上我
辰時三刻,天蒙蒙亮。
咚。
寂靜的院子里,突然傳來重落地的聲響。
「陳郎,你沒事吧?」
相里菱低了嗓音,語氣中著說不出的關切。
「嘶~」
「不礙事,阿菱你快回去吧。」
「我不過是虧空了力氣,腳發而已。」
陳慶咧笑著,搖搖晃晃撐起站了起來。
隔壁的相里菱鬧了個大紅臉,幽怨地想:你還好意思說。自己累得半死,把我也折騰得差點閉過氣去。
「阿菱,我明天再過去呀。」
陳慶把雙手攏在邊,小聲喊道。
「你別過來了,小心再摔著。」
相里菱嗔了一句,飛快地跑回了屋裡。
「哈哈。」
陳慶叉著腰,得意地放聲大笑。
朝思暮想那麼久,今日終於得償所願。
那滋味……可真特娘的回味無窮呀!
陳慶扶著酸痛的腰肢,腳步虛浮的往居所走去。
好馬費草,好費漢。
古人誠不欺我。
一開始相里菱還扭扭的,擔心床榻會鬧出響來,被隔壁的師兄師弟聽見。
這還能難得住穿越而來的陳老師?
直接扯了跪坐用的草席,鋪在壁爐旁。
老陳推車,走起!
熊熊的爐火燃燒,照亮了兩人疊的影。
在本能的驅下,陳慶揮汗如雨,不知疲倦。
相里菱雖然武藝不俗,力氣不弱於他,但本質上仍舊是傳統封建的子,對這等事只知逆來順,哪怕疼得咬牙關,也未做出任何抵抗。
陳慶兩頭充,顧不上憐惜對方,放開手腳大開殺戒。
火照映中,兩顆香瓜如倒吊金鐘,搖曳生姿,視覺效果極其驚人。
如果不是穿越了,陳慶高低要拍下來,留著以後時常拿出來欣賞。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陳慶打了個擺子,地癱在相里菱的背上。
Advertisement
「阿菱,緩口氣。」
「等會兒再戰一場。」
陳慶撥開側臉被汗水打的頭髮,住小巧的耳垂,意猶未盡地說道。
「先生!」
「先生?」
扶蘇走進屋裡的時候,陳慶正呈大字型躺在榻上,時不時勾起角嘿嘿傻笑。
他打了聲招呼,沒想到對方卻沒有任何回應。
於是扶蘇往前兩步,站在了榻邊了兩聲。
沒想到陳慶還是沒有應聲,只知道一個勁兒咧直笑。
「先生不知昨晚遇到了什麼事,不如說出來聽聽。」
扶蘇忍俊不地說道。
「昨晚,嘿嘿。」
「俺老陳抖擻威風,殺了個三進三出,如無人之境……」
「殿下,你怎麼來了?」
陳慶得意洋洋地念著戲詞,一回神才發覺不對勁。
待看清了扶蘇的樣貌,慌忙坐起來。
「先生想必是做了什麼夢。不知道趙雲是哪位英雄?」
扶蘇仍舊溫文爾雅,哪怕發現陳慶有些不太對勁,也沒繼續追問。
陳慶尷尬地笑了笑。
面對這位鈦合金兄弟大舅哥,虛心更虛。
「常山趙子龍,乃是後世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等有空我講給你聽。」
「不知道殿下來尋我何事?」
陳慶拖著疲憊的軀下床,趿拉起鞋子問道。
「乃是關於通往北地的直道。」
扶蘇一臉正:「三年前,父皇為了解決北軍的糧草供給,下令修建一條通往九原郡的通直大道。截彎取直,塹山堙(yin)谷,力求用最短的距離,最快的速度把糧草運輸過去,因此工程十分浩大。」
「可惜,父皇與蒙恬將軍都低估了其中的難度。」
他惋惜地說道:「直至今日,這條大道仍未完全貫通。不地方仍舊狹窄陡峭,只能容納單架馬車通行。朝廷運輸糧草,輒千萬石,被這幾險關卡住,平白增添無數損耗。」
Advertisement
「父皇雖未怪罪,但我知道蒙將軍始終掛懷於心,不得安寢。」
陳慶笑道:「殿下無須煩憂。」
「蜀的硝石已經運抵咸,等雷火司的工坊搭建好,水車運轉起來,火藥的產量起碼暴增數十倍。」
「哪怕是珠穆朗瑪峰擋在前面,我也給你炸平了。」
「一萬斤火藥不夠,就十萬斤。」
「十萬斤不夠,就一百萬斤。」
「移山填海,等閑事爾!」
扶蘇怔怔地著他,震驚地說不出話來。
移山填海,等閑事爾?
這句話說得好霸氣!
「殿下可是不信?」
「後世開山修橋,可不了炸藥。」
「就連核彈都能用來滅火、修水庫,咱們這才哪兒到哪兒。」
陳慶大喇喇地說道。
「先生所言,本宮自然不疑。」
「核彈又是何?」
扶蘇好奇地問道。
「這可就說來話長了,目前以大秦的條件,還很難造出如此厲害的武。」
陳慶為了掩飾尷尬,主往外面走去。
兩人一邊說一邊聊,索乘上馬車,沿著通往北地的直道,去最近的一險關考察。
寒風蕭瑟中。
同樣有一輛馬車沿著崎嶇的山路,朝著咸的方向進發。
頂盔摜甲的大秦士兵看押著瑟的匈奴,目兇厲,時不時對走得慢的人揮下鞭子。
伊稚斜手腳都被鎖上了沉重的鐐銬,聽到部下的慘聲后,不忍地別過頭去。
他遙著灰濛濛的天空,心無比地苦。
祭祀不是說,此次南下定然能帶回糧食和俘虜,幫助部落度過這個冬天嗎?
怎麼會敗得如此之慘!
他是草原上數得著的勇士,沒想到卻被大秦的幾個小兵使詐擒獲。
當龐國生幾人在他面前流用竹筒水壺傳著喝水的時候,伊稚斜才知道自己被耍了,頓時氣得火冒三丈。
Advertisement
可事已至此,還有什麼辦法呢?
只希家中的妻兒能夠靠著留下的資,度過這次白災。
「吁……」
「前方何人,報上名來。」
押送匈奴戰俘的隊伍拐過一轉角,卻沒想被迎面而來的一輛華貴馬車攔住了去路。
為首的屯長仔細分辨了片刻后,驚惶地跪在地上:「參見太子殿下!」
「免禮。」
「你認得本宮?」
扶蘇在北地充任監軍數年,認識他的人不在數。
「小人在將軍行營,曾見過殿下。」
屯長語氣激地說道。
「辛苦了。」
「這是……匈奴人?」
扶蘇往後打量了一眼,立刻認出了那群蠻族的份。
「正是。」
「小的奉命押送匈奴戰俘及其首領赴咸審。」
屯長沖後的人招呼道:「太子殿下親臨,快快讓開道路!」
扶蘇想阻止卻未來得及,他連忙喊道:「切勿大干戈,你們有軍務在,自然是你們先過,本宮暫且避開就是了。」
陳慶卻興地跳下馬車:「我的礦工可算來了呀!」
「讓我看看,在哪兒呢?」
「有多?」
他和扶蘇同車而坐,士兵們自然不敢阻攔。
狹窄的山道上,陳慶像是趕集一樣,東張西打量著即將屬於自己的貨。
匈奴早就沒了在草原上的兇,知道他是秦國的大人,畏懼地低下頭去。
嘩啦啦。
伊稚斜能聽得懂一些大秦話,聽到太子殿下的名號,頓時扶著牢籠的欄桿,巍巍地站了起來。
「大秦太子何在?」
「可敢與我一戰?!」
他用盡氣力,發出憤怒的吼聲。
匈奴人紛紛抬起頭,一臉悲憫地看向自己的首領,神悸。
「你這死賊酋,若是衝撞了太子殿下,了你的皮!」
旁邊看押的士兵舉起長槍,惡狠狠地呵斥道。
伊稚斜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繼續吼道:「大秦太子何在……」
「嚎喪呢!」
陳慶三兩步奔了過來:「太子殿下何等尊貴,你算個什麼東西,也配和他較量。」
伊稚斜頓時轉腦袋,怒目而視:「我是屠各部的首領,草原上萬里挑一的勇士,被尊稱為鵰手!你又是哪個?」
「我……」
陳慶瞧著對方說話的時候,腦袋不停晃,一頭髒兮兮的頭髮甩來甩去,簡直和搖頭獅子有得一拼。
他不由戲謔道:「我是太子邊一名打雜的小兵,人送外號大雕纏腰間。」
「你這鵰手,我看也是徒有虛名。」
「在草原上還能混混,遇到我這等天賦異稟之輩,怕是你不吧!」
猜你喜歡
-
完結741 章
醫品嫡妃︰攝政王寵妻日常
聲名赫赫的楚神醫穿越成了被渣男舍棄還揣著崽的絕世小可憐,她小白眼兒一翻只能認命。從此“小可憐”搖身一變,過起了帶娃虐渣、賺錢撩美人的生活,天天美滋滋,日日換新歡,豈料小崽崽的渣王爺爹竟然想吃回頭草?!楚神醫︰“崽!呸他!”小崽崽︰“我tui!!!”某王爺︰“我不是!我沒有!聽我說!”
120萬字8 44828 -
完結589 章

抄家前,王妃搬空王府庫房去逃荒
24世紀醫學天才孫明竹一朝穿越進小說,成了即將被抄家流放的戰王妃。她趕緊將王府庫房搬空,揣上所有財產,帶球流放。流放路上靠著空間內的囤貨吃飽穿暖,一路救死扶傷,還在邊寒之地生崽崽,開醫館,過上了美滋滋的小日子。終於,她那被汙蔑通敵叛國的王爺老公平反了,將皇帝的庶子身份拆穿,登上皇位,來接他們娘仨回皇宮了! 孫明竹:“大寶二寶,來跟著娘一起回皇宮去,可以見你們爹了。” 大寶:“娘,爹爹不是已經死了嗎?你是給我們找了後爹嗎?還是皇上?” 二寶:“不要不要,有了後爹就有後娘,二寶不要後爹!” 孫明竹:“不,那是親爹!” 大寶:“親爹是皇帝?那娘豈不是得去和好多壞姨姨爭寵?我聽隔壁說書先生說,皇宮裏都是惡毒的壞姨姨,娘你這麼傻這麼笨,肯定活不過三集!” 孫明竹:“……放心,你們爹不行,沒這個能耐擴充後宮,他隻能有娘這個皇後,也隻有你們兩個孩子。” 二寶:“那太好了哇!那娘我們回去叭!” 直到回到皇宮,便宜皇帝老公要在她寢宮過夜。 孫明竹:沒事沒事,他不行,也就是睡在我身邊裝裝樣子。 第二天早上的孫明竹:“什麼鬼!為什麼和書裏說的不一樣!我看的難道是盜版小說嗎?”
88.5萬字8 651436 -
完結4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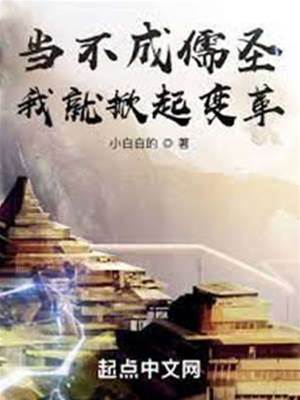
當不成儒圣我就掀起變革
作為一個演技高超的演員,林柯穿越到了大魏圣朝,成了禮部尚書之子。但他是娼籍賤庶!這個世界把人分為上三流,中流流,下九流……而娼籍屬于下九流,不能參加科舉。母親是何籍,子女就是何籍!什麼?三尊六道九流?三六九等?我等生來自由,誰敢高高在上!賤籍說書人是吧?我教你寫《贅婿兒》、《劍去》、《斗穿蒼穹》,看看那些個尊籍愛不愛看!賤籍娼是吧?我教你跳芭蕾舞、驚鴻舞、孔雀魚,看看那些個尊籍要不要買門票!賤籍行商是吧?你有沒有聽說過《論資本》、《論國富》、《管理學》、《營銷學》……還有賤籍盜,我和你說說劫富...
30.5萬字8.18 2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