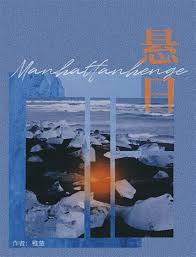《賣火箭的小女孩[星際]》 第252章 故地
原來時間已經過去這麽久了。
“還記得, 那是剛去聖羅蘭就遇上了菲勒進攻,我們不得不立刻投戰鬥。”艾略特·萊茵語氣放鬆的道,“你對我說需要幫忙找頌布的時候, 我覺得按照我的能力和報網,應該很快就可以找到這個人。”
“但是沒想到, 一直等到今天。”
楚辭訝然道:“您記得這麽清楚?”
“對。”艾略特·萊茵道, “我這個人有一個病,如果某件事一直於未完的狀態, 我就會一直回想,導致那段記憶在我的腦海中越來越深刻,以此督促我加快效率。”
“我這大半輩子, 隻有兩件事讓我這麽惦記過, 其中之一就是尋找頌布的軌跡。”
楚辭道:“我深榮幸。那另外一件呢?”
“另外一件?”艾略特·萊茵停頓了一下, 聲音平靜的道, “是慕容的父親, 我的兄弟、摯友在被謀殺之後,我用了三年的時間為他報仇。”
他微微低下頭去看楚辭, 道:“仇恨可以轉化為力, 但仇恨, 並不應該侵蝕我們的心智。”
“就這一點來說, 你做得比我要好很多。”
“因為我總能遇到讓我看見明的人。”楚辭眨了眨眼,“比如您就是其中之一,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幸運?”
萊茵笑道:“也是我的幸運。”
就在這時,西澤爾推開門,對楚辭道:“轉換好了, 頌布怎麽理?”
楚辭震驚:“還活著?”
“已經腦空白了, ”西澤爾道, “但是生理機能還未停止。”
楚辭抬手做了個開槍的作,西澤爾挑眉:“你自己手?”
Advertisement
“都行。”
“我來理吧。”艾略特·萊茵說著轉進屋。
楚辭對西澤爾道:“去看看他的記憶?”
“我來吧,你去休息一會。”
西澤爾微微往後傾,靠在了門口的欄桿上。不知道是不是在霧海奔波久了,他隨意的厲害,頭發翹著,襯衫領子斜飛,也沒有掖進子裏,短靴上沾滿幹涸的泥漿,脖子上還有一道痕,不知道什麽時候劃傷的。看上去妥妥一個星際流浪客,和軍服括、冷漠肅重的聯邦師長判若兩人。
“待會回去讓婆婆也幫你剪頭發。”楚辭看著他道。
西澤爾了自己淩的頭發:“我頭發長嗎?”
“長不長是一回事,主要是想你領略一下什麽剪頭發。”
“……”
楚辭朝他扮了個鬼臉,跳下臺階往升降梯跑去,好像生怕他會追上去打似的。
原本楚辭是想下樓去買早飯,但是在升降間鏡子般的地麵上,他看到自己的尊榮其實也沒有比西澤爾好到哪裏去,遂又悻悻然的返回了房間,洗澡洗服。
但他收拾的速度實在太快,再次出門準備去吃飯的時候,西澤爾和艾略特·萊茵依舊看記憶的看記憶,理的理,他隻好自己一個人前去吃飯。
另一邊,艾略特·萊茵問西澤爾:“此人的需要保留嗎?我聽林的意思,他似乎在聯邦也犯下了不罪案,日後如果需要呈堂證供……”
西澤爾搖了搖頭:“留著他的記憶就足夠了。”
艾略特·萊茵將拖到下水管道,慢慢傾倒了一瓶溶解劑。
Advertisement
和骨很快溶解為了一灘濃水,剩下幾段不可溶解的金屬骨骼,和一支機械手臂。
萊茵拉過水管,地上的濃水很快褪去,他將機械手臂拆除幾個零件,
撿起金屬骨骼,道:“我去趟金屬冶煉場,親自將這些東西投進熔爐。”
西澤爾走過來,從機械手臂的零件裏挑走了一節“腕骨”,應聲道:“我和林回風鈴大道等你。”
“好。”
艾略特·萊茵朝他點了點頭就離開了。
西澤爾將模擬了頌布所有記憶的芯片放進了神像儀。
因為隻是原始模擬沒有經過任何編輯,因此整個記憶片段都是混,毫無邏輯可言,而在頌布的視角裏看到的世界染上了他的個人神緒,滿目猩紅,有如濃稠的漿一般。
對待別人的記憶,尤其是原始記憶必須慎之又慎,以免被他的緒所幹擾。西澤爾調整著神像儀的旋鈕,將這段記憶不停拉近,拉近,直到出現了曈曈的人影。
不知道不是因為他臨死之前回憶了鍾樓號的場景,西澤爾看到的第一幕竟然是鍾樓號上的拉萊葉。
後的傀儡們重複著所說過的話,咧開和笑得一模一樣,令人骨悚然。
他繼續調整旋鈕,場景瞬然一變,變了錯的軌道、巨大的全息投影和眩的青藍紅紫霓虹,是自由彼岸。
眼前的場景變換的非常快,時而顛倒時而旋轉,西澤爾似乎瞥到了儀表盤,他才明白頌布應該是在駕駛飛行。
他瞬間反應過來這是頌布在製造了雪浪公寓的基因異變事故之後逃離現場,飛行如同艾略特·萊茵猜測的那樣並未沿著飛行索道行徑,而是一路直飛到了區位對接門附近的普通人區。
Advertisement
降落在一片廢棄工廠附近的空地上。
工廠外圍隻剩下一些殘破的鐵籬牆,穿過這些籬牆就是大片大片的鋼架平房,裏麵被分割無數的小格子,頌布一直在往裏走,一直往裏走——
記憶場景卻截然而止。
西澤爾按停了旋鈕。即使沒有接下來的場景他也知道頌布是去幹什麽的,他去找康維,他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康維,也就是說,他認識康維或者至也知道他的存在。
可是認識康維並不代表他知道綠通道,這是巧合還是……預謀?
他再次按旋鈕,發現場景又回到了鍾樓號。
但這次沒有了拉萊葉,而是變了重機槍掃,艦橋大廳裏的人不斷倒下,依舊滿目紅。
然後場景再次跳到自由彼岸,卻是頌布從綠通道離開,去往占星城的時候。
西澤爾繼續拉旋鈕,記憶再次跳回了拉萊葉。
接著是一聲驚痛的尖,遠方有人在奔逃,到都是嘈雜的聲音,明晃晃的日灑下,但卻似乎有什麽比日更明亮的東西一閃,一頂紅的帽子掉落在地上。
他認得那頂帽子,現在它還好好的掛在北鬥學院研究員公寓裏的架上。但它曾經落塵土,浸了地上淋漓的泊。
那是誰的。
西澤爾離開了神像儀,他看向小破旅館狹窄的窗外。旅館很偏,開在數棟建築隙裏,因此哪怕有窗戶,也隻能看到高樓大廈之間的霓虹和投影,這裏沒有天空。
他想起楚辭說過,那是他過最嚴重的一次傷,從那之後,他就很傷了。
從那之後,他就背井離鄉,在罪惡之城四漂泊。
Advertisement
西澤爾收回目,頂著的神像儀的旋鈕出了一會神,再次將下放在神像儀的像孔上。
旋鈕繼續轉,依舊是和拉萊葉有關的場景,來來回回的循環著,西澤爾從新調整了一遍,卻依舊是如此結果。
他將芯片從機裏取了出來,神逐漸不可捉。
==
“啊?”正在給老婆婆找剪刀楚辭回過頭去,“什麽意思,神手是什麽。”
“通俗來說就是他的記憶被過手腳。”西澤爾道。
“好家夥,”楚辭將找出來的剪刀放在櫃臺上,著下道,“幸虧留了一手,那還能恢複嗎?”
“能,他的大腦沒有發現電子幹擾裝置,所以應該是提前預設的某種神暗示,有些重要信息會被他的大腦自過濾,但依舊會留下一些痕跡。我模擬了他所有記憶的原始狀態,不過得找專業的神分析師來進行追溯。”
“霧海應該是沒有這種職業,”楚辭無奈道,“隻能去聯邦。”
西澤爾點了點頭。
“我剛聽見你們說什麽神分析師?”
老婆婆蒼老的聲音從樓梯口傳來,按理來說應該是聽不清楚楚辭和西澤爾的談話的,因為他們聲音很低,而樓梯距離前櫃臺還有一段距離。但是老婆婆並沒有刻意掩飾的神力等級頗高這件事,楚辭拎起剪刀在手裏靈活的一轉,刀口朝著自己,遞給老婆婆道:“是,我們找到的那段記憶被過手腳。”
“神分析可不是什麽輕鬆的活兒。”老婆婆唏噓的歎了一句,招呼西澤爾坐在窗戶口,準備給西澤爾剪頭發。
楚辭搬了個小凳子在旁邊圍觀,老婆婆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單片眼鏡進眼窩裏,然後開始作緩慢的剪頭發,一邊絮絮叨叨的道:“因為神暗示而忘的記憶很難挖掘,需要深到記憶的裏層去,太危險了,恐怕很有神分析師願意這麽做。”
楚辭問:“怎麽個危險法?”
“你用神像儀觀看過別人的記憶嗎?”老婆婆問。
楚辭點了點頭。
“覺怎麽樣?”
“很難,”楚辭回想了一下當時看劉正鋒記憶時的覺,“就就腦子裏被塞了冰塊。”
老婆推了一下眼鏡,發出一聲鼻音:“那還是因為你神力等級高。”
楚辭道:“您怎麽知道我神力等級高?”
西澤爾話道:“經驗富的縱師是能看出別人的神力等級範圍的。”
楚辭笑道:“那看來我還不是經驗富的縱師。”
“你才多大?”老婆婆也笑了起來,臉上皺出好幾道深深的褶子,“老婆子我都多歲了,多歲?哎呀忘記了……”
絮絮叨叨的道:“平時急也還算不錯,怎麽就單獨忘了這個……我剛才說到哪了?”
“說到用神像儀觀看別人的記憶。”
“哦,像儀。”老婆婆咳嗽了幾聲,聲音有些渾濁,“沒有經過理的記憶才需要神像儀;或者直接將活躍的人腦與機神通,才需要神像儀。這就好比是你在近距離的觀察別人的大腦和神。而要觀察別人的神,同時也要保持獨立思考,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很容易陷神迷宮。如果觀察者心智不夠清晰堅定,無法維持高度集中的自我神,那就很有可能會被別人的記憶和神緒所左右。”
“所以是因為高等級的神力縱師能夠穩定維持高度集中的自我神狀態,減輕了痛苦和危險?”
“可以這麽說,神像儀是有使用限製的,隻有神醫師的職業證書或者神力等級達到一定程度才可以用,”老婆婆籲了一聲,“哪像現在,隨便一個規模大點的地下診所都能找到神像儀。”
楚辭看向西澤爾,西澤爾輕輕點了下頭,卻被老婆婆一把按住,厲聲道:“別,小心剪禿了!”
西澤爾立刻一不敢,腰背直,猶如軍部開會。
楚辭忽然皺起眉:“那是不是……記憶芯片存儲的記憶也有可能出問題?”
他想起了劉正鋒。
老婆婆給出肯定答案:“當然。”
“可恢複嗎?”
“要看模擬的記憶還是原始記憶。”
“原始記憶,植大腦裏的。”
老婆婆道:“在活正常躍的大腦裏植記憶芯片是很愚蠢的做法。”
所以劉正鋒的記憶很有可能也有問題。
“這種不行了,”老婆婆搖了搖頭,“記憶芯片會改變他的大腦結構,就算人還活著,要想恢複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噥,剪好了,自己看看?”說著慢吞吞挪到盥洗室洗剪刀。
楚辭立刻非常自覺的搬來了鏡子懟到西澤爾麵前,一邊思考道:“但我不能理解,為什麽已經都對他們的記憶過手腳了,基本沒有了泄的可能,為什麽還要追殺?”
西澤爾低聲道:“你忘了頌布說過他被追殺的理由?”
“因為拉萊葉逃走,而在限定時間之沒有找回。”
楚辭重複著這句話,回想起劉正鋒、麥布納等,對那位神的、隻聞其名未見其麵的西赫士有了更深一步的認知:恐怕冷酷、狠戾,將生命在看不值一提的遊戲,而這些曾為賣命的人,也不過都是螻蟻。
他將原本舉在手中的鏡子往旁邊櫃臺上一磕,手肘撐在上麵,神微哂。
“誒,”西澤爾他,“你怎麽把鏡子拿走了,我還沒照呢。”
楚辭不耐煩的道:“別照了,非常好看。”
“是嗎?”西澤爾故意道,“難得聽見你誇我。”
“誇你的人能從一百三十六層排到無人區,不差我一個。”
後廚傳來老婆婆撒普斯的聲音,撒普斯“噔噔噔”的從樓上衝下來:“幹嘛幹嘛,他們倆不是在這嗎?為什麽又要我。”
“他們倆有別的事要忙,你去街上給我買瓶清洗劑回來。”
撒普斯抱怨著走了。
楚辭將鏡子放回盥洗室,在門口問老婆婆:“我們倆有什麽事要忙呢?”
老婆婆提出來一桶油漆,對西澤爾道:“反正你待會要換服,去把臺的欄桿刷一遍。”
楚辭將油漆接過去,道:“我哥手能力很差勁的,還是我來吧。”
西澤爾:“……”
他提著油漆桶去了臺,西澤爾跟了上來,道:“你會刷漆?”
“我不僅會刷漆,”楚辭掰著指頭給他算,“我還會修剪花木、采買、修家政機人、裝洗機和冷藏櫃等等。”
“真巧,”西澤爾懶洋洋的道,“我都不會。”
楚辭本來想損他兩句,但是一回頭,看到午後金影餘韻裏,西澤爾的發梢仿佛燃燒的碎金,英俊的側臉神安靜,微微低著頭,脖頸那條幹涸的痕還在。西澤爾的皮和他差不多,都是冷質的白,因此那道傷痕格外鮮明,像某種紅的圖騰,爬進了他的領口裏,總讓人想扯開他的領子看看。
猜你喜歡
-
完結109 章
情予溫寒
一個(偽)性冷淡在撞破受的身體秘密後產生強烈反應然後啪啪打臉的集禽獸與憨憨於一身,只有名字高冷的攻。 一個軟糯磨人卻不自知的受。 一個偽性冷、偽強制,偶爾有點憨有點滑稽的故事。 為何每個看文的人都想踹一jio攻的屁股蛋子? 面對“刁蠻任性”又“冷漠無情”舍友,他該何去何從?
25.9萬字8 38664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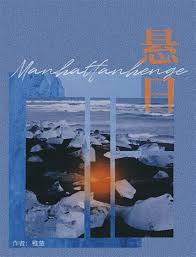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