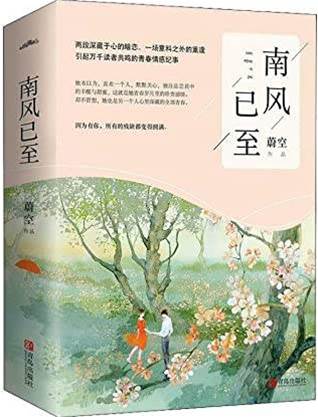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暖君》 第92章 領訓
周娥直到臨近申末才回來,從后院直接進了正院上房,和李苒拱了拱手,先自己給自己倒了杯茶。
“壞了。”
周娥待了句,連喝了兩三杯茶,痛快的呼了口氣,這才坐到榻前扶手椅上,沒開口先嘖嘖有聲。
“真是開了眼了,桃濃那句說得對,一窩子畜生。”
“嗯?”
李苒坐直了上,吳嫂子沒能出來嗎?
“吳嫂子沒事。唉,也不能說沒事,那件事應該沒事了,可后頭……唉,真是畜生啊!”
周娥一下接一下拍著大。
“我從頭說,今天看了一天熱鬧。”
周娥欠起來,頭湊到李苒面前,低聲音道:“一天都沒看到那個老頭,還有那倆漢子,咳,說正事兒。”
周娥坐回去。
“是里正報的,我不是回來了一趟麼,再到府衙,說是已經查明了。
是這麼說的:白老頭喝多了酒,從樓梯上摔下來,好巧不巧,一頭撞在旁邊放著的大木砧板上,那砧板多呢,這頭就崩了。
吳嫂子呢,膽子小,就嚇暈過去了,說是里正一碗涼水把潑醒的,醒了之后,嚇的只會哭。
白家那倆小畜生,聽說他們爹死了,頭一件事,先往他們爹屋里沖進去找銀子,說他爹藏了好幾大箱銀子,還真有不。
說是,把腳店和后面那個小院,各個門都鎖了,都是兩把鎖,白老大一把,白老二一把,嘖!呸!”
周娥又長嘆了口氣,接著道:
“白老頭這死,自己把自己摔死了,當時就定了案,買了口薄皮棺材,那兄弟倆說,人死如燈滅,他們爹是個豁達的,早就說過,等以后一蹬死了,一把火燒了最好,就是要用棺材,也一定要用個最便宜的。
Advertisement
白老頭死這事兒,就是幾句話,就料理了結了,快得很,后頭吵吵,都是因為那間腳店,還有吳嫂子。
白老大和白老二,異口同聲,說吳嫂子是他們白家的奴兒,買來就是放在腳店做廚娘,順便侍候他們老子爹的。
這麼不要臉的,就是這京城,也不多見。
里正說吳嫂子不是奴兒,是白老頭的繼妻,又找了當年的人。
這兄弟倆就改了口,說他們爹的死,是因為吳嫂子侍候不周,嚎著要府治吳嫂子一個侍候不周致死的罪,最好發賣掉。
唉,真是一對兒畜生。”
“后來呢?”
李苒蹙眉問道。
“后來,該吃飯了,就先散了。”
周娥看著李苒,片刻,頭又往前湊,“那個,桃濃說晚上請你吃飯,把晚上那一場推了。”
“是有事吧?”李苒瞄著周娥。
“桃濃那意思,這事最好跟你商量商量,我覺得也是,多一個人,總歸能想的周到些。”周娥一臉笑。
“嗯,走吧。”李苒站起來。
周娥也站起來,兩人一起出了翠微居,直奔清風樓。
桃濃正在清風樓雅間里轉圈,見周娥先進來,掀簾子讓進李苒,長長吐了口氣。
“坐坐坐,咱們先吃飯。”桃濃陪著一臉笑,客氣極了。
李苒坐下,看著桃濃招呼一聲,幾個焌糟很快擺了滿桌子的菜,從桃濃看到周娥,沒說話,給自己盛了半碗湯,抿了口。
“我沒有食不語的規矩,瞧著,這是沖我來的,說吧。”李苒說了句,接著抿湯。
“我就說聰明得很,你說吧。”周娥示意桃濃。
“哪敢沖姑娘,實在是沒辦法,唉。”
桃濃連嘆了幾口氣,是真愁。
Advertisement
“今天不是鬧了一天麼,后來黃推說,晚了,明天接著審,旁邊那個書辦,說讓吳嫂子留一留,要畫個押什麼的。
等白家那倆畜生出去,那書辦就問吳嫂子,有什麼打算,說一個婦道人家,又帶著個小閨,不容易,他們推是個心善的,說是讓吳嫂子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明天趕早過去,給他個回話。
吳嫂子就找了我,問我該怎麼辦,我跟周將軍商量了半天,想來想去,還是得請姑娘拿個主意。”
李苒凝神聽著,嗯了一聲。
這會兒出來,只能是商量吳嫂子的事兒,這想到了。
“我先說說這事兒的難。就一條,一個人立不起來。
白家是個虎狼窩,肯定沒法再呆下去了。得從白家出來。
白老頭已經死了,要,讓白家那倆畜生以后沒法再找麻煩,要麼改嫁,要麼,我覺得白家倆畜生那話倒不錯,干脆讓他們把吳嫂子賣了,我說讓周將軍買下……”
“我買不了,沒地方放。”周娥立刻接了句。
“你買下好了,讓周將軍出錢。”李苒看著桃濃道。
“我倒是想,可我一個下九流,賤籍,我買下們娘倆,吳嫂子倒無所謂,那小閨怎麼辦?
良賤不通婚,那小閨就別想嫁人了,能找個良家做妾,都是大福氣了,這哪能行。”
李苒聽的連連眨眼,這個,真沒想到,真不知道!
“我沒法買,我也沒地方放。”李苒迎著桃濃殷切無比的目,趕擺手,“要不,改嫁?”
“到哪兒找合適的人家?都多大年紀了?又不能再生孩子了,又連死了兩個丈夫,還帶著個拖油瓶,再找,最多就是白老頭這樣的,有兒有一大家子,嫁過去做牛做馬,唉,那還不如死了呢。”
Advertisement
周娥一邊說一邊搖頭。
“也不想再嫁了。”桃濃接過話兒,
“這個人,逃到京城之前,一直是做奴兒的。從小兒,就是為了當奴兒養大的,是個好奴兒,上好!你看看這樣子,就是個得有個主子的。”
桃濃看著李苒,象推銷件兒一般。
“不能立戶麼?你和周將軍,還有我,平時多照看些,真要淪落為奴,那小閨不是更慘?”
李苒不是很能理解桃濃這個思路。
“姑娘這話可真是……”桃濃一臉干笑。“您府上,別說象您三哥邊小廝那樣的,就是一個使的奴兒,走在街上,都是昂首闊步,一般人可不敢惹。
有一個兩個,求了主子放出來自行嫁娶的,一般兩般的人家,都不敢上門去求,求也求不到。
姑娘可真是。”
“說的沒錯,什麼都不懂。”周娥一邊聽一邊點頭,先點著桃濃和李苒說話,再點向李苒和桃濃說。
“還是你買下吧,再出點錢,讓開家小飯鋪,都放在你名下。你能做生意吧?”
李苒看著周娥道。
“這辦法好!”
桃濃拍手贊。
“我就說,姑娘不合適,姑娘這份地步兒,靜太大,再說,吳嫂子又……可不能算是吉利人兒,姑娘買下,說起來都不好聽。
再說,姑娘是長安侯府姑娘,再怎麼,也算是有一堆長輩的。
咱們不能給姑娘添。
還有,你煞氣重,滿京城,誰不怕你?投到你門下,白家那倆畜生指定不敢再打主意擾。
這樣最好!”
周娥牙痛般咧著,好一會兒,勉強點了點頭,“我自己都……行吧,唉。”
Advertisement
“吳嫂子多能賺錢呢,你這是撿到大便宜了。”
桃濃眉梢飛揚,聲調也上揚愉快起來。
; “那就讓他們把吳嫂子賣了,得去找找做這一行的人伢子,還有,這價錢不能由著那一對兒畜生要,這事我去就行,現在就去,得趕。”
桃濃說著話,已經站起來了。
“你坐下,用得著你?”周娥一把揪回桃濃。
“喲,你瞧我,糊涂了,這事兒,咱們周將軍把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當當,等這事兒都安排好,我請你喝酒,得好好敬敬你!”
桃濃唉喲一聲,重又坐下,看著周娥,一臉討好。
周娥繃著臉抬著頭,似是而非的嗯了一聲。
三個人商量好,也就吃完了飯。
桃濃急匆匆回去給吳嫂子回話,周娥看著李苒,努了努,“從萬壽觀回去?”
“不用,回去吧。先等事了了。”李苒搖頭,示意徑直回去長安侯府。
吳嫂子這案子沒清結之前,大家都回避些最好。
第二天,離正午還有半個多時辰,周娥探頭進屋,和李苒笑道:“都好了,吳嫂子連閨,一共花了二兩銀子,我讓找開飯鋪的地方去了。”
“們娘兒倆現在住哪兒了?”李苒關切道。
“先跟桃濃一,我跟說了,找個前店后院的,最好找個能買下來的,已經沒事兒了,你放心。剛才侯爺傳了話,讓我趕去一趟兵部,我現在就過去瞧瞧。”
周娥回來的很快。
愉快而去,垂頭而回。
周娥靠著門框,頭從簾子外進來,有幾分有氣無力的和李苒待道:“我得出趟遠門,半個月吧。你去一趟清風樓,那個,萬壽觀那邊兒。”
萬壽觀三個字都沒說完,周娥已經放下了簾子,李苒急忙追出去問道:“什麼時候?”
“就現在。”周娥頭也不回的揮了下手,垂頭耷肩往后院去了。
李苒看著周娥進去了后院,低頭看了看服,抬腳往外走了兩步,又站住,提高聲音了聲小云。
小云應了一聲,從茶水房出來。
“周將軍要出遠門,我現在要出去一趟,車……”
李苒看著小云,小云忙曲膝笑道:“姑娘是要讓人備車是吧?我這就打發人去說一聲。”
“嗯。”李苒微笑應了,放慢腳步,往二門過去。
二門外,車夫已經等著了,李苒上了車,吩咐去清風樓。
長安侯府離清風樓極近,李苒在清風樓前下了車,石南那個小廝站在清風樓門口,看到李苒,并未迎上去,欠了欠,轉往后。
李苒跟著小廝,進了后面湖邊一座雅間。
謝澤站在正屋門口,讓進李苒,示意坐。
“周娥走了?”謝澤倒了杯茶推給李苒。
“正收拾東西呢,說要出去半個月?”李苒端起茶,抿了一口。
“一個月。”謝澤再給自己倒了杯茶,“去軍馬場喂一個月馬。”
李苒差點呃出聲來,“是你?因為……那家腳店?”
“因為不知輕重,竟敢把你拎了出來。”謝澤語調中著明顯的惱怒。
李苒沒敢接話。
周娥拎出來,心甘愿的被周娥拎出來,論起來,這個錯,一點兒也不比周娥小。
“還沒吃飯?”謝澤看著明顯心虛的李苒,見點了下頭,蹙眉道:“先吃飯。”
“嗯。”李苒垂頭應了,拿起碗,先盛了半碗湯喝了,又吃了半碗飯,放下了碗。
西青和槐枝上前收了飯菜,重新沏了茶端上來。
“周娥十五歲從軍,到現在,三十多年,是個老**子。
當了十幾年的將軍,到現在,刑統背不全,軍法也背不全,有了事兒,不管什麼事兒,都是照**子那一套,先出一堆歪主意。”
謝澤看著李苒喝了半杯茶,哼了一聲,接著剛才的話,聲音冷厲。
李苒后背靠在椅背上,大氣不敢出。
他生氣了。
“這事不怪你。”
謝澤看著坐的筆直,一幅驚訓模樣的李苒,語調緩和下來。
“長安侯必定沒待過你這些,我該早跟你說,是我疏忽了。”
李苒暗暗舒出口氣,稍稍放松了些。
“周娥這個人,極講義氣,就是太講義氣了,不分輕重,也從不衡量得失。
你說戰功卓著,卻沒能象其它人那樣,開府建衙,那是因為,拿的軍功,換了痛快兩個字。”
“嗯?”李苒眉挑了起來。
“周娥七八歲的時候,被人伢子賣進了甜水巷,十五歲那年,逃出京城,投了軍。
先皇稱帝的時候,論功行賞,只要報仇,皇上就允了,按功勞折算人頭,立下的功勞不夠,還倒欠了十幾顆人頭。
砍頭的地方也是挑的,就在龍津橋上,一口氣砍掉了二十九顆人頭。”
李苒聽的再次直了后背,輕輕了口氣,怪不得甜水巷和各個瓦子里的那些人,那麼怕。
“是個天生的戰士,若論攻防對陣,領兵沖殺,臨陣應變,軍中沒幾個人能比得過,在軍中極有威。
可自始至終,都是為副,從來沒獨領一軍獨擋一方過,不是因為是人,是因為從來不知道什麼謀定而后,什麼思慮周祥。”
李苒這一次呃出了聲。
周娥看起來,一直都是有竹,穩如泰山,極有大將風范。
謝澤看著李苒滿臉的怎麼會這樣,哼了一聲。
“剛領千人隊時,連沉住氣、不聲都做不到,練兵的時候,皇上盯著,耳提面命,想了無數方法,后來,總算教會了用扎馬步來穩心神。
你以后要多留心,要是看到岔開雙,像是在蹲馬步,那不是穩如泰山,那是慌極了,快撐不住了。”
李苒一下子想起來昨天早上在腳店里,周娥岔開的雙,那一幅穩如泰山的模樣。唉了一聲,不知道說什麼,以及該有什麼樣的表。
“昨天扎馬步了?”謝澤明了的問道。
李苒連連點頭。
謝澤嘆了口氣。
“皇上沒讓單獨開府,就是不放心。也不愿意單獨開府。
年后長安侯要領兵南下,皇上的意思,周娥舊傷太多,也有了些年紀,又是戰將,和長安侯不同,不宜再隨長安侯出戰。”
謝澤的話頓住,片刻,嘆了口氣,接著道:“得有個人看著,本來……唉,我已經把調到我這里了,等從馬場回來后,還是跟在你邊,你要看著些。”
“……”
李苒呆了片刻,一個好字卡在嚨里,卻沒能吐出來。
一直視為穩妥依靠的周將軍啊……
“這一陣子,周娥不在,大慶殿那一帶,晚上別過去了。”
謝澤看著瞪著眼睛張口結舌的李苒,想笑又想嘆氣。
“那……”
李苒一個那字之后,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那想見他怎麼辦?周將軍要一個月才能回來。
謝澤看著李苒,一幅等往下說的樣子。
“我要是有什麼事兒,怎麼找你?”
李苒抬頭看著謝澤問道。
“你能有什麼事兒?”謝澤反問了句,沒等李苒答話,嘆了口氣,“真要有什麼事兒。”謝澤的話頓住,微微蹙著眉,片刻,接著道:“我會知道的。”
李苒呆了一瞬,眼淚差點下來,“我要是,就是想看看你……”
“我最近很忙……明天我不在京城,后天吧,我讓人遞話給你。”
謝澤話說到一半,見李苒眼淚下來了,立刻改了口。
“唉,回去吧,我晚上有事兒,不能多耽擱。”
謝澤說著,出帕子遞給李苒,看著李苒了眼淚,站起來,將李苒送出雅間,看著走遠了,再次嘆了口氣。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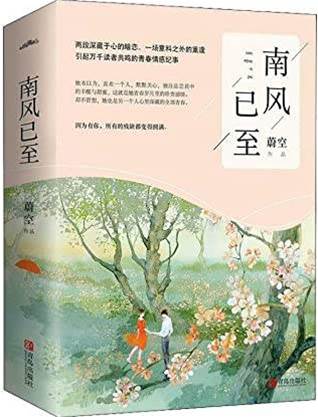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