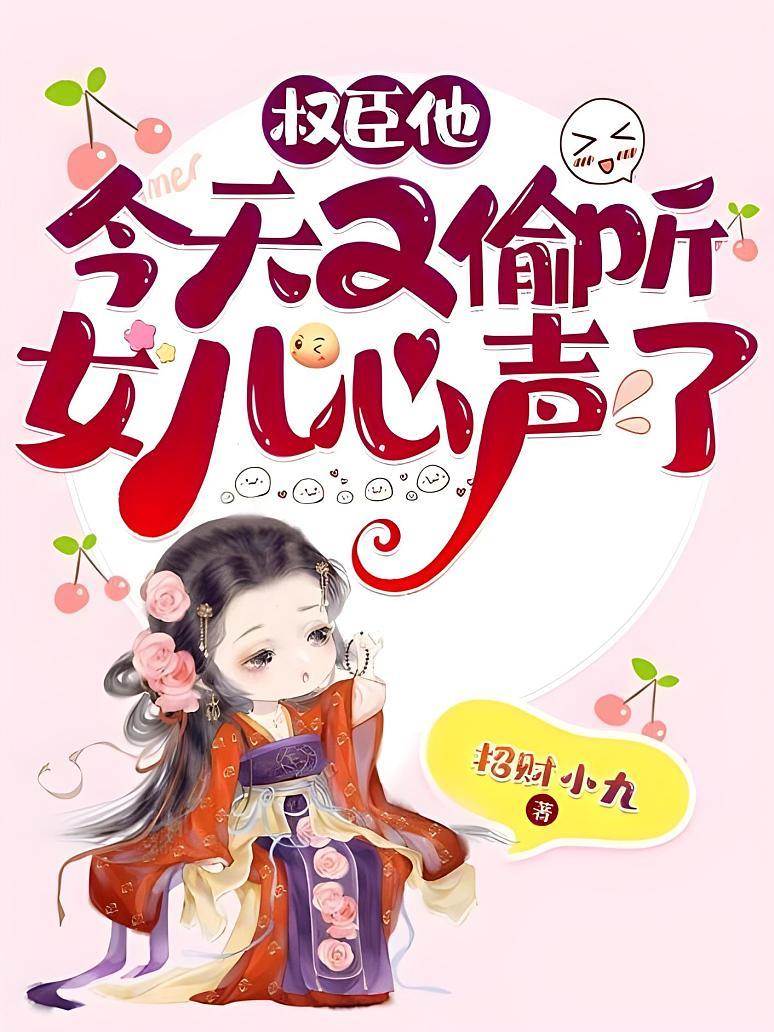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黜龍》 第六十四章 擐甲行 (17)
唯獨白有思,也是微微一愣,但明顯想到了什麼,眼神有些忍不住在張行上打轉。
“死的病的,加上逃的……算了,你只說大概還剩多可戰之力?”張行迅速回過神來,正來問。
“小兩萬人……大概。”雄伯南趕應聲。
“我知道了。”張行忽然起,上甲胄也明顯帶起了一陣金屬的聲。
而這個作也引得在座的大多數人一起起,卻不是甲胄聲了……畢竟,雖然每晚能統一下令卸甲,但四五日不洗澡,還淋著雨,酸味也是不了的。
;大家都很辛苦。
“此間人,除魏公與柴舵主所領后勤人員外,所有人,立即上馬,現在隨我去北面,攔住東線的諸位兄弟。”張行環顧四面,下了命令,他已經意識到,關鍵的時刻到了。“現在就走,雄天王帶路,徐大頭領和牛頭領速速安排好部隊,也一起過來……三娘也來。”
“這是自然。”最后被點到姓名的白有思抱著長劍搶先做答。
而眾人剛去牽馬,原本就沉的天氣,卻是忽然間又開始滴雨了。
這一次,早就習慣的眾人連罵娘都懶得罵了。
這支約百余人的銳騎士部隊行非常迅速,本不是之前大隊輜重行軍能比的,只是下午時分,便抵達了濮和甄城之間的道上,卻沒有見到人。
一開始,大家以為這些東線部隊人心惶惶,怕是迫不及待往濮去。
不過,隨著雄伯南騰躍而起,指引了方向,眾人方才醒悟——士卒疲敝,怕是遇到雨后,心生畏懼,直接停在了某些村寨、市鎮中避雨去了。
所以,部隊還在東面。
于是,眾人復又向東而去,果然,很快就在雄伯南的指引下撞上了這支龐大而混的軍隊。
Advertisement
因為雄天王提前告知,李樞先行帶著祖臣彥、房彥朗、杜才干、楊得方等文首領趕來,速度之快,倒是驗證了他早已經放棄對軍隊管束的事實。
雙方見面,張行翻下馬,不顧兩人上全都酸味明顯,直接握手來言,開門見山:
“李公,西線與東線不同,東線部隊已經狼狽不堪,在敗局中,自然對一哄而散暫時沒有什麼,可西線這里卻從頭到尾沒有遭遇敗績,而且資齊備,卻不愿意輕易言棄;更重要的一點是,東郡與濟郡乃是諸位頭領、執事、護法的家鄉,之前一直維系妥當,而若是咱們不戰而走,將兩郡士民扔到韓引弓那種軍頭腳下,他們醒悟過來,必然會生出怨氣的,這一年辛苦反而白費……所以,何妨努力一戰,勝了萬事迎刃而解,敗了也算是為諸位兄弟盡心盡力而為了一場,然后再行撤離?”
李樞微微一愣,又看了一眼張行后的白有思,再去看了眼若有所思的徐世英以下滿滿當當的西線骨干,沉默片刻,方才來問:“這是你的主意,還是思思的主意?”
張行立即會意,這是李樞又把事想復雜了。
而白有思也聽得明白,當即抱長劍含笑來言:“世叔想多了,黜龍幫的事本該是三郎與諸位自專,我今日但為一劍而已,其余種種,便是有些想法,也該這一仗之后再說。”
李樞點點頭:“若是拼一把,為黜龍幫兄弟盡心盡力,自然無妨。只是人家三路來圍,局面這麼難,你便是想打,又準備怎麼打?”
“此事簡單,且待東線幾位大頭領、頭領們一起過來。”雨水依舊淅瀝,張行卻緩了一緩。“省得要說許多遍。”
李樞再度頷首,只是讓人去喊注定早已經知道靜的那些東線頭領們。
Advertisement
這種態度,與其說是配合和贊同,倒不如說是順水推舟,他本對再打一仗并沒有絕對的認可,只是不想落到張行所言“招人怨”的地步罷了。
當然,反過來說,也的確說明了張行認準了對方的真實心態,勸說效果非常之好。
須臾片刻,王叔勇、單通海、程知理、夏侯寧遠、梁嘉定、張善相、丁盛映、翟謙、尚懷志、翟寬、黃俊漢、柳周臣,包括跟著程知理過來的賈閏甫,紛至沓來。
再加上隨張行過來的雄伯南、徐世英、牛達、郭敬恪、魯明月、魯紅月、李文柏、張金樹、賈越、閻慶……最起碼軍中首領已經來了個七七八八。
張行掃視一眼,知道這些人有優有劣,也知道這些人各自有許多故事,有許多言語和說法,但此時,本沒時間多說什麼,乃是一手拽著李樞,一手指向了東面,直接分析起了軍事:
“諸位,我的意思很簡單,首先,任他幾路來,我只一路去……三路大軍,屈突達部是東都的命子,絕不會輕拋;韓引弓心懷鬼胎,必然遲疑不定;唯獨齊郡老革張須果做事最主,最舍報效他的朝廷……所以,只要咱們打敗張須果,其余兩家必然喪膽,不再多事,此局非但能解,而且豁然開朗。”
已經淋了五六日雨水,眼睜睜看著手中部隊從簡單撤退演變不控崩潰的東線頭領們紛紛愕然,半信半疑,而西線首領們則明顯為之一振。
“其次。”張行復又以手指向南邊。“我們只要合兵一,是有足夠兵力和實力打敗張須果的……西線這里的兩萬余生力軍就在離狐,而且還有充足的軍械、軍糧補給,碭山的部隊也能趕來,只要大軍向南匯合,就會立即有四五萬大軍,我們就在那里整備妥當,布置陣地,然后把追擊的敵軍吸引過去,以逸待勞,一定能勝。”
Advertisement
聽到這里,周圍氣氛更加振作一些,但也有人似乎是想說什麼。
而張行本不作理會,只是回頭來看徐世英:“徐大頭領,你是離狐人,你心里有沒有作戰的想法?戰場和戰,隨便說一個。”
徐世英在雨中抿了下,只是沉片刻,便坦然來言:“歷山西面有片地方,一到這季節就容易泥沼,我們可以把他們引到歷山和那片泥沼中間,在那里構筑陣地,攔住他們,然后再派遣兵從泥沼中的小路穿過去堵住他們來路,接著只要堅持住,他們肯定會控制不住往泥沼中走,然后自行潰散……大勝就是我們的了。”
張行立即點頭,然后環顧左右:“你們聽到了沒有?”
周圍頗多人意,但還是有人麻木不。
而張行也繼續來講:“我知道,即便如此,你們還是擔心我所言虛妄,擔心會敗,但你們想過沒有,若不打這一仗,坐視部隊崩潰,坐等軍來圍剿,我們難道會有好果子吃?我們這些有修為的人,還能逃散,可是諸位大頭領、頭領,頗有些人是本地出,難道要坐視軍過來,家鄉?你們知不知道韓引弓的部隊城必做劫掠,殺良冒功、強暴婦?何況咱們本就是正經的反賊呢?”
“那便打嘛!”出乎意料,片刻的沉默過后,居然是單通海第一個呼應。“只是張大龍頭,現在不是我們不想聽你調遣,而是軍隊已經不控制了,家鄉子弟兵都不聽我們言語了,就是借著一勁順著道往西走,拉都拉不住……要不咱們一起去濮?”
“去濮不是不行,但能去離狐還是要盡量去離狐。”張行有一說一。“因為我們是傾巢而出打這一仗,一旦被韓引弓發現濟空虛,或者吸引到屈突達的注意力,很可能會一敗涂地……而且便是打贏了,也要迅速折回南線去防守韓引弓,所以,戰場選擇還是離狐更好。”
Advertisement
“總得試一試。”徐世英也趁勢開口。“我們本為此事而來,看看咱們能不能一起努力,把人拽到離狐去,只要拽到離狐,就地休整,得到補充,然后再就地作戰,便順理章了。”
“那就要看張大龍頭你這張到底有多厲害了。”單通海瞥了眼徐世英,一聲嘆氣。“士卒可不像我們這些頭領懂的那麼多厲害,你一說,我們雖然心中畏怯,但還是曉得應該搏一搏的……”
“其實未必是底層士卒的事,他們只是太累。”李樞忽然。“張龍頭,據我看來,反而是那些伍長、什長、伙長,乃至于隊將,他們不是累,更是沒了心氣,不想再作戰……這才全軍失序的,若是能把他們拉起來,整個軍隊說不定也能拉起來,轉向離狐。”
你不是很懂嗎?為什麼一開始不管?
張行心中無語,面上卻只是點點頭。
話說,張行心知肚明,便是眼下李樞和這些頭領們答應的很利索,可實際上,從上到下,也都還是有些沮喪和無力。
而張行的真正倚仗和法寶,從來都是他在這留守大半年里對這兩個郡的保護,以及在本地的組織建設,還有一些正確策略與出擊帶來的資積存……那些被從魏玄定從濟城運來的糧食、軍械、燃料,以及輕易員起來的兩萬多部隊,還有那些兩郡部暢通無阻突破了雨水天氣的后勤輸送通道,才是真正決定這一戰勝負的東西,也是真正能讓東線敗軍迅速恢復信心的東西。
但是問題在于,現在的局面已經糟糕到你不來把人拉走,他們的高層就會直接散伙,部隊就會失控的地步了。這個時候,你說我有那些東西,徐世英他們也能作證說有,不親眼見到,誰會信呢?
誰都知道熱粥和勝利的希更有效,但時間過于倉促,局勢過于急迫,只能先耍皮子,讓這些人看看他的“有多厲害”了。
一念至此,張行繼續拉著李樞的手向周邊人認真來問:“眼下哪里的部隊最多?”
“三里外的那個村子里。”王叔勇終于得到機會,不等李樞開口便手一指。
張行放眼去,只見下午的細雨中,遠的村莊頭頂云霧繚繞,但卻沒有過多嘈雜聲,考慮到東線部隊的數量,幾乎可以想見彼人員堆積卻又死氣沉沉之態。
“走。”
張行終于松手,然后翻上了黃驃馬。“咱們一起過去,把沿途所見的尸首和病員給聚集起來,病員先放在村子里好生照顧,然后送往離狐,尸首就在村子邊上妥善放置好,準備挖坑下葬,再盡力把那些基層軍來……能做到吧?”
這當然能做到,但是確定有用嗎?
東線的首領們,包括王叔勇在,明顯有些遲疑,而西線的首領們,包括徐世英在,卻都毫無表,只是應聲而已。
李樞看著這一幕,眼皮忽的一跳。
但還沒完。
且說,對于修行者和生力軍來說,單純運送傷病員、搬運尸首和挖坑這種純粹的力活不要太簡單,只是尋找尸首有些麻煩,因為你很難區分在雨中睡著的人、昏迷的人和死的人。
故此,一行人很快就將幾十個傷病員匯集了起來,然后又將一個大坑給挖好,反而是尸首匯集比較緩慢。
至于這個喚作黃莊的小村落,早已經布軍士,卻在之前挖坑時只在細雨中冷眼看著這一幕不說話。不過,當尸首漸漸增多,他們也漸漸意識到是要干什麼的時候,卻還是忍不住緩緩爬起來,往這個村莊的邊緣匯集——生老病死,即便是再累再麻木,面對著最終歸宿的土,也終究不能做到無于衷。
最起碼,總該想知道,死的人里面有沒有自己的鄉鄰故舊吧?
與此同時,如徐世英、王叔勇、翟謙、尚懷志之類的人,雖然態度各自不同,可是在挖完坑后,都還是盡量給了張行面子,努力去將村莊里的基層軍們紛紛喊來。
便是單通海,干站了一會后,也終于去幫忙了。
故此,放尸首的大坑旁,很快就聚集起了麻麻的人,這些人,因為雨水沖刷,似乎稱不上臟污,但普遍丟盔棄甲,跟全副甲胄外面還套了一件綢披風的西線骨干相比,明顯了一點生氣和鮮活。
不過,這兩撥人外加那些頭領們聚在一起,在細雨中看著這些尸首,卻又不分彼此,一時有些傷其類,心生哀慟起來,繼而甚至有些哭泣聲若若現。
而就在氣氛似乎要導向哀兵之態的時候,張行和賈越抬著另一尸抵達了。
他將尸首小心運到坑中,認真擺好,然后聽著哭聲,面不變,心中卻知不能再等,而出了尸坑以后,更是稍微環顧四面,便忽然越眾往一個方向走去。
周圍人無論如何都曉得這是張大龍頭,也都紛紛避開,只用或麻木或期待或審視的目看著這位穿著甲胄、披著綢披風的人穿過細細的雨線,走到盡頭,然后踩著一個早已經的柴火垛,輕易跳到了村莊邊緣一家農戶低矮的側屋屋頂上。
來到這里,張行居高臨下看了一圈,下方漸漸安靜,而只是稍微沉默了一會,他便扶著驚龍劍嚴肅開口,乃是用了真氣加持,聲音宏亮一時,震于村野:
“諸位,人總要死的,但死的意義不同,我看一本小說里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紅山,或輕于鴻。’為大義而死,為鄉里百姓抵抗暴魏府而死,不管是怎麼死的,都比真龍所化的紅山還重;替軍賣力,替欺百姓的大魏府去死,就比大雁的一還輕。今天我們要安葬的這些袍澤,就是為東境百姓抵抗暴魏府而死的,他們的死,是比紅山還要重的!”
細雨中,有人打了個激靈,有人依舊麻木,還有人覺得,跳到屋頂上的這個人說話有些啰嗦。甚至,有些人心中冷笑了一下,完全不以為然。
但依然有一部分人稍微咽了下口水,然后嚴肅了許多,而嚴肅是會傳染的。
到整個雨幕下的場景,就是整上忽然了一下,接著忽然又安靜了許多。
“我知道,一定有人想說,你滿口大義,只是想哄我們去死,是不是大義,難道是你空口白牙說了算嗎?你是至尊下凡嗎?”張行環顧下方,聲音依舊宏亮清晰。“我當然不是至尊下凡……但是大義在我們,這難道不是天下人公知的事嗎?難道不是至尊也該承認的事嗎?
“大魏朝廷一畝地征兩畝的稅,老百姓窮的吃土,這不是苛政?徭役不斷,三征東夷,死傷無數,每家每戶都有認識的人一去不回,這不是暴無度?而我們黜龍幫起兵抗擊暴魏,救民于水火!難道不是大義所在?若是真有哪個至尊敢說大義不在我們,那他也不配再列位至尊了!”
這時候一道閃電劃過,張行趁機歇了一口氣,數個呼吸后,雷聲如約轟隆隆作響,很多被張行言語吸引的人也都被雷鳴驚醒,一時抬頭去看并不算烏云布的頭頂。
雷鳴之后,雨水漸漸有些發急,這位大龍頭繼續來言,卻言簡意賅:
“諸位,你們告訴我,這些為了將東面幾個州郡從暴魏手下解救出來,而披甲執銳,離家出征,最后因為跟軍作戰,死在這里的這些兄弟,是不是了不起?是不是一死重于紅山?!”
這一次,聲小了很多。
有趣的是,不是這些小首領,很多原本在路上相會,并沒有太多認可姿態的頭領,此時反而如白有思一般,看著這位西線大龍頭目灼灼起來。
有的時候,就是需要有人簡簡單單的告訴你,你做的那些看起來普普通通的事,其實都是對的,你的那些付出和犧牲,都是了不起的。
“暴魏必亡,抗魏者自生大義!”張行舉起一手指,言語如陳述著某種簡單事實一般肯定。“咱們這次東征,雖敗猶榮,軍雖勝,也遲早要遭覆滅!”
接著,他的言語復又變得誠懇起來:
“而諸位,也請務必聽我一言,我真的在南面離狐給大家準備了足夠用的糧食、木炭、帳篷、武,只是甲胄了一些,需要諸位盡量自己帶上……須知道,甲胄是很寶貴的……有人說,男子漢大丈夫生于天地間,有至尊在上,有鎧甲在,有大義在前,這時候只要邁開雙,去取功勛,便能公私兩便,得償所愿,那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
“諸位兄弟,咱們一起把這些一死重于紅山的兄弟給埋了,然后擐甲在,就隨我走吧!”
聽到這里,別人不知道,就在柴火垛旁邊的李樞莫名一個哆嗦,好像也被雨淋病了一般。
PS:說來驚悚……《黜龍》兩萬均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19 章

混沌修神訣
一個農村出來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青年,歷經千辛萬苦大學畢業,被初戀甩,同時至親奶奶離世,心灰意冷,決心投井了卻殘生,卻不經意間得到逆天傳承,別人修仙他直接修神
86.9萬字8 10162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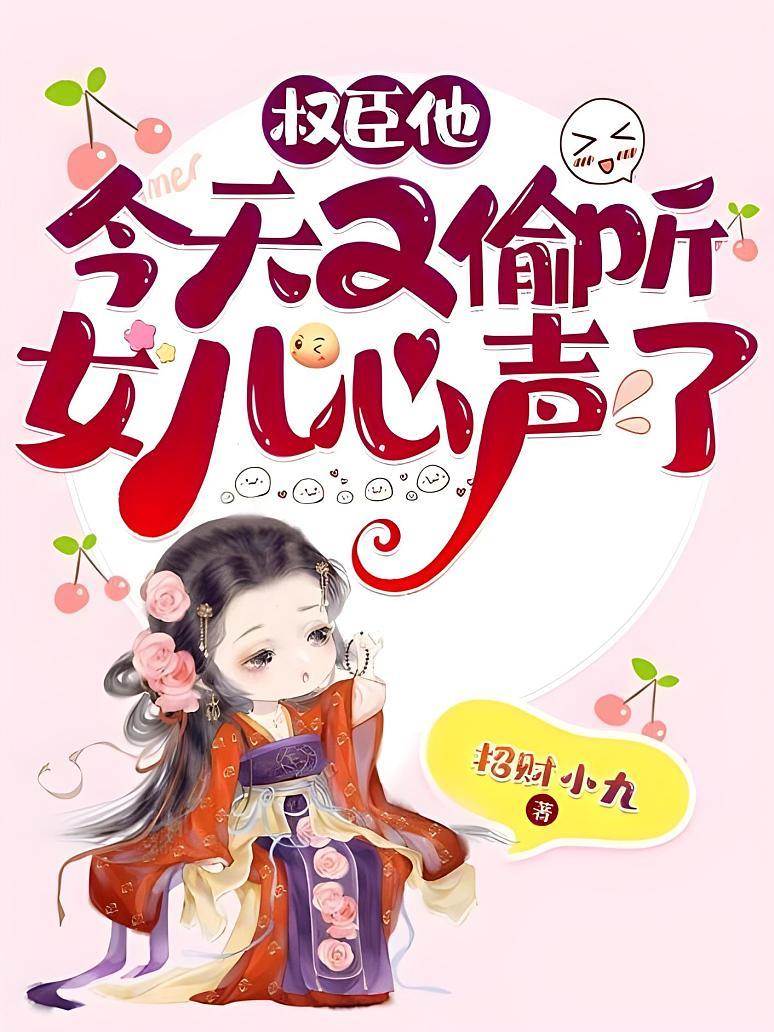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