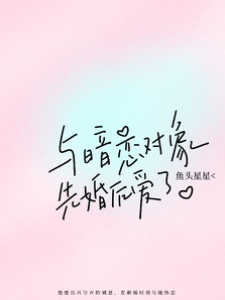《十二年,故人戲》 42.第四十一章 相思未相負(2)
;
他再佯裝不下去。
將抱未抱地站著,遲疑了一會,還是把抱在了懷裡,下在的頭頂上:「那就不走,左右我都在這裡。」屜里放著北上的火車票,是後日上午的,這裡日後會騰空,他也不再來。本沒有什麼好的名聲的人,再荒唐一會也是無妨的。
沈奚挲著,偏過去,臉著,清晰地聽著他的心跳。
半晌,將臉抬起,去著他。從下往上看,他的臉浸在燈里,廓更顯清晰。
他被一雙眼瞧得心頭悶堵,低聲笑說:「三哥不是個君子,也不坦,你這樣子看我,是要出事的。」
話到此,是會要出什麼事,兩人心知肚明。
「……什麼都沒有,」小聲道,「他是和我求婚過,我沒有答應。」
沈奚一鼓作氣,坦白說:「雖然不清楚你在北京聽過什麼,是段家,還是別人說的,或者是你的人打探到醫院裡的傳言,那都不是真的。先前求婚沒答應,之後求婚更不會答應。」 請前往𝕊тO.ℂ𝓸м閱讀本書最新容;
他瞧著。
一時想笑,笑自己是酒醉失意,竟著了的道。
窗外朦朦朧朧有汽車鳴笛的響,像還有蟲鳴,一扇門外,樓梯上也有人在走。這房間裡一旦安靜,才發現這扇門究竟有多不隔音。剛剛……
他的手,扶在後頸。
「辜薇是個不見獵不撒鷹的人,挑這位段家二公子,也是費了不力氣,」他低頭,去找的,「是等著人家的夫人病逝了,做得續弦。這兩年……」這兩年,發生了太多的事,又何必急在這一夜說盡?
中國人喝酒,溫熱了喝,往北走的燒白酒,往南走的紹興花雕,他在二十幾歲時都嘗過。西洋人喝酒,冷的……今日他喝得的就是花雕,溫熱的酒,像中醫的藥湯,灌下去料定是不醉人的,偏後勁足得很。
Advertisement
眼下這後勁起來了,倒像回到二十來歲,最風流最快意時。孩子的舌是最的,含著是用力怕疼,不用力氣親吮又不得勁……;
他輕重呼出的熱量,在的臉上。
「你父親的手……還算是功的,」微微著,不忘今日的要事,「只是……還要看之後的發展,你曉得他年紀大了……」
「醫院來過了電話,」他含糊耳語,「是慶項接的。」
那就好……
沈奚雖不懂為何,但覺得到傅侗文不喜歡和他討論父親的事,總要繞開他。聽他說醫院來了消息,猜到是手後段孟和吩咐人給他消息了,也就不再去提。
「今夜不走了,是不是?」他低聲說。
方才放下那話,是之所迫,這會被他一問,卻不吭聲了。
明知故問……
他笑:「不走,我們去床上說,三哥是站不住了。」
說著,他到開關,撳滅了燈。
「你……」不好意思指摘他,又要上床。;
「央央如今是長大了,不三哥了。」他忽然笑。
先前那樣的況,如何得出。
「來聽聽。」他低聲說。
沒等吭聲,卻又親下來。
外頭,漸漸地下起雨來。
雨落在市井小巷,落在心頭的荒煙蔓草上,聽著雨聲,恍惚覺得自己和他躲在破敗老宅的屋檐下,背靠得不是木門,是磚牆,腳下是蜿蜒水流,眼前是一串串的水珠子……安靜的像是年的,朦朧親昵……
他這樣的人,偏就有這樣的本事,能讓每一場的親熱都不同。
可他真是的初,藏在心路深的懷。他如此有一搭沒一搭親著,仔細地品著,過了會覺得不得勁,小聲:「你來試一試。」
Advertisement
是要試著,去學他的樣子,吮他的舌,吃他的。
沈奚窘了,推他。;
他終於熬不過酒的厲害,打了個趔趄。沈奚忙扶住了他,讓他先上了床。傅侗文斜斜地倚在枕頭上,襯衫解開大半,出脖頸下的膛。
在沒有源的房間裡,瞅著的那雙眼倒是晶亮的,含著水似的。
沈奚擔心地他的脈搏,那裡在一下下地跳著,還算是好。
傅侗文半夢半醒里,在黑暗裡,去的臉,繼而把往上拽。
全都回來了,有關於過去兩人的相細節,在填補著這兩年的空缺。恍惚著,以為,回到了傅家的老宅子……
他在錦被裡翻了,連著被子抱的子,手下不停歇地解白絨線的裳,酒讓人滾燙,興致高漲。白絨線下,是他慕的東西,是「春逗融白膏」,又是「膩初凝塞上」……過去不是沒被他這樣弄過,可久別重逢就是床榻上折騰。
是最陌生,又是最悉,所以最**。;
「三哥……」沈奚低低地求饒。
他去親的脖頸,低低地「嗯」了聲,像不滿足似地在說:「央央的子比過去容易燙了……是長大了。」
在他口中,永遠是孩子,以的年紀在尋常家庭早該相夫教子,在醫院也是獨擋一面的人,在這裡,在他懷中的棉被裡裹著,卻只是「長大了」。
沈奚聽他漸漸綿長的呼吸,揣測他是否已經睡。
他又口齒不清,低語著:「有句話,央央可聽過?」
他沒說是什麼,如何曉得?
「願天上人間,占得歡娛,」他聲愈發低了,「年年……今夜。」
Advertisement
深厚意盡在這一句話里,有對過去分開的不甘,分隔兩地的相思意,還有今夜得償所願重抱人的歡愉。沈奚久久發不出聲,再去他的臉,是睡著了。
一夜雨,從深夜到黎明破曉。;
五點半,沈奚睜開眼,迷糊地看著他的臉在自己的肩旁,沉睡著,他的手還在自己的衫里。棉被胡掩在他的腰以下,蓋著他的下半和的上半。沈奚腳涼了,了下,好冷。面紅耳赤地握住傅侗文的手腕。
輕輕地,從自己服里拉出來……裡頭的洋紗背心被他扯得不像樣。
悄悄瞅一眼,睡著正。
於是地,把白衫掉,重新把洋紗背心穿了一遍。從始至終大氣也不敢出,像和人的大學生似的,著腳,拎著皮鞋跑去了門外……
反手虛掩上了門,左手就是洗手間。
這裡的布局很悉,於是穿好鞋,進去,匆匆洗了把臉,用了臺子上的漱口水,梳子尋不到,對照著鏡子把自己的頭髮散開,用手指刮著草草扎了兩個辮子。
看看四周,他沒過任何擺設,只是在窗口多添了兩盆植。
從洗手間出來,譚慶項剛好聽到靜,在樓梯下張上頭。;
兩人視線對上,譚慶項忍俊不,對悄悄招手,小聲問:「來吃早飯?」
沈奚應了,悄然下樓。
廚房裡,不只有譚慶項,還有周禮巡,兩個男人也是剛才起床的樣子,不修邊幅地穿著襯衫,挽著袖口在那吃粢飯糰和豆漿。因為昨夜兩人隔著一扇門,「旁觀」了一場來勢洶湧的重逢和好,沈奚見了他,窘迫著,在飯桌角落坐下。
廚房本就狹小,三個人滿滿當當。
Advertisement
譚慶項把白砂糖的陶瓷罐推到沈奚面前,為倒了一碗新鮮豆漿:「兩年沒見了。」
這本該是昨夜的話,只是昨晚他不是主角,只好擱在了今日。
「那天……他和我吃飯,你應該一起過去的。」沈奚說。
「開玩笑,我過去幹嘛?」譚慶項好笑,「再說了,他把我大都穿走了,我怎麼去?」
周禮巡嗤地一笑:「還有我的領帶。」;
……
沈奚曉得兩人要調侃,端了碗,湊著喝豆漿。
譚慶項和沈奚的革命友誼深厚,知道兩人之間的事也多,有些話,並不適宜在周禮巡面前掰開碎了談,於是也就沒和沈奚多說,繼續和周禮巡剛剛的談話。
聽他們聊了會,沈奚捋清了一些疑。先前就奇怪,周禮巡漂洋過海回到中國,不該只是幫傅侗文理家裡的事。原來,他幫傅侗文是次要的,北上去見外總長才是主要的。
譚慶項對沈奚解釋:「政府這兩年一面支持參戰,一面也在為戰爭勝利做準備。北京已經聚集了許多外員,還有專修國際法的博士。大家都在反覆研究國際法的條例,想要在戰爭勝利後,順利拿回我們在山東的主權。」
沈奚雖不關心戰爭,可是許多同學都在英法兩國,對戰局也多有點了解。
在去年德、奧陣營就開始衰敗,陳藺觀來信也如此說。;
救國這條路,他一直在實踐,從不顧忌個人名聲的好壞,只在乎更實際的東西,從來從來都不是寫個文章喊個口號那麼簡單。
攪拌著豆漿的調羹,輕輕著碗,像個小孩似地,在想著心上人。
「是侗文說服我回國的,」周禮巡這個法學博士也笑著說,「他是個最能蠱人心的人,我無法拒絕這種,以我畢生所學,為祖國爭奪權益的。」
沈奚好奇問道:「先生是準備北上了嗎?」
譚慶項和周禮巡對視一眼。
其實原定是明日,傅侗文要一道北上,但顯然,計劃是要變了。
兩人默契地,齊齊笑而不語。
周禮巡提前上樓去收拾行李,準備趕火車。
廚房剩了和譚慶項,譚慶項才低聲問:「你和段孟和?」
沈奚搖頭:「都是謠言。」;
雖然醫院裡也常常這樣傳,但和段孟和確實是君子之,除了突然的求婚,沒有任何逾越。不過這裡不比在紐約,男兩人相約出去吃頓飯,或是常在一多說兩句,便已經算是關係。謠言不止,也沒辦法,在醫院的醫生,除了只有一位婦科的住院醫生,追求者眾,也逃不開這樣的命運。
段孟和和總理是親戚,也是副院長,自然關注更多,連累了。
譚慶項笑:「早知有這場誤會,我應當去醫院和你敘敘舊,一來二去,全明白。」
他說得沒錯。
「侗文他……」譚慶項嘆氣,「當年那場病險些沒命,雖然不能說是因為失去了你,但當年那樣被困、失意,你再一走,對他打擊是很大的,」他小聲說,「人生苦短,不想放手的,以後咱們別放,行嗎?」
沈奚被他逗笑。
兩人聊了會,約莫都是這兩年沈奚在上海,傅侗文在北京的事。最後沈奚都忍不住唏噓:「譚先生,你沒有自己的生活嗎?我們也算是生死之了,並不一定只要說他……」;
「我?」譚慶項尋思著,「很無趣啊。」
他兀自一笑,輕聲問:「你們醫院的護士,有沒有未曾嫁人的?我母親催我結婚,是催到已經要跳河了。只是要同我結婚了,恐怕是要北上換一家醫院就職的,」說完又嘆氣,「前些日子侗文倒托人讓我見了兩位小姐,你曉得我自己的條件,小姐是不敢娶的,還是要普通點的人好。」
沈奚想到蘇磬,小聲問:「那位……蘇小姐,你不要再努力努力嗎?」
譚慶項愣了,搖頭不語。
他把幾人用過的碗筷收拾了,放進水池子裡。
沈奚猜想自己到他的肋了,疚著,聽到他背對著自己,笑說:「讓你介紹個護士,你就拿我過去的事來堵,沈奚啊,還是不是朋友了?」
不愧是至好友,佯裝輕鬆的本事都是一頂一。
沈奚順著他說:「好,我幫你留意。」;
今天上午是的門診日,沒法子不去醫院,縱是再捨不得,也是要走的。
沈奚在床畔,枕頭邊蹲了會,看他的臉,只覺得一點都沒有年紀增長的痕跡,反倒比過去更俊秀了。看著看著,覺察出自己的傻,於是留了張字條在書桌上,又去書架上挑了個最漂亮的空墨水瓶著,離開了公寓。
里弄里,鄰居們都在忙活著,在雨里收拾廚房、燒飯。
雨勢未減,要去公事房的男人們都在找尋著雨,沈奚問譚慶項借傘,譚慶項不悉公寓的東西,前後尋不到,無奈只好去和隔壁鄰居借,人家見第一眼驚訝起來:「沈小姐啊,你回來啦?我還說你的公寓是賣給青幫的人了呢。那房子外啊,都是青幫著人在守著……嚇得我們呦,你曉得的,我們這些老實人哪裡見過這樣的場面……」沈奚不曉得如何解釋,含糊著說自己急著去上班。
對方給進去找傘,被屋裡的老人提點了兩句,約莫猜到沈奚的背景也許就是青幫,再拿傘出來時客氣了不,權當方才沒慨過,笑著把傘遞給。笑著說過兩日會拿回來,對方忙道:「沈小姐拿去用,不用急著還,家裡傘多得很。」;
怕趕不及門診時間,倉促而去。
上午的門診照常忙碌,不尋常的是,今日和病人說話,能想到他,寫診斷也能想到他,就連午餐時,聽到幾個住院醫生閒聊昨日大雨,沖塌了一段路,也會想到傅侗文。
午餐後,回到辦公室里,隔壁的醫生又在聽電臺。
胡琴是聲聲不息,京戲是曲曲不斷。
手撐在臉旁,在跟著人家聽電臺,心裡反覆三個字——傅侗文。
電話鈴響。
恍神了一刻,清清嚨,提了聽筒:「你好。」
線路那端是翻書的聲響。
幾乎是一剎那,已辨出是他……
「我在想,晚上要挑選哪一家餐廳,」他說,「是否要有上好的酒。」
他在提出和約會?是正經談的步驟。;
「別喝了吧。」猶豫。
昨日醉得糊塗了,再喝對子也不好。
他在電話里笑:「幾點結束工作?我要去醫院探父親,再接你走。」
「五點,或者,」小聲說,「你更早點來也是可以的,我上午門診後,時間都很自由。」
幸好辦公室里有平日準備的裳,還不至應付不了約會。
他又笑。
笑得莫名失措:「你笑什麼……」
「我在笑,沒有一份正經工作的男人,已經用漫長的等待打發了一個上午,」他道,「我在你們醫院附近的西餐廳,菜品乏善可陳,你如果能早些離開,我很樂意現在接你走。」
猜你喜歡
-
完結62 章

打翻春色
【雙潔京圈甜寵】釣係悶sao清貴大佬??渣又野反骨大小姐!撩欲!極限拉扯!蓄謀已久!初見,溫妤把京城權貴裴譯渣了,男人一眼看穿她,“不想負責?”第二次,溫妤闖進廁所把他看了,男人又問,“還不負責?”第三四五六次,溫妤渣的有些不好意思。第七八九十次,溫妤臉皮已經刀槍不入。直到某晚,溫妤醉酒挑釁,男人反手把她摁在落地窗前,嗓音幽沉,“這次,負責嗎?”溫妤像受驚的小兔子連連點頭。“嗯嗯嗯嗯。”裴譯輕笑入耳:“晚了!”-京圈都說裴譯是禁欲佛子的代名詞。溫妤強烈反對:漏!分明就是反義詞!宴會廳,溫妤問他,“你喜歡我什麼?”裴譯眉眼微彎,“夠渣,夠帶勁。”在場的富家子弟,對於裴譯這朵高嶺之花的戀愛腦表示:“尊重鎖死,早生貴子。”-閱讀指南非女強!輕鬆文!1v1豪門雙強!高潔高甜!男主十年暗戀成真!寵妻無底線!腹黑隱藏病嬌!六歲年齡差!男女主有嘴不聖母!-立意:天之驕子,為愛折腰。
17.3萬字8 6323 -
完結134 章

房東先生是我老公
【隨性灑脫酒吧老板vs清醒理智高中老師】薑梔因為工作調動從清市回到雲市,第一次遇見周晏清是在他家,她要租他的房子。第二次見麵是在她家,他是她的聯姻對象。第三次見麵是在民政局,他從房東先生變成她的老公。……“我和你結婚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不如咱們處處看,兩年為期,不合適就離。”女孩安靜點頭,同意他的提議。後來,他把她堵在床邊,“還離嗎?”薑梔眼眶濕潤,“不離,想要和你永遠在一起。”他是光,是她的救贖,是不可多得的寶藏。立意:即使生活滿目瘡痍,依舊充滿熱愛!【雙潔 細水長流 單向救贖 溫暖治愈】
28.6萬字8.25 7683 -
完結250 章

領帶扯斷!港風美人被大佬攬腰寵
【先愛+曖昧拉扯+日常+男主蓄謀已久戀愛腦】 晏灼妤是獨一份的港風美人,十八歲時因一段演出視頻走紅網絡。 視頻中,烽火連天的戰場,少女身披銀光熠熠的戰甲,烏黑長髮以鮮紅綢帶高束,長戟烈馬,桀驁不馴,被網友譽為荒蕪玫瑰。 裴未燼作為頂級世家的掌權人,手段狠厲、冷酷決絕,人稱「玉面修羅」。 一雙淺灰眼眸冷欲十足,從無緋聞纏身。 卻無人知曉,他被少女鎖骨上那一抹硃砂痣,勾的魂牽夢繞,肖想十餘年。 直到一張照片在網上瘋傳,兩人戀情意外曝光。 照片中,細雨如絲,黑色邁巴赫車上,穿著酒紅絲絨長裙的女人,姿態慵懶地依偎於車身,黛眉緋唇,穠麗旖旎。 美人細白長腿被一雙布滿青色脈絡的修長大手圈住,她嬌縱的將香檳色細高跟踩在男人肩上。 男人虔誠如信徒,寵溺的揉著她酸痛的足踝,赫然是裴家那位掌舵人,裴未燼! 夫妻旅行綜藝上,節目組搜集了嘉賓們的童年照片。 當眾人對一張酷颯的寸頭小女孩照片紛紛猜測時,裴未燼難得露出笑意。 「這是我太太。」 此言一出,全場譁然。 主持人直覺有料:「裴總為何如此確定? 「這張照片是我拍的。」 遇見你是我蓄謀已久的愛意,你如西北野草,我做東風讓你借勢,隨風野蠻生長。 野火燎原,灼燼冬夜。
51.7萬字8 2986 -
完結164 章

禁欲帥哥被我撩得神魂顛倒
【正文已完結➼先婚后愛➕甜寵➕撩漢➕寵妻狂魔➕一見鐘情➕雙潔】【叱咤風云的商業大佬和軟萌少女的先婚后愛】 陳邢人前總是一副矜貴禁欲,生人勿近的樣子,在外是叱詫風云的商業大佬。一到滿半糖面前就總是老婆老婆的追著喊。 —— 欲求不滿的男人:“老婆,貼貼。” 滿半糖:“不要!滾!” 陳邢:“寶寶,求求你。” —— 聽說陳氏集團總裁清冷禁欲,不近女色。 滿半糖:“哼,不過小小總裁,隨便拿捏!” 婚后。 陳邢每日必做就是哄老婆。 陳邢:“老婆,不哭了,好不好。” 陳邢:“寶寶,對不起,我下次輕點。” 陳邢:“寶寶,我保證,就一次。” 滿半糖每天都被他欺負得哭唧唧。 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嘴里沒一句實話。 —— 半夜,陳邢給自己好兄弟發去信息。 陳邢:【原來有老婆是這種感覺。】 沈之杭:【???】 陳邢:【我有老婆。】 沈之杭:【我知道,大半夜你有病啊?】 陳邢:【你沒有老婆,你不懂。】 沈之杭嘴角一抽:這人有病。 —— 大家喜歡加書架,給好評呀!!
21.3萬字8 8196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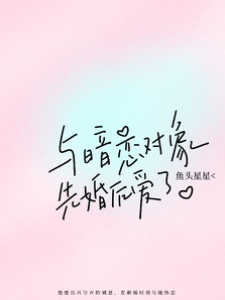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
完結170 章

娘娘嫵媚妖嬈,冷戾帝王不禁撩
一紙詔書,廣平侯之女顧婉盈被賜婚為攝政王妃。 圣旨降下的前夕,她得知所處世界,是在現代看過的小說。 書中男主是一位王爺,他與女主孟馨年少時便兩情相悅,孟馨卻被納入后宮成為寵妃,鳳鈺昭從此奔赴戰場,一路開疆拓土手握重兵權勢滔天。 皇帝暴斃而亡,鳳鈺昭幫助孟馨的兒子奪得帝位,孟馨成為太后,皇叔鳳鈺昭成為攝政王,輔佐小皇帝穩固朝堂。 而顧婉盈被當作平衡勢力的棋子,由太后孟馨賜給鳳鈺昭為攝政王妃。 成婚七載,顧婉盈對鳳鈺昭一直癡心不改,而鳳鈺昭從始至終心中唯有孟馨一人,最后反遭算計,顧婉盈也落了個凄然的下場。 現代而來的顧婉盈,定要改變命運,扭轉乾坤。 她的親夫不是癡戀太后嗎,那就讓他們反目成仇,相疑相殺。 太后不是將她當作棋子利用完再殺掉嗎,那就一步步將其取而代之。 如果鳳鈺昭命中注定要毀在女人手上,那麼也只能毀在她顧婉盈的手上。
32.1萬字8 1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