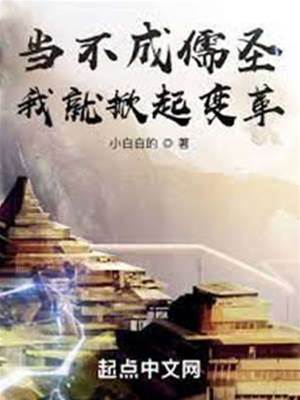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大明春色》 第164章 兔死狗烹
高賢寧送走恩師和朱高煦,回到青樓客房收拾好東西,又在房裡猶自坐了許久。
外面傳來的竹之聲、子拿強調的唱曲,此時已味同嚼蠟,他完全沒了興趣。那些東西雖,確實只能在心中無事、上無勞之時,方能有心境品味。
而現在高賢寧卻一肚子的憂心。豈不言恩師齊泰的安危,是有一條已夠他擔心了:私通包庇欽犯,被燕王的親兒子朱高煦看到。朱高煦只要說出去,一切就完了!
但朱高煦說得也有道理,他若是來害人的,何必如此麻煩?
就在這時,忽然門外一陣喧嘩之聲,有子的聲音道:“那山東口音的人就在裡邊。他的好友出手闊綽,說那山東文士乃太學生哩!”
高賢寧心裡頓時“咯噔”一聲,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覺有甚麼事要事發了!
“篤篤篤……”房門傳來了敲門聲。
高賢寧聽罷,心道既然來人講究斯文、還要敲門,自己也不能無禮在先。於是他起大方地開了房門。這時他馬上愣了一下,因為站在門口的人是紀綱!
紀綱是他的同窗、已任錦衛都指揮使。齊泰剛走,紀綱便出現在這裡,好事還是壞事?
“哈哈……”紀綱笑道,“高兄果然在這等地方。”
高賢寧沉住氣,微笑地作揖道:“同窗別來無恙?”
“你看俺這。”紀綱指著自己的服,又指著高賢寧道,“老兄瞧不起俺,不請俺進去坐坐?”
“失禮了,請!”高賢寧不不慢地微笑道:“我為何瞧不起紀兄?紀兄之生員功名已被革籍,既然未得建文朝恩惠,那投效今上有何不可?而我多年吃著朝廷祿米,每月到縣學領著鴨魚銅錢,因此當年理應為濟南城出力、勸阻靖難軍攻城。你我不同哩!”
Advertisement
“說得好有道理!”紀綱喜道,又回頭道,“這是俺的同窗好友高賢寧,俺兄弟!一篇《周公輔王論》名震天下,連聖上也其才。你們都撤了!”
眾漢子抱拳道:“遵命!”
二人走進客房,紀綱便滿臉笑容道:“高兄與別的儒士不同,不迂腐。誰待你好,高兄便待誰誠心,俺便覺得高兄這樣的人不錯!”
高賢寧道:“紀兄的人該早知道我在揚州了,卻到今日才來。我已領了。”
紀綱笑了笑,沉道:“今上乃太祖之子,並非不能坐天下。今上既然召高兄進京,也算有知遇之恩,待高兄不薄啊。既然如此,高兄不如再看在俺的面子上,進京一回?”
紀綱稍微停頓,又沉聲道:“俺並不想勉強,前陣子聖上下旨召你進京,俺知道你到揚州了,不也沒來強求?但昨日聖上召見俺,俺親自來找你,兄弟就不好辦啦!”
“我願與紀兄進京。”高賢寧忽然道。
紀綱面驚訝之,“真的?”
高賢寧道:“紀兄應知,我不是個玩笑之人。”
紀綱雙手合掌道:“太好了,高兄真乃痛快人!”
高賢寧面帶笑意道:“紀兄記著同窗誼,我豈能拋卻?”
紀綱大笑道:“俺們這就走!快馬返回,還趕得上城門關閉之前進京。”
高賢寧拉住紀綱的袖口,低聲道:“我有一言,紀兄可願聽?”
紀綱道:“高兄但說無妨。”
高賢寧居然附耳過來,耳語道:“紀兄這一行得罪人太多,不是好事。兄可聞兔死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耶?”
紀綱愣了一愣,
笑道:“俺知道,多謝高兄忠言。” 高賢寧的目在紀綱臉上仔細觀察,搖頭微微歎了一口氣。或許紀綱只是知道那兩個詞兒罷了。
Advertisement
當天高賢寧便到了京師。酉時已近,皇帝仍然馬上召見。皇帝見到這個寫周公輔王論、搞得天下士子都知道的人,竟也來歸順了,自是十分開懷。
皇帝當天就封高賢寧為翰林院編修,並在京師賞賜了一座府邸。
君臣相談甚歡,直到深夜。以至於高賢寧只能坐吊籃出午門,並在千步廊後面東側的翰林院衙署裡住一晚上。
高賢寧心裡是清楚的:皇帝如此禮遇,看中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名聲。
天下進士、舉人甚眾,高賢寧一個太學生、功名只是秀才,憑所謂才華、便能與皇帝秉燭夜談?
今上不是漢文帝,高賢寧亦非賈誼。
但高賢寧還有另一個價值,便是名聲。一篇周公輔王論,搞得天下皆知,朱棣要大義就不該攻皇侄建文……而現在寫文章的人已經投靠了朱棣,既未以作則,那文章所寫之義、還能人信服嗎?
……
朱高煦昨夜酉時進城,先去了他爺爺興辦的方窯子“金陵十六樓”之一的醉仙樓,找了個姑娘作陪,聽曲到深夜,然後馬也假裝忘記了取,徑直回郡王府,只等明日再來取走坐騎。
他在醉仙樓順走了一條板凳,拿麻繩拴上,嫻地翻牆回家,然後去了杜千蕊房裡。
第二天一大早,朱高煦便走出了杜千蕊的房間,出門見了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半老徐娘王大娘。王大娘見了他,揶揄地笑了一下,朱高煦也笑嘻嘻地看了一眼。
他便準備到飯廳去,等人上早飯。走到一條簷臺下,卻見姚姬拿著牙刷、剛刷完牙要進屋。姚姬面無表地微微執禮,“見過王爺。”
朱高煦頓時覺姚姬今早似乎冷冰冰的,他疑地點點頭。
Advertisement
就在這時,姚姬又道:“王爺若無事吩咐,我先進屋去了。”說罷轉便走。
朱高煦想到對自己濃意之時,再對照現在的態度,頓時有種冰火兩重天般的反差!姚姬上的氣息,有時候著實讓朱高煦覺得反差太大、有點不著頭腦。
便像現在的忽冷忽熱,又如清純秀麗中的嫵妖嬈。的段也是,沒有寬松的僧袍遮掩了,穿上稍微合的襦,脯簡直大得不協調,但腰姿卻隻堪一握。幸好姚姬材高挑、肩背拔,只是太人。
朱高煦便喚道:“姚姬?”
剛剛走到門口,便轉過來,看著朱高煦,“王爺還有何事?”
朱高煦臉上帶著笑容,走上前道:“你吃醋了?”
姚姬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的表,聲音舒緩,不不慢地說道:“王爺乃宗室貴胄,三妻四妾不是很尋常之事?我在您眼裡,真的蠢到了那種地步,要和富樂院帶回來的一個子爭風吃醋?”
朱高煦一聽,似乎是那個道理。於是他更困,又沒惹,今早為何忽然變冷了?
“那又是為何?”朱高煦收住笑意,皺眉道,“我有時覺得與姚姬十分親近,有時明明在眼前、卻仿佛在千裡之外。”
“沒甚麼!”姚姬目有點閃爍,“我有失禮之麼?”
朱高煦道:“那倒沒有,就算有,我也不在意。罷了,我從來不願強人所難,你若不願意說,那回房去罷。”
姚姬微微屈膝作禮告辭,忽然又微笑著低聲道:“杜姐姐既然要裝,何不裝得像一點?”
朱高煦的角頓時微微搐了一下,馬上又開口道,“難道不舒服,我怎麼沒聽出來?”
姚姬明亮的目在朱高煦臉上拂過,“不仔細聽是聽不出來的,但我能聽出來。”說罷進屋子去了。
Advertisement
朱高煦踱步去飯廳,一路上便在回想剛才的景,尋思姚姬是什麼意思……
難道姚姬識破了他的伎倆, 知道他前天晚上悄悄出去了?於是的冷淡,是因為朱高煦乾這事兒、沒選,所以埋怨他的不信任?
朱高煦真的不夠信任姚姬,因為有些事推敲起來比較蹊蹺;而且問家鄉、底細時,也語焉不詳岔開話題。難道不無腦地信任一個人,有錯麼?
不過,朱高煦也覺得有可能自己多想了。最後那句話意思不明,但並不像指責朱高煦。
他走到飯廳裡坐下來,很快心便好起來,因為丫鬟端上來的早膳、著實看起來很有食。一籠灌湯包,一大碗松花蛋瘦粥,數碟各不相同的鹽水泡菜。
朱高煦昨天下午騎馬二百裡,沒吃晚飯,半夜才從醉仙樓回家,現在著實有點了。
他前世就是一個很重的人,便是滿足需要,不是說條件不好的人、就不能滿足需要。食也,最普遍的滿足不就是這兩樣?其中最簡單又最重要的就是食,一天會三次,至三次食,便是每天都能滿足三回。
朱高煦津津有味地用早膳,心也漸漸好了。
高賢寧答應進京做,又有把柄落到朱高煦手裡,今後朝中就多了一個他的人……這相當不容易,朱高煦不覺得自己作為藩王,在父皇眼皮底下明目張膽去拉攏朝臣、是明智之舉。
但另一方面,王貴一天不帶消息回來,朱高煦一天就無法放心,總在擔心和期待之中。
這種即將得手、又有不確定的覺,就像人生若隻如初見的邂逅,心跳加快。他其實很用。
猜你喜歡
-
完結741 章
醫品嫡妃︰攝政王寵妻日常
聲名赫赫的楚神醫穿越成了被渣男舍棄還揣著崽的絕世小可憐,她小白眼兒一翻只能認命。從此“小可憐”搖身一變,過起了帶娃虐渣、賺錢撩美人的生活,天天美滋滋,日日換新歡,豈料小崽崽的渣王爺爹竟然想吃回頭草?!楚神醫︰“崽!呸他!”小崽崽︰“我tui!!!”某王爺︰“我不是!我沒有!聽我說!”
120萬字8 44828 -
完結589 章

抄家前,王妃搬空王府庫房去逃荒
24世紀醫學天才孫明竹一朝穿越進小說,成了即將被抄家流放的戰王妃。她趕緊將王府庫房搬空,揣上所有財產,帶球流放。流放路上靠著空間內的囤貨吃飽穿暖,一路救死扶傷,還在邊寒之地生崽崽,開醫館,過上了美滋滋的小日子。終於,她那被汙蔑通敵叛國的王爺老公平反了,將皇帝的庶子身份拆穿,登上皇位,來接他們娘仨回皇宮了! 孫明竹:“大寶二寶,來跟著娘一起回皇宮去,可以見你們爹了。” 大寶:“娘,爹爹不是已經死了嗎?你是給我們找了後爹嗎?還是皇上?” 二寶:“不要不要,有了後爹就有後娘,二寶不要後爹!” 孫明竹:“不,那是親爹!” 大寶:“親爹是皇帝?那娘豈不是得去和好多壞姨姨爭寵?我聽隔壁說書先生說,皇宮裏都是惡毒的壞姨姨,娘你這麼傻這麼笨,肯定活不過三集!” 孫明竹:“……放心,你們爹不行,沒這個能耐擴充後宮,他隻能有娘這個皇後,也隻有你們兩個孩子。” 二寶:“那太好了哇!那娘我們回去叭!” 直到回到皇宮,便宜皇帝老公要在她寢宮過夜。 孫明竹:沒事沒事,他不行,也就是睡在我身邊裝裝樣子。 第二天早上的孫明竹:“什麼鬼!為什麼和書裏說的不一樣!我看的難道是盜版小說嗎?”
88.5萬字8 651436 -
完結4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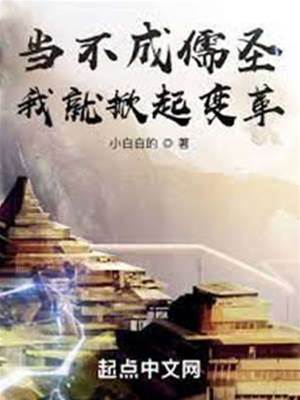
當不成儒圣我就掀起變革
作為一個演技高超的演員,林柯穿越到了大魏圣朝,成了禮部尚書之子。但他是娼籍賤庶!這個世界把人分為上三流,中流流,下九流……而娼籍屬于下九流,不能參加科舉。母親是何籍,子女就是何籍!什麼?三尊六道九流?三六九等?我等生來自由,誰敢高高在上!賤籍說書人是吧?我教你寫《贅婿兒》、《劍去》、《斗穿蒼穹》,看看那些個尊籍愛不愛看!賤籍娼是吧?我教你跳芭蕾舞、驚鴻舞、孔雀魚,看看那些個尊籍要不要買門票!賤籍行商是吧?你有沒有聽說過《論資本》、《論國富》、《管理學》、《營銷學》……還有賤籍盜,我和你說說劫富...
30.5萬字8.18 2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