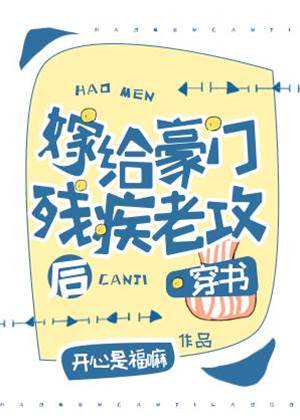《萬人迷反派生存指南[快穿]》 第162章 少主的修仙日常19
奚容本是合歡宗主, 便是個不起眼的小派,也是萬千寵長大的小寶貝,雖說奚容自小沒了娘, 但有姑姑疼, 他爹雖不靠譜,但也從小將他捧在手心里。
整個合歡宗大大小小師兄弟都對他非常好,后來遇見了寒清玉,也是寵著他。
如今突然到了個陌生的地方, 屋子里一大片都是可怕的魔修。
這種魔修是一眼能看出來的,他們沒有藏修為, 也沒有裝作普通修士, 上是邪惡的氣場, 因此奚容就能直觀的到魔修是多麼的可怕。
化神期,他爹也就這樣的修為,還是一宗之主。
現在這麼多在這之上。
而他, 全部是靠在寒清玉才長的修為,自己沒出什麼力,心境和格斗方面本是跟不上, 別說和人對抗了,說不定一出手就會被人拿, 在場的就是個守門的奴才都比他修為高,更何況他的修為很虛。
他在這些眼里就像嬰兒一樣難以對抗任何人, 更何況他離其中修為最高的魔尊這麼近。
本來就做好打算識時務者為俊杰,做小伏低陪個笑,希能饒命。
可誰知魔尊問了一次又一次, 竟要他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這樣的話。
寵侍。
豈不是和他的爐鼎一樣的地位了?
而那些魔修一個個的還看他!雖然是不認識的人, 但被這樣看著笑話, 奚容本不住。
他明明把頭發擋住了臉,又被魔尊輕輕開了,仿佛是要和他的下屬展示他新的寵侍一般,偏偏要他說出這種話,還不讓細作,細作比寵侍有尊嚴多了。
這一刻奚容突然理解了寒清玉當時修為大跌,在山里當他爐鼎的日子,是多麼的沒有尊嚴。
現在風水流轉,到他了。
Advertisement
如此便越想越委屈,心里一陣酸楚,又不知道自己在之后會如何惹怒了魔尊,下場怎麼凄慘,便是哭了起來。
那豆大的眼淚一粒一粒如同明的珠寶一般往下掉,漂亮的眼睛看了過來,眼尾和鼻頭都是微微的淺紅,真是麗可憐得令人心碎。
小心翼翼的委屈的哭,連聲音都沒有發出來,那一滴一滴的眼淚仿佛滴在了人心上。
便是再的心腸都忍不住的心。
不過魔修們應該都是些殘忍腥的家伙,怎麼可能見人哭哭就心放過他呢?
奚容若是在家里哇哇大哭撒個,肯定是一大堆人寵著捧著,可在這兒,本是沒有撒的意思,也不敢哭,卻是忍不住了才掉了眼淚。
甚至怕惹了魔修不高興,還不敢出聲。
堂下一眾魔修都驚呆了。
怎麼就哭了呀?
真的就哭了。
看起來也是摟抱得好好的,本沒有弄疼他,難道就是大聲說幾句話,便把人嚇哭了?
好膽小。
魔尊也真是的,干嘛要惡趣味的著小人說這種話呀?
現在都把人弄哭了。
可是哭起來真的……更可了。
但是的魔修們沒有機會再看第二眼了。
就那麼一瞬間,魔尊已經抱著人進去了自己的寢殿,用寬大的袖袍將人罩著,再也沒有讓下屬們看見一丁點可的臉。
那可怕的魔尊雖是從巖漿里泡澡出來的,但是寢宮里看起來是冷冷清清。
沒有想象中那樣,魔尊的寢宮全是骷髏頭,或者是什麼可怕的裝飾,更沒有花里胡哨價值連城的裝飾。
頂多是夜明珠照明,各種家算是名貴,帳簾的質量和擺設也非常好。
暴戾的魔尊把奚容放在榻上。
和清心閣一樣的,窗邊放著一張榻,那榻很是寬大本來是邦邦的木頭,就在剛才,把奚容放上去的一瞬,已經鋪好了的墊子。
Advertisement
底下是乎乎的棉花墊子墊子,最上面還鋪了一層乎乎的毯子,不知道是什麼靈的皮,又又舒服,人坐在上面細膩又和。
但是此時此刻奚容沒功夫欣賞什麼毯子,也本沒注意到榻有沒有墊著毯子。
只知道魔尊很可怕。
冷冰冰的把他從大廳摟抱在到了房間里,奚容不知道哪里惹到他了,那一瞬間非常快,已經到了寢殿。
奚容往后退了一下,便看見魔尊俯下來。
“怎麼哭了?”
奚容連忙把眼淚掉,“沒、沒有……”
魔尊金的眼眸一直看著他,手了奚容的臉,“是哪里疼?”
在魔尊的眼里,本沒有哭這個概念,他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哭過,但知道疼的話,有的人會哭,那些被懲罰的犯了事的魔修,毒辣的刑罰會讓人下意識的慘痛流淚。
他認為疼才會哭。
見奚容就這麼哭了起來,便以為哪里弄疼了他。
瞧著是好好的,但這小孩像個爺,白白養得極為氣,說不定方才沒輕沒重便將人弄疼了。
問他。
他卻又搖頭。
那漂亮的手自己了一把眼淚,但麗的眼睛又潤了,一會兒又涌落出更多的眼淚。
那可真如珠寶碎玉一般的麗,是瞧著便令人心都碎了。
魔尊呼吸一窒,連忙去看他上哪里傷著了。
漂亮的臉蛋和在外面的手沒有任何外傷,查了一下息,靈力也是暢通無阻的流。
魔尊便將他鞋了,看看他的腳。
那潔白的小足出來的一瞬間,簡直像一件麗的藝品。
骨頭真是麗極了,通潔白,腳踝的關節是淺,便是捧在手心里把玩都能玩上許久。
但整個麗的小足也沒有外傷。
難道上哪里傷了,要不然怎麼哭得這麼慘?
Advertisement
于是便去他服。
沒想到這次招到了奚容的劇烈反抗。
“你干什麼?不要,不要!”
奚容被他突如其來的作嚇到了。
他那麗的羽穿著上,扯掉腰帶,全的服都松了,但他掙扎得厲害,像只不聽話的小貓似的,也許上有傷,一掙扎可能會更疼了。
魔尊冷冰冰的呵斥,“不準。”
那腔調可怕極了,仿佛要是奚容不聽話會有更可怕的后果。
他一說,奚容便是不敢了,只能任由他解開服。
但是哭得更是厲害,已經是哭出聲音來,整個人水做的似的,眼淚回來了的掉著。
魔尊覺得也可能剛才掙扎的時候有把哪里弄疼了,便是快速的將服全部拿了去。
魔尊的眼眸微。
好漂亮。
他麗的小寵侍真是漂亮極了,世上最麗最珍貴的寶都不及他萬分之一。
見他雙手抱著他自己,以為他是冷,便連忙用靈力有將邊的溫度弄高了些。
好脆弱。
本來是怕他冷著了,已經是將周圍的溫度弄了暖和,可他仿佛還是冷。
他手一,發現奚容在發抖。
魔尊的眼皮跳了一下,連忙把人輕輕的翻來覆去瞧了一遍。
見著實沒有什麼傷口,也不見是被弄疼了的紅痕,只是手腕上有些紅,顯然是剛才他抓著奚容的手腕,多用了些力,那那麼輕輕的握一下便已經留下了紅痕,真是。
見他打開了雙手,又覆而摟著自己,便以為他真的冷,連忙用茸茸的大毯子將他包裹起來,用用被子蓋著。
再俯輕輕摟住他。
“怎麼還哭得這麼厲害?是哪里疼了,還是冷?”
又是抖又是哭,真是可憐極了,直將人心都弄碎,被子好好裹著了,小毯也蓋好,再將周圍的溫度調到最舒服溫暖的程度,卻還是沒把他弄舒服。
Advertisement
如此便覺得他可能在疼,將他纖細雪白的腕子握在手心里輕輕的。
他曾吃掉過自己的一只靈,就此有了些靈的功能,他的唾像那靈一般有特有的治愈功能。
但一會兒那手腕子更紅了,仿佛那整個手腕,連周圍的皮都被淺暈染開來。
見人還在抖,便是了冷冰冰的外,一同鉆進被窩里幫他暖著。
那榻上終究是不舒服,便帶著毯子將人一同摟抱到了床上去睡。
魔尊的溫比尋常人要熱一點,因為練功走火魔,曾傷了筋脈,如今每隔一個月便要去炙熱的巖漿里泡上一圈,的火氣很大,一會兒便將床弄得暖烘烘的。
他的服也換了的里,便把奚容上的服扯掉,將人好好摟在懷里。
漂亮的小寵侍僵了一下,還在搭搭的哭。
那氣氣的樣子,再哭可能要哭壞了。
魔尊連忙幫他眼淚,又輕輕拍他的背脊哄,卻怎麼哄都哄不好。
腦子里沒有任何哄人的話,只能冷冰冰的命令,“不準哭。”
這一說,哭得更厲害了。
好像開頭還自己憋了一下哭意,接著哭得更兇。
魔尊這次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便把人摟著他的眼淚,終于知道了自己可能把他嚇壞了,便輕輕的哄。
“別哭了,沒有想弄疼你。”
聲音放輕。
見懷里可的小寵侍也沒那麼繃發抖,如此便知道怎麼哄人了。
“別哭了,不哭……”
好氣。
像易碎的寶一樣,不僅是作要輕輕的,說話也不能重,便是平常語氣說話也不能,稍微重一點都要把人嚇到。
“你什麼名字?”
問了,也沒有聽見答復。
小寵侍搭搭的哭,把他口都哭了,如今哄了一番,已經放松,漸漸睡去。
就在他懷里,也不,特別的乖。
摟抱在了后半夜,突然想起。
他記得把人帶回來的時候說是要他做自己的小寵侍,要他暖床的。
如今倒好,哭了大半宿,哄了順著才不哭了。
又把被窩里弄得暖烘烘的,怕他冷。
他倒是反過來了暖床人。
猜你喜歡
-
完結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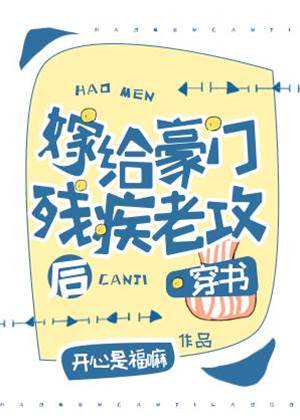
嫁給豪門殘疾老攻后
景淮睡前看了一本脆皮鴨文學。 主角受出生在一個又窮又古板的中醫世家,為了振興家業,被迫和青梅竹馬的男友分手,被家族送去和季家聯姻了。 然后攻受開始各種虐心虐身、誤會吃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會變成船戲之路。 而聯姻的那位季家掌門,就是他們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季靖延作為季家掌門人,有錢,有顏,有地位,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可惜雙腿殘疾。 完美戳中景淮所有萌點。 最慘的是自稱是潔黨的作者給他的設定還是個直男,和受其實啥都沒發生。 他的存在完全是為了引發攻受之間的各種誤會、吃醋、為原著攻和原著受的各種船戲服務,最后還被華麗歸來的攻和受聯手搞得身敗名裂、橫死街頭。 是個下場凄涼的炮灰。 - 原著攻:雖然我結婚,我出軌,我折磨你虐你,但我對你是真愛啊! 原著受:雖然你結婚,你出軌,你折磨我虐我,但我還是原諒你啊! 景淮:??? 可去你倆mua的吧!!! 等看到原著攻拋棄了同妻,原著受拋棄了炮灰直男丈夫,兩人為真愛私奔的時候,景淮氣到吐血三升。 棄文。 然后在評論區真情實感地留了千字diss長評。 第二天他醒來后,他變成主角受了。 景淮:“……” 結婚當天,景淮見到季靖延第一眼。 高冷總裁腿上蓋著薄毯子,西裝革履坐在豪車里,面若冷月,眸如清輝,氣質孤冷,漫不經心地看了他一眼。 景淮:……我要讓他感受世界的愛。
16.2萬字5 6189 -
完結89 章

打死不離婚[ABO]
俞抒和喜歡的人結婚了,但他只是個替身,而且他還帶著不可見人的目的。 進了徐家之後這不疼那不愛,盡是一群使絆子的,俞抒都忍了,因為喜歡徐桓陵。 可徐桓陵喜歡的,是俞抒的雙生哥哥,心里永遠的白月光。 一次偶然,徐桓陵標記了俞抒,真正的噩夢開始……。 噩夢結束,剩下的只有不甘和憎恨,渾身是傷的俞抒爆發了。 誰想知道真相的徐桓陵居然幡然醒悟,白月光也不要了,想當牛皮糖。 俞抒望著中毒一樣的徐桓陵,把兒子偷偷藏起來,然後給徐桓陵寄了一份離婚協議。 追妻路途長,挨虐路更長,徐總點了根兒煙把高冷的臉湊過去等著挨打,只想見見兒子,抱一下老婆。 PS:前期渣攻,後期追妻狂魔撩人不要錢;前期深情隱忍受,後期火力全開腳踹八方。 先婚後愛,微虐下飯,又酸又爽,有包子,有各種渣,極其狗血,雷者繞道。 一貫先虐後甜,有萌寶出沒,雙潔HE。
24.7萬字8 64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