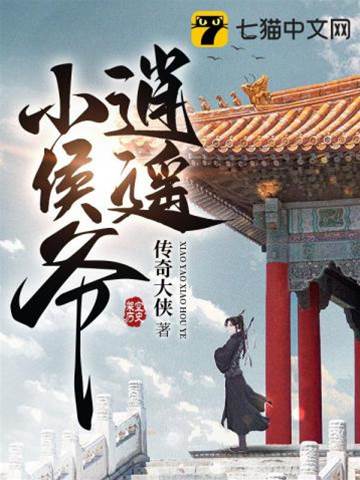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回到明朝當王爺》 0106章 紅袖侍酒
柳榆槐樟,沿著溪水錯落生長.因為這幾日剛剛下過大雨,山中洪水瀉過的痕跡十分明顯,一些老樹挨著河水的樹虬結在外面,落水干涸的河道上散落著一些枯樹干。
一株垂楊柳下,斜斜的是一塊大青石,石下匯一方湍旋清澈的河水,大約一人多深,四丈方圓。左邊山坡上就是左哨營五百親軍建起的營房,山道下是高老莊,從這兒可以俯瞰整個村莊,看清自已家園中的院落亭臺。
進六月中旬,天氣炎熱,鄉村環境雖然清靜幽雅,可是知了晝夜聒噪不休,人難以睡。此時,一張香妃竹榻就搭在小河邊上,楊凌跟老太爺似的躺在竹榻上,斑駁的灑在他的上,讓人昏昏睡。
他的雙手雙腳都纏著白布,一魚竿兒矗在他的前,魚漂兒在水面上輕輕地打著晃兒,魚兒早了釣,卻無人去換上魚餌。
從京師回來已經十天了,楊凌被夾拶指弄得模糊的手腳在神醫高文心的心侍候下早好的七七八八的了,可是韓娘、玉堂春幾人不敢大意,見他腕上足踝初生,怕磨破了皮兒,仍然縛著厚布好生將養。
下這湘妃竹榻是嚴嵩贈送的禮品,嚴家在地方上算是個小地主,進了京城可就排不上字號了,既送不得大禮,干脆送些應時的雅,倒合楊凌的心思。
楊凌對帝陵取回的土壤為何沒有破綻,一直心下存疑,嚴嵩拜訪時他也曾旁敲側擊地試探了一下,嚴嵩心里一直以為國公和王守仁才是奉旨作弊的人,說不定楊凌也知道真相,所以倒不敢據功自有,更不敢說出實。
可是他既以為自已窺破了其中,又心難搔,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也是助了把力的,所以言語間不免出些許消息,楊凌聽出是國公、王守仁和嚴嵩三人聯手助他渡過難關,心中的激自然難以言喻。
Advertisement
回來這幾日,錦衛錢寧、于永,神機營三司佐、宮衙門劉瑾、馬永等這些有、有關系的人大多親來探,走不開的也托了人送來厚禮。
這些人出手何止千金,楊凌挨了頓打,上了趟菜市口表演了一通清秀,忠臣名譽遍傳民間,還賺得缽滿盆溢,戴義、李鐸、倪謙幾人可沒得比,不但比不了,他們還得買了禮也上門來探楊凌,到此形他們也知道能夠免死九九是賴著楊凌,這個探自是謝恩,只是彼此都心照不宣罷了。
楊凌曾任職東宮侍讀,歸屬詹士府管轄,所以詹士府也禮節地派人前來問候了一下,楊凌如今是帝前寵臣,灸手可熱,詹士府也不敢怠慢了,竟然派來一位翰林學士問。
楊凌是宣府最年輕的秀才,十六歲就得了功名。詹士府派來的這位更不含糊,這位正德帝的侍講學士名楊廷和,十二歲時就是名滿蜀的神,由學政特批跳過生、秀才直接考上舉人,十九歲中進士,二十歲翰林,那一溜兒輝煌,楊凌的學歷跟人家一比,可真是米粒華與日月爭輝了。
好在這位年近五旬的楊學士為人很隨和,平素說話也絕不因為自已飽讀詩書就開口閉口的充滿酸腐氣,兩人一番攀談,楊凌對這位侍講大學士頓生好。
楊廷和本來只是礙于皇帝的面子,才了詹士府差遣前來看,對這位秀才出、火箭般串升起來的帝前寵兒,他心中也是不以為然的。
可是一經攀談,楊廷和發覺這位秀才說話雖然雜無章,對于種種事務的看法沒有一個系統的觀念,但是每每口出奇語,必一言中的,或能道出其中厲害,若能舉出解決之法,雖然有些奇思妙想過于激進,未必適合朝廷采用,但是這種超人一等的見識就是許多飽讀詩書的宿儒也想不出來,有時漫不經心的一句話,細細想來竟是大有道理,楊廷和不對他刮目相看,頓時收了怠慢之心。
Advertisement
幸好楊凌不知道這位本家的赫赫威名,與他攀談時想起點什麼才無所顧忌地放膽直言。他的學問雖比不得楊廷和,可是偶爾隨意一句話,有可能就是后世有識之士觀諸歷史后總結作下的結論,他這時說出來,在楊廷和眼中,自然覺得此人頗有遠見,見識不凡。
這就象一個頑和一個武林高手,頑無意間的一句話,一個舉,恰好蘊含了什麼至理在里面,他自已雖茫然不知,可是看在行家眼里,卻是大啟發。
楊凌說的那些不系統的錯錯落落的觀點、見識,楊廷和可不敢以為這些發人深省、前所未聞的話楊凌本人也不知就里,還道人家是不肯深談。
但他學問何等深厚,只消此啟發,結和他的學識和經驗,自然推演衍化出真正可以施之于朝政的舉措,這一來楊廷和可不敢當他是不學無之輩了,還道此人深藏不,不由對他肅然起敬。
楊大學士倒不忌才,回去后提及楊凌,頗多贊譽。楊廷和在翰林院中是極有威的才子,有他一句贊語,再加上那個新晉的翰林嚴嵩沒命地吹捧,原本對于楊凌越級高升,比他們苦讀多年還在翰林院熬年頭混日子覺不滿的翰林們可不敢太張狂了,原本經常公開斥責楊凌秀才出、難稱大任的馬上得多了,這樁好倒是楊凌始料未及。
李鐸戴義等人其實第二天來看了楊凌后便趕回泰陵去了,倒不是他們傷勢好的比楊凌更快,而是現在他們不得當初被洪鐘打的再狠一點,如果他們被抬回泰陵督工,才顯出他們對朝廷的忠誠呢。
楊凌這回也學了個乖巧,不敢再怠慢公事貽人口實,本想跟著趕回泰陵去,戴義卻以為他是“放心”不下那位誣告他的王三爺,急忙地拍脯、表忠心,一副“我辦事你放心”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可他一臉的笑,楊凌可不想和王瓊解下不解之仇,看了他模樣反而更不放心了。恰在這時,當今正德皇帝的恩旨到了,正德皇帝這道旨意,先把弘治帝送給楊凌的那副懸崖勁松圖送了回來。
估計正德皇帝也知道怎麼比他也比不過先帝的繪畫水平,所以那畫上他也沒敢胡涂抹,填首詞加句詩什麼的,不過他卻加蓋了一方大印。比字畫比不過老爹,那就比誰的印大好了,正德那方印,跟玉璽差不多大小,好一副山水畫,上邊通紅一個四四方方大印,怎麼瞧怎麼不倫不類。
正德旨意上誥封了韓娘為三品誥命夫人,囑咐楊凌好好養傷,在家中靜候旨意安排,楊凌本來就不是真心想去修墳,這一來就順理章留在家里福了。
迎來送往的忙了幾日,今兒消停了,楊凌就人搬了竹榻,和娘到這山澗溪水旁乘涼釣魚。韓娘見相公有了倦意,輕輕將溫潤的小手從他手中了出來,拉過一旁的薄衿替相公搭在腰間,然后踮著腳尖兒悄悄地走開了。
這一,只是略有倦意的楊凌就醒了,楊凌瞇著眼,悄悄張開條兒看著娘,只見韓娘躡手躡腳走開了些才恢復了形,站在一棵樹下轉了兩圈兒,仰著臉兒打量一番,又鬼鬼祟祟地扭過頭看了眼楊凌。
楊凌好奇心起,不知道娘要干什麼,一見扭頭,忙閉了眼裝睡。韓娘見楊凌睡了,又四下張幾眼,然后飛快地拉起裾塞在腰間,挽起兩只袖子,往掌心里淬了口唾沫,雙手一攀樹干,雙手替攀援,迅捷得像只靈猴兒,俏左晃右晃的,刷刷地攀上了高高的樹干。
楊凌吃了一驚,本來還怕韓娘摔下來,可是看到這麼矯健的手,不大為嘆服,韓娘站在樹干上神間很是欣然,好象很久不曾玩過這游戲似的。
Advertisement
這是一棵有些年頭的老桃樹,下邊的枝干被樵夫已經砍去,只留下些尖銳的枝權,樹冠茂盛的葉子里掩藏著許多核桃大小茸未褪的青桃。
韓娘踮著腳尖摘了些下來,從懷中掏出一方手帕包好,又揣回懷中爬下樹來,跑到河邊將青桃拿出來在河水里洗凈了,拿起一個來喀嚓咬了一口,也不管那桃子是否酸,吃的津津有味兒。
楊凌悄悄站起來,慢慢走了過去,他的腳腕上纏著厚厚的布帶,不是那麼靈活,一不小心踩在一塊石頭上,嘩啦一聲,把剛剛從河邊站起來的韓娘嚇了一跳,子一跳,一腳踏進了河里。
等忙不迭地把腳拔出來,扭頭瞧見相公笑地站在邊,不尷尬地站在那兒,著腦袋象個等著挨訓的孩子,小里還著一角泛著清香氣的桃子。
楊凌瞧見韓娘裾扎在腰帶上,一只繡花鞋水淋淋的,左手用手帕兜著六七個小青桃,右手拿著個啃了一半的,微黑俊俏的臉蛋兒紅撲撲的,俏的鼻尖上還掛著兩顆細的汗珠,就那麼傻傻地站在那兒,不噗哧一笑,說道:“我的三品誥命夫人,在做什麼壞事?”
韓娘一向溫婉賢惠,楊凌都幾乎忘記了的年齡,瞧現在這副模樣,才省起是個從小在山里野慣了的孩子,說到底如今不過才十六歲而已,正是貪玩瘋的年紀,卻已相夫持家,扮作人婦了,也虧得能忍了這麼久。
見韓娘憨態可掬地站在那兒,難得出副傻傻的表,楊凌笑嘻嘻地替把擺拉下來,拂開腮旁的發,溫地道:“喜歡吃青的果子,回頭家人去買就是了,這樣的野果子帶些味兒,不好吃的。”
韓娘本調皮好,自嫁了這秀才老爺可不知忍了多久了,今日回到悉的山林一時忘形,居然爬樹摘果。做為一個已婚婦人、又是誥命夫人,這般不顧形象,還真擔心楊凌責備,可是一瞧楊凌滿臉寵溺,韓娘提著的心才放了下來,趕咽下里的桃子,丟開手里啃了一半的桃子,忸怩地捉著角窘道:“相公,人家......人家......對不起......”。
楊凌笑笑,不以為然地道:“不就是爬了樹嗎?爬就爬了唄,咱家沒那些七八糟的規矩”,他攬住娘肩膀往竹榻旁走,邊走邊道:“你別想那麼多,這些天在家,我只見你打坐練氣,那棒功夫可是好久不了。
娘,練武功可以強健,并不是什麼低三下四的行為,誥命貴婦怎麼了?你別太在意別人看法。別忘了,市井間現在可都說相公是楊家將后人呢,楊家的子武藝高強那是理所當然的,呵呵,回頭我兵丁在后園開出塊地來,以后每天你仍要練武,相公也跟你學”。
他坐在竹榻上,順手一扯,韓娘就跌坐在他上,韓娘忸怩地作勢掙扎了一下,就笑著不作聲了。楊凌攬著娘的纖腰,著耳朵道:“娘,這兒長大了不喔”。
抓住楊凌的手,不可抑地道:“相公,不要,這是在外邊啊”。
楊凌嘿嘿一笑,不忍見難堪,順勢放低了手,一到那水淋淋的青桃子,楊凌忽地心中一閃,驚喜失聲道:“娘,你是不是有孕了?怎麼......怎麼吃酸桃子?”
說著他的手不自地向娘平坦的小腹,韓娘的推開他手道:“沒有呢,沒有呢,人家從小就吃青桃兒”,說著轉過臉兒來,怯怯地道:“相公,娘是不是太不爭氣了?”
楊凌失笑道:“怎麼會,我們繼續努力,總會有的嘛,再說,如果不生也不見得是你的事”。
“嗯?”韓娘詫然不解其意,人不就是生孩子的麼?如果不能生不是人的罪過還能怪誰?
楊凌不想跟解釋那些太難說清的東西,看了俏眸圓睜,一臉詫然的可模樣,不在頰上吻了一下,笑道:“來,了鞋子吧,著穿著不舒服”,說著不由分說替娘褪下鞋,出一雙白生生的小腳丫。
人的腳可不是隨便給人看的,就算是自已相公,大白天兒的在這外面韓娘也臊的不行,忙將腳丫蜷到榻上,拉過薄衿掩住。在心里,還是牽掛著方才丈夫滿臉的失神,真的呢,都同房四個月了,這肚子咋這麼不爭氣呢?
小妮子著肚子,連吃青桃的胃口也沒有了,嘟著小兒想了半晌,忽然吃吃地道:“相公,皇上什麼時候大婚呢?”
楊凌心中一跳,丟下自已剛下的靴子吱吱唔唔難以應對,皇上大婚就是他納妾的時候,還是奉旨納妾,怎麼拒絕啊?
自打從京里回來,這事兒他就有意避而不談,反倒是府中上下,人人都適應的很,好象老爺納妾天公地道似的,尤其皇上所賜,府里的奴仆出去對人說起都一臉的自豪。玉堂春和雪里梅也早已自覺地以妾禮侍奉他和娘了,那玉娘姐姐起來,似乎也別有一層寓意。
楊凌滯了一下,支唔道:“皇帝賜下,相公也不知如何拒絕了。玉兒、雪兒都是好姑娘,可是你也看到了,場險惡,這次倒了三位尚書,朝中不知多大臣對我不滿呢,跟著我......未必是福啊”。
韓娘雙手摟著膝頭,淺淺一笑起來:“相公總是杞人憂天呢,娘真不知道相公到底在擔心什麼,相公不要怪罪娘大膽,相公,你以為要如何對他們,們才會開心、才會幸福呢?”
幽幽一嘆道:“相公,你不知道皇上許了親事后們心里有多歡喜呢,我卻覺得出來。有時想想,人家進了咱家的門,不這樣還能怎麼辦呢?娘知道相公疼我,可是要是娘得了個善妒的罪名,娘......真的不會開心呢。
對玉兒、雪兒來說,能夠跟了相公,就是們的福氣。們雖出卑賤,可是重重義,咱家落難的時候,肯舍命陪著咱,相公兒越作越大了,妻妾滿堂是娘預料中的事,如果真要迎些姐妹進門兒,娘倒愿是們呢”。
說著拉住楊凌的手,聲道:“相公,那日我們決定去法場喊冤,都知道如果事不可為,便只有陪著你一死的份兒。娘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可是玉兒、雪兒妹妹,還有文心姐姐可沒理由陪著咱送死呀,咱可不能對不起人家。
唉!如今玉兒雪兒終有了依靠,文心姐姐都十八歲了,了老姑娘,卻......皇上把賜給了咱家,就是咱家的人了。相公回頭和皇上說一聲,不如把也收了吧,反正妾比婢份也高不了哪去,皇上不會計較這事兒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連載617 章
大唐醫王
一個現代醫師回到貞觀年間,他能做些什麼?如果他正好還成爲了李淵的兒子,李世民的弟弟呢?李元嘉,大唐醫王。
117.4萬字8 29994 -
完結195 章
嗜寵夜王狂妃
世人皆傳:“相府嫡女,醜陋無鹽,懦弱無能”“她不但克父克母,還是個剋夫的不祥之人”“她一無是處,是凌家的廢物”但又有誰知道,一朝穿越,她成了藏得最深的那個!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傾城容顏,絕世武藝,腹黑無恥,我行我素。他是帝國的絕世王爺,姿容無雙,天生異瞳,冷血絕情,翻手雲覆手雨,卻寵她入骨,愛
74.8萬字7.92 52514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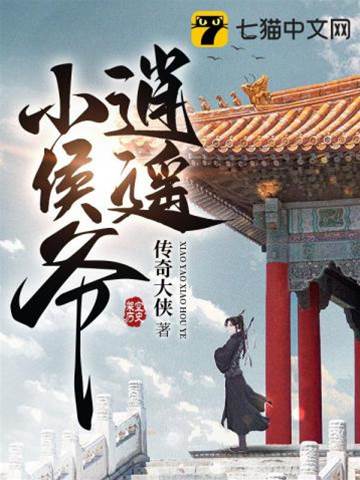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