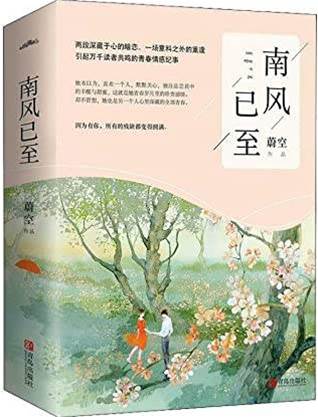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緋聞前夫,請離婚》 第1卷 第447章 他正在陪少奶奶
紀瀾希為了顯示自己的病態,還特意畫了個看起來弱柳扶風的妝容。
徐傲秋夸聰明,勾冷笑,如果蠢了,早就在這里待不下去了。
兩人去了蘇黎住的別墅。
卻被保鏢給攔住了:“紀小姐,太太,你們不能進去。”
“我來找我兒子宴初,有什麼問題?”徐傲秋一聽這話,很是火大。幾個保鏢,都敢攔,真是膽大包天。
紀瀾希拉了拉的服:“媽,他們也只是奉命行事,不如讓他們去跟哥說一聲吧。”
“麻煩你去告訴我哥一聲,就說我們有很著急的事需要找他。”紀瀾希得的笑著,看向保鏢。
保鏢點點頭,走了進來,紀小姐果然比徐傲秋要懂事的多。
保鏢想。
蘇黎和陸宴初在一個桌子上吃飯,本來不愿意和他一起吃飯,可他搬出來一個月約定的事說事。
想到熬過這一個月,就解,便忍下來。
蘇黎不想和他太多接,吃飯也快了許多,都沒怎麼挑菜,只是吃著白米飯。
Advertisement
保鏢此時來了,跟們說:“,陸先生,太太來了,還有紀小姐也來了。在門口等著呢。”
蘇黎一聽紀瀾希來了,眉頭一皺,碗里的白米飯都覺得倒胃口。
正要讓陸宴初把紀瀾希和徐傲秋帶走,不要打擾,可還沒開口呢,就聽到陸宴初冷漠的對保鏢說:“我沒空,讓他們倆回去吧。”
他已經著了紀瀾希太多次的套路,現在他一定要和劃清界限。
哥哥和妹妹,就只能是哥哥和妹妹,多一點關系也不能有。他不能讓阿黎再傷心。
保鏢愣住了:“啊?”
“你開車送他們回去。”陸宴初說完,就繼續吃飯。
保鏢轉就出去了。
蘇黎繼續吃著飯,不一會,就聽到外面的大喊大聲:“宴初,你出來!你出來啊!看看瀾希,都發高燒了,非要看到你才肯吃藥。”
蘇黎放下碗筷,看了眼他:“你去看看們吧,我不喜歡太吵。”
說完,就回了屋。
Advertisement
站在玻璃窗前,看到外面下起了暴雨。
紀瀾希和紀徐傲秋就那樣被淋著雨,也不離開。
當然陸宴初也沒出去。
紀瀾希讓雨水沖刷的眼睛很難睜開,狼狽的不像話:“媽,我就是個笑話。哥不愿意見我啊!他寧愿我淋雨,都不愿意見我!”
“瀾希,我們回去好不好?你在發高燒啊。瀾希,他現在讓蘇黎那個賤人給迷住了。不會見我們的。”徐傲秋哭著勸道。
紀瀾希不信陸宴初會狠心到這個地步,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會不會堅持一樣,他就出來了。
跪在了雨地里,徐傲秋嘆氣:“瀾希,你這又是何苦?”
“我一定要等到哥出來!陸宴初,你別想躲著我!你什麼時候出來,我什麼時候走!”紀瀾希大聲喊道:“我知道你就在里面看著我!是個男人,就出來見我,躲在里面,算什麼男人?”
想激怒陸宴初,這樣他或許就出來了。
然而說再多的話,浪費再多的口舌,他也沒出來。
Advertisement
蓉姨撐著傘來了,勸道:“紀小姐,陸先生今天真不方便見您。他正在陪呢,您要不先回去?下這麼大的雨,您的子要啊!”
蓉姨也看不慣紀瀾希,覺得紀瀾希忒不要臉了,都沒主找麻煩,還上門挑事,脾氣好不計較,換自己早就放狗咬人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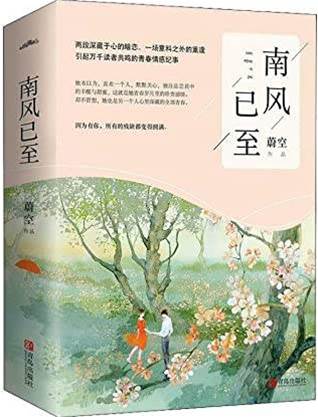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