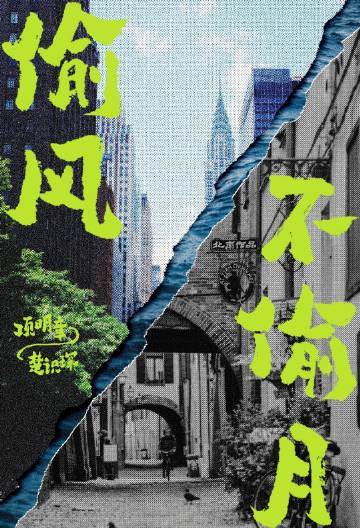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許你兩世相顧》 第255章 不會是你老相好吧
“言然……”溫言之眉眼突然和了下來,抓著阿楚的手一松。
阿楚見狀,立馬從他上逃了下來,像避瘟神一般往旁邊躲閃。
溫言之眼神松,他眼中的和一下子散去,臉上布上了霾。
原來還是,他的言然沒有回來。
他有些失,自顧往前走去,阿楚覺得他有些不對勁,默默地跟在后面,“喂,溫言之,好歹我也是顧言然啊,怎麼對待我們倆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啊,你對溫的可是能滴出水來啊。”
“你不是。”溫言之停下腳步,語氣有些冷。
阿楚撇撇,“可是還是同一個不是嗎?”
溫言之轉過,“你都說了,這也是的,我希你不要做什麼危險的事,傷害的不僅是你,還是。”
“得了,得了,不就是心疼嘛。”阿楚哼了一聲,往前走去,“劉楚佩傻,有人疼,顧言然單純,有人,我就不一樣了,不傻不單純,但是什麼也沒有,還被人一通嫌棄。”
慘,真是太慘了,阿楚自己都開始心疼自己。
“你放心,這也是我的,我自然會好好照顧的,倒是顧言然,你應該好好看著,我也就沒出來一段時間,就盡出些幺蛾子,連毒品都讓人給注上了。”阿楚無奈道:“那脾氣,有過一次兩次,以后還會有三次四次的,你怎麼可能每次都在旁邊。”
“要我說,直接讓我陪著不就好了,我能讓被人欺負?”阿楚看著溫言之,自信滿滿道:“我可從來沒在別人那里吃過虧。”
“你瞧,今天江杉那小賤蹄子不就被我整治了嗎?”阿楚說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讓顧言然理,我得等到天荒地老了。”
溫言之皺眉,“今天的那個人是你?”
Advertisement
“對啊,怎麼了?”
“你已經出現了一天了,那顧言然相對應的,也會有一天時間的記憶空白,你這樣對很不好。”
阿楚豎起食指,擺了擺指頭,“不不不,不是一天,昨天我也在,應該說是差不多兩天了,應該說,那天從醫院去學校的路上就是我了。”
溫言之的眼神更加冷了,“是嗎?那你演的可真像。”
阿楚聳聳肩,“自然了,我和一起長大,什麼格脾氣,有什麼習慣,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要是演的不像,早就被許家的人發現了。”
“那你今天是故意暴自己的?”雖然是問句,但是溫言之的語氣里滿是肯定 。
阿楚點點頭,“算是吧,不然你也發現不了的。”
“目的呢?”
“我需要你的幫助。”阿楚真切地看著他,“我有時候會替顧言然做一些事,但是又需要有個人接應,我想不到更合適的人了。”
“這麼信任我?”溫言之挑眉?
“不是我信任你,是言然信任你,這件事我都聽的,對你有執念,但對你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你可以在你出現時,告訴我。”
“可以。”阿楚點點頭,“若是你溫言之的時候,就是我阿楚了。”
阿楚拿出手機,撥了一個號碼,隨之溫言之的手機響起,“這是我的號碼,你存一下,到時候我會拿這個號碼聯系你的,你可別撥錯了。”
“你倒是警惕。”溫言之笑笑,這謹慎的子跟顧言然倒是一模一樣,但是顧言然比阿楚更一些。
“謝謝夸獎。”阿楚挑眉,“既然你非要送我回去,那就送吧,幫我打個掩護,謝謝。”
突然,臉上是笑意僵住,即使是在黑夜中,溫言之也發現了的異常,“怎麼了?”
Advertisement
阿楚并未說話,弓著子,氣一些,似乎在抑著什麼,朝著溫言之擺了擺手,“沒……沒事……扶我……一下……”
阿楚了幾口氣,最后長長呼出一口氣,這才緩過來,“剛剛覺很奇怪,里好像有另一個意識蘇醒。”
“言然?”溫言之眼神亮了亮。
“應該是。”阿楚點點頭,“不過你別高興地太早,我出來可以隨意,可回去就沒那麼簡單了。需要撞擊或者強大的外力才能讓出來。”
撞擊或者外力?
溫言之突然想到了騎馬那一次,顧言然從馬上摔了下來,頭撞擊到了旁邊的護欄,這才從劉楚佩又變回了顧言然。
“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阿楚攤攤手,“我是上帝視角,很多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不過告訴對沒有好,我也就不說了——”
突然阿楚的被捂住,“唔——”阿楚拼命掙他的大手。
他這又是要干嘛!
“噓——別說話……”溫言之也低了聲音,將阿楚拉到了樹林后面,“有人。”
阿楚意識到事嚴重,立馬閉上,將手電關閉,跟著溫言之一起躲進了樹叢后面。
可是聽了半天本沒有一靜,阿楚皺眉,溫言之又在搞什麼幺蛾子,剛剛探出腦袋,又立馬收了回來。
了眼睛,以為自己看花了眼,再往前看去,又回頭看了溫言之一眼,與他對視后阿楚確認,自己沒有看錯。
前面真的有人,是一個白子,長發及腰,要不是阿楚的心里素質強大,換作隨便一個生,怕是早就嚇得尖了,乍一看,真的是太滲人了。
只見那個子匆匆往這邊走過來,后似乎還跟著另外一個男子。
Advertisement
兩人沒有打燈,看樣子就知道,他們倆出現在這里,很不尋常。
天太過黑,顧言然有夜盲,導致阿楚的夜視能力也極差,看過去,只能憑借著月,看見是一男一,別的就再也看不出什麼了。
但避開視力不好的缺點,耳朵可好使了。
那邊傳來的對話阿楚一字不落地聽了進去。
“人呢?我剛剛還看見燈了。”男子的聲音中有一些急切。
“噓……聲音輕一點,他們或許是發現了我們也不一定。”子刻意低著聲音,但是這一點聲響在寂靜的山中還是十分清晰。
“不會吧,我們可是半路跟著的,他們本不知道啊。”男子疑道。
“顧言然知道我來了。”聲突然停住,往四周去。
的眼神往阿楚與溫言之所在方向掃來的時候,阿楚下意識將子往后了一。
真的是,劉楚玉來了!看來本不死心,一直在墓外面,等著出來。
劉楚玉似乎一直都知道的行蹤,不管是來南京,去了溫家老宅,還是回了東城,劉楚玉似乎總是能知道在做什麼。
這才是讓最煩的,永遠都是劉楚玉在暗,在明,這讓很被,除去這個不說,不管是顧言然還是劉楚佩又或是,就連劉楚玉現世的模樣都不知道,找個人比登天還難。
阿楚聽前面的似乎沒有了靜,緩緩移出子,想要去看那個子的臉。
剛剛將子探出一點點,突然有一道力將拉了回來。
幾乎在同時,一束打了過來,好巧不巧,恰好就打在剛剛阿楚探出子的地方。
阿楚嚇得心跳都要停了,屏氣凝神,發現腳步聲越來越近。
太過于寂靜的山林,輕緩的腳步聲都讓覺得十分詭異,阿楚靠在溫言之懷里,都覺得溫言之的心跳聲音都太響了。
Advertisement
“他們會不會已經往山下跑了?”男子的聲音突然打破了寂靜,“我們要不要去山下看看。”
“怕什麼,他們車還在那呢。”子哼了一聲,“不過顧言然那人小聰明多,溫言之那人心思深,我們還是多一個心眼是好。”停住自己的腳步,“算了,深山野林的,他們也待不了多久,我們去口等他們,他們總會來的。”
說吧子便往山下走去,男子隨其后。
等十分鐘后,完全沒了聲響,溫言之才放開。
阿楚大口著氣,拼命呼吸著新鮮的空氣,真是憋死了。
“來找你的?”溫言之看著阿楚,見松了口氣,問道。
“難道不是來找你的?你剛剛沒聽到說了你名字嗎?”阿楚撇撇,雖然知道那是劉楚玉,但是這件事,沒準備告訴溫言之,所以一直科打諢。
“是你認識,還是顧言然認識?”溫言之察覺到阿楚在逃避的問題,他一把抓住的手,“說清楚再走。”剛剛發生的事就讓他覺到這似乎是個患。
“都認識,行不行。”阿楚甩開他的手。
“是誰?”
阿楚氣急,“我也不知道啊!”要是知道是誰,早就沖過去打了,就是因為不知道才小心謹慎啊。
算了算了,溫言之不了解實,不知者無罪。
溫言之看著阿楚眼神帶著一探究和狐疑。
“我真不知道!只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但是不知道是誰,今天是第一次那麼近見到,但是天太黑了我本看不清臉。”阿楚有些氣惱,今天是本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又這麼生生給浪費了。
“你這表是什麼意思?”阿楚看著溫言之的臉似乎有些不好。
“我好像在哪里聽到過剛剛的聲音……”
“哪個?男的的?”
“的。”
阿楚撇撇,戲謔道:“怎麼?不會是你老相好吧!”話音剛落,阿楚就見溫言之臉一變。
震驚,“不會……真的被我說中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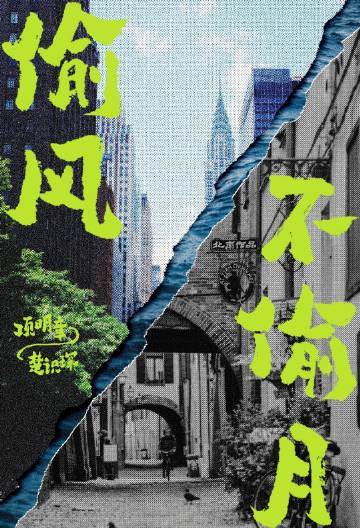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70 章

離婚后,秦少夜夜誘哄求復合
薄棠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她暗戀了秦硯初八年。得知自己能嫁給他時,薄棠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他的情人發來一張照片秦硯初出軌了。 薄棠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秦硯初不愛她。 他身邊有小情人,心底有不可觸碰的白月光,而她們統統都比她珍貴。 恍然醒悟的薄棠懷著身孕,決然丟下一封離婚協議書。 “秦硯初,恭喜你自由了,以后你想愛就愛誰,恕我不再奉陪!” 男人卻開始對她死纏爛打,深情挽留,“棠棠,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她給了,下場是她差點在雪地里流產身亡,秦硯初卻抱著白月光轉身離開。 薄棠的心終于死了,死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
30.6萬字8 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