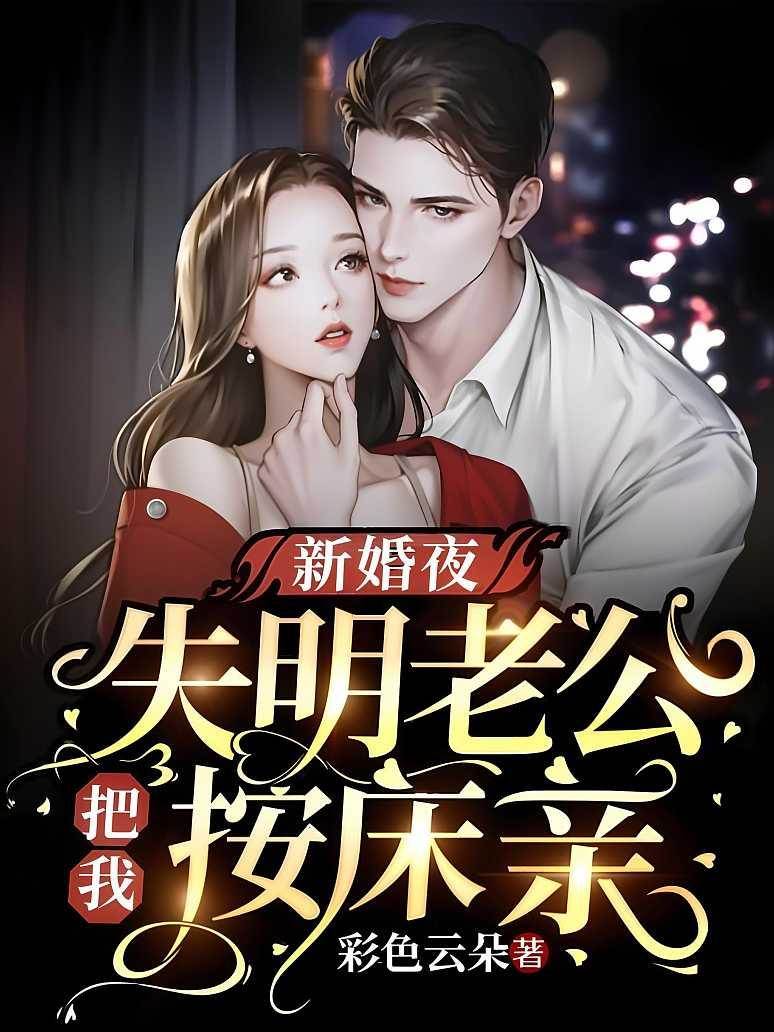《囚她》 第122章(2)
“那是漕運司和鹽院那班蠻人。”
況苑笑道:“小人眼拙,要我說市舶司,能認真為民辦事的,也識得大人一個,吏治清明,高升指日可待。”
張優笑道:“承你吉言,承你吉言。”
況苑冷眼瞧張優得意之相,嘆了口氣:“還是大人有福氣,裏外無一不順心,家有妻,外有紅,著實令人羨慕。”
男人說起人,自然是滔滔不絕,況苑和他纏了半日,灌了半壇子酒,瞧他已有八九分醉意,正要趁機探問一下張家對杜若和蔻蔻之意。
“就算大人先頭那位妻子,也是賢良,聽說求娶的人不,只是礙著大人,不敢造次。”
“?什麽兒,我張優哪有什麽狗屁兒。”張優臉通紅,舌頭打結,“沒有,沒有。”
“大人不是有個兒,小名蔻蔻的麽?我聽人說起……”
張優撇撇:“哈,你說那小雜種……”
況苑頓手,執著酒盞:“張大哥何出此言。”
“我連那賤婦手指頭都沒過。”張優胡咧咧說話,“哼,也不知跟哪個野男人生的野種,栽在我張優頭上,讓我張優當了個大王八。”他滿臉漲得通紅,“這母有一日落到我手裏……我呸……早晚讓他們生不如死……”
況苑臉如寒冰,慢慢站起來:“大人此言可當真?”
“當真……如何不真。”
張優喝得爛醉,只想在椅上躺下睡了,去被況苑扯著翻來覆去盤問,最後實在不耐煩,趴在桌上打起盹來。
若張優酒後吐真言,蔻蔻不是張優的孩子……那就是他……的兒。
他況苑的兒。
他匆匆出了酒樓,腳下不停,只有一個念想,去了杜若家看看。
人早就睡下了,滿屋子都黑漆漆的,院門栓得牢固,他也不知從哪裏來的一把子力氣,撐著高牆,一挪騰,翻進了屋子:“杜若,杜若,你出來!”
Advertisement
杜若和婢聽見門外男人喧嘩,不知多驚嚇,再一細聽,是況苑的聲音,這才心稍安。
“你出去把這個瘋子打發走。”杜若點燈起來,打發婢出去應付,“快讓他走,別喊了。”
婢出門去說話,直接被況苑轟走:“走開,杜若出來!”
他徑直往室去,不管不顧往裏走:“杜若,蔻蔻,蔻蔻。”
“況苑,你瘋了。”杜若迎出來,就要攔他,橫眉冷對,“你喝醉了跑來我這兒鬧事,走,快走。”
他氣籲籲,看了一眼,撥開:“讓我看看蔻蔻。”
材高大的男人直奔床帳去。
“況苑!你到底在做什麽?”
“我看看我自己的兒。”他紅著眼睛,回頭朝著大吼,“我況苑的兒。”
“你瘋了! 不是你的兒!”
“張優都對我說了!”他話語撕心裂肺。
杜若聽他所言,如一盆冰水從頭澆,釘在當地。
他見那副模樣,那臉上的神,心痛,惶恐,失落……真想昭然若揭,何用再去質疑張優醉話的真假。
蔻蔻也被外頭的靜吵醒,了眼睛,正見床帳起來,含糊喊了聲:“娘親。”
眨眨眼,糯糯的喊:“況叔叔。”
他看著玉雪可的孩子,了的發:“我吵醒蔻蔻了?好孩子……乖乖睡覺。”
醉酒的男人格外細致,學著杜若的樣子,細聲細氣哄孩子,輕輕拍著,凝視著孩子小小的一張臉,生得像母親,但又不全然的像,更不像張優那個畜生,那一雙眼,一道眉,和他一模一樣,只是孩子,天生秀氣些罷了。
蔻蔻迷迷糊糊,被他拍一拍哄一哄,竟也闔上眼,慢慢睡了。
況苑回頭,看見眼眶發紅,怔怔出神的杜若。
Advertisement
這個膽大包天的人!
他氣洶洶站在面前,一雙亮炯炯的眼盯著,眼神莫測,而後一攬臂,摟住了:“杜若!”
男人的氣息鋪天蓋地下來,掙不得,低喝:“況苑!”
男人的力道比繃的繩索還要強,語氣卻格外的溫:“懷胎和生産的時候,是不是很苦?”
咬牙,幾要落下淚來:“關你何事?”
“為什麽要生蔻蔻?為什麽要從張家出來?你心底是不是也有我?”
懷中的人在抖,在哽咽。
“你說你喝了避子湯,你說懷的是張優的孩子,只有撒謊的人才敢萬分篤定。是我的孩子,我和你,我和你的孩子。”他聲道,“老天有眼,對我不薄。”
“別這樣,況苑。”杜若低泣,“這樣對我們都好。”
“我將雪珠安頓好,再來娶你。”
他真的是醉了,仍是攀著牆頭,匆匆而來,又匆匆翻牆出去。
高枕安睡的況夫人半夜被況苑吵醒。
“母親……”況苑推門直闖況夫人屋,雙一彎,直接跪在況夫人床前,重重的磕了一個頭:“我和雪珠,非離不可,求母親全。”
況夫人看著床下的兒子,唉聲道:“你這大半夜的做什麽,非得鬧得家中犬不寧?”
“兒子不孝,兒子今日才得知,兒子在外有個孩子!”
況夫人雙眼瞪圓:“你說什麽……”
“兒子想娶的那人……母親認識,雪珠也知道。”況苑額頭磕在磚地上,“是杜若。”
“母親也知道張家事,母親也說過他家可憐。張優混賬,尋花問柳,冷落妻子,幾年前張家修園,我見屋無人,故意勾引,脅迫和我,後來懷胎,我兩人斷,離了張家、回娘家度日,我那時已有意和雪珠和離,只是一直拖到如今,母親,我心中想娶的人是杜若。”
Advertisement
況夫人指尖抖:“ 你……你這個沒人倫的混賬東西……那張家……那張家和你弟弟……你怎麽可以做這種事,這事捅出去,你讓我們況家臉往哪兒擱。”
“那是我的孩子,瞞著我,瞞著張家人,獨自一人養大。”況苑連連磕頭,“那個孩子小名蔻蔻,母親若是見了,也會喜歡,今年剛三歲,比寧寧還可些,母親,你最疼寧寧……你也疼疼我的孩子。”
“如今是自由,我亦求自由,我可娶,可嫁,只要母親肯全。”男人的額頭一片青紫,“我可以帶著們去別生活,南直隸省這麽大,總有我們一家三口的容之地。”
“一切都不是問題,一切都有解決之道,請母親助我一臂之力。”
況夫人聽見額頭撞擊磚地的聲響,看見兒子眼裏的雪亮彩。
做母親的,怎麽可能拗得過兒子。
親如母,說到底,不是親母。
況夫人獨自去見過蔻蔻一眼。
婢牽著蔻蔻出門玩耍,況夫人仔細瞧著,孩子的確玉雪可,模樣和況苑小時候,真的有幾分神似。
當年沒有人能理解杜若的行徑,孩子都有了,為何要和丈夫吵得要死要活,不顧一切要和離。
昨日母子兩人徹夜長談,況苑把杜若懷胎前後的糾葛、蔻蔻出生的年歲都細細說了,真是欷歔,一個醉那樣的人,三四年前的事,他居然也能記得如此清楚。
人心是秤,是親是疏,只看砝碼重不重。
況夫人倒戈得很快。
當年況苑親時,況家家境平平,杜家的姑娘,況家是攀不起的。
如今來看,杜若模樣段都好,配況苑綽綽有餘,何況還有個孩子。
私不是彩事,但張優和杜若鬧出的事,況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知道這是個要強的姑娘,又是和自己的兒子……就算想怪,也要先怪起自己兒子來。
要娶也不是不行,當然要穩妥的辦,杜若娘家那邊不是問題,只有張家那邊要想法子安穩住。
只是雪珠……唉……
薛雪珠知道況苑半夜鬧到了況夫人房,天明時分況苑才回了書房,額頭上還帶著傷。
況夫人出門半日,回來之後,見雪珠在邊服侍,對的態度有所轉圜,握著雪珠的手:“你這些年在我邊,也和親兒沒什麽兩樣。”
“母親厚我,這些年對我的好,雪珠都知道。”
“只是我也老了……唉……”況夫人黯然長嘆,“兒孫自有兒孫福……我管不住勸不住苑兒,心中又覺得對不住你……不過也說不定,你以後還有好的際遇呢……”
“雪珠,你若願意……以後就我一聲幹娘,我們仍當母相,如何?你的事,就是我們況家的事,我們還是一家人。”
薛雪珠擡起頭來,目盈盈,了角,溫婉一笑,只是這微笑未免沾了些苦意:“好。”
的丈夫終歸還是說了婆母,說了所有人。
有一筆不菲的補償,父母兄弟都接了這個現狀,為之勞的婆家也拱手想讓走。
一個男人為做到這個份上……有什麽不知足的。
無須親自手打點,況家,殷勤將當年的嫁妝、這些年的日常用、使喚的婢都準備妥當,的丈夫一日周全甚于一日,的婆母每日噓寒問暖,甚至的父母兄弟都被邀上門來,來點檢照應的生活。
只需要點頭。
和離文書準備得很妥帖。
離開前,想再陪著婆母丈夫去寺裏上香祈福,願佛祖保佑,家人皆好。
只是沒想到……這炷香其實與全然無關。
回程的馬車上只有和婢,婆母和丈夫還留在了寺裏,要替生産的苗兒請一封平安符。
過了今夜,就徹底退出了況家。
“回去,我也要替自己求道符。”
年輕的素婦人抱著個稚兒下了馬車,一大一小兩人進了寺廟。
悄悄跟著們走,心裏亮如明鏡。
的丈夫從寶殿出來,容煥發朝們走去,有許多年不曾看見他這樣燦爛的笑容。
他把孩子抱在手裏,親昵啄了啄孩子的額頭,低頭和婦人說話,那婦人蹙起細眉,爭辯了兩句,甩袖想走,被他牽住,心平氣和說了兩句。
三個人站在了一,孩子在笑,大人在吵,卻是和睦之家。
他們在等人。
的婆母跟著禪師出了殿門,在殿門前了青天,噓了口氣,將手裏的如意符塞進了大袖裏。
知道婆母的習慣,知道這是求過了禪師,求得了一張上好的闔家福簽。
年長的婦人走向了那一家三口。
他們站在一說話,的丈夫將年輕婦人和孩子都推到婆母面前說話,的婆母板著面孔,卻手了那稚兒的發髻,而後從懷裏掏出一件東西,仔細套在了孩子的藕節般的手腕上。
知道那是什麽。
那是婆母家傳下來的古,是傳給子孫輩的銀鐲。
年輕婦人抱著孩子在婆母面前連連落淚。
的丈夫當著自己母親的面,溫摟住了年輕婦人。
的婆母換了一副慈的神,眼裏含著笑意,手去抱年的孩子。
沒有人激一個人十年的勞苦,就連那些溫的話背後都是虛假意。
在丈夫眼裏,只是個無趣的妻子,在婆母眼裏,只是個任勞任怨的兒媳。
一個骯髒的男人和一個無恥的人,竟然會有個圓滿的結局。
綠葉之下有一雙寧靜的眼一閃而過。
況苑好不容易勸杜若,帶著蔻蔻見了況夫人一面。
自從知道蔻蔻是他的兒,他是真的等不及,恨不得一家三口長相廝守。
只是一切還需要從長計議,但已可以預見未來的曙。
家裏已經收拾得妥當,雪珠執了幾年中饋,家中每一項都清清爽爽,各房的鑰匙、賬目、人往來都還給了況夫人,的東西也收拾得妥當,明日一早,薛家大舅子會來將自家妹子接回薛家。
“雪珠在我們家這麽多年……我知道舍不得走,也最不想虧待。”況夫人嘆道,“最後一夜,你們夫妻兩人好好說說話,你也給拿拿主意,以後再嫁,或是如何,我們況家也要出一份力,別把這份生分了。”
“這是自然,母親放心。”
況苑是帶著滿懷歉意回了自己屋子,他的妻子也在屋等他。
“我知道你今晚會過來和我說幾句話。”微笑,“夫妻十載,過了今日,就要各奔東西。”
冷清自持的妻子今日有些灑的意味。
“這些年,過得很辛苦吧?”替他斟茶,淡聲道,“我沒有當一個稱職的妻子。”
“是我對不起你,讓你辛苦。”他誠懇道,“耽誤了這麽些年。”
如今想起來,何必耽誤彼此這麽多年,合則聚,不合則散,拖拖拉拉反倒傷人傷己。
雪珠把茶盞遞給他,和的眸子裏有堅毅:“以茶代酒,夫君不若和我對飲一杯。”
“十年前,我嫁進來的時候,你知道我不能飲酒,你就斟了一杯茶水,以茶代酒,就這麽喝了合巹酒。”和笑道,“現在想起來,那畫面依然在眼前,久久不忘。”
溫婉的人巍巍舉起茶盞,手中如有千金,看著眼前的男人,將一杯茶水仰頭倒口中。
他也朝妻子舉杯致敬,低頭啜了半盞茶,只覺茶味不對,再擡眼看雪珠,只見目閃爍盯著自己,溫一笑:“怎麽,味道不對麽?”
這茶又苦又辣,如幹柴。
“這茶……”
雪珠不說話,只神莫測看著他,笑容有幾分詭異。
況苑兀然皺眉,咳了一聲:“你……”
裏早已疼得五髒,面上卻是毫不顯,平靜淡定,只有漸漸赤紅的臉才昭顯出一點異常,雪珠咧一笑,剛想說話,猩紅的已經從嚨湧到裏,浸潤了潔白的牙齒,顯得猙獰又可怕。
“夫君……你不可以這樣對我。”
作為一個妻子,毫無保留獻出了自己的所有。
冷清不是的錯,的家教向來讓如此,是野的他讀不懂的心。
冷淡不是的罪,已盡力去接男歡,也縱容丈夫出去尋歡作樂,甚至還為他納妾,卻一直不能讓他滿意。
沒有孩子不是的錯,為此吃盡苦頭,甚至願意養別
猜你喜歡
-
完結962 章

重生後我成了護夫狂魔
前世,雲七念太作,直接把自己給作死了!重活一次,看著眼前帥得讓人神魂顛倒的老公,她隻想喊:寵他!寵他!寵他!老公喜歡什麼?買!老公被人欺負?打!老公要她親親抱抱舉高高?冇問題!老公說要再生個猴子,雲七念:……???什麼叫再?直到有一天,一個Q版的軟萌小包子出現在她麵前,她才明白一切。從此以後,誓要更加寵他,愛他,珍惜他!
86.7萬字8 66386 -
完結94 章

先婚后甜
商界大佬沈浩煜,家世顯赫,長相英俊,是眾多上流名媛的擇偶目標,可惜他性情冷淡,無人能撩動,眾人都等著看什麼樣的女人能讓他俯首。沒想到他在家人的安排下和顏家二小姐顏歡結了婚,聽說沈浩煜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是被家里長輩逼著結婚的,夫妻性格不合,…
33.3萬字8.18 56306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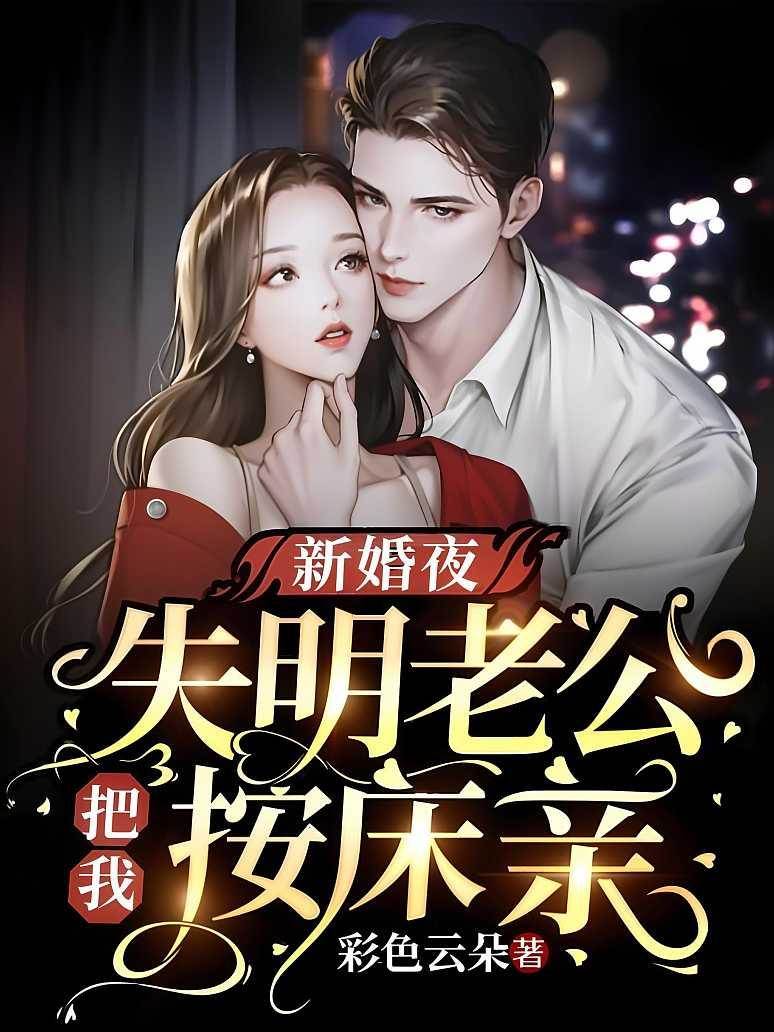
新婚夜,失明老公把我按床親
鄉下的她剛被接回來,就被繼母威脅替嫁。 替嫁對象還是一個瞎了眼的廢材?! 村姑配瞎子,兩人成了豪門眾人笑柄。 她沒想到,那個眼瞎廢材老公不僅不瞎,還是個行走的提款機。 她前腳剛搞垮娘家,后腳婆家也跟著倒閉了,連小馬甲也被扒了精光。 她被霸總老公抵在墻上,“夫人,你還有什麼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她搖了搖頭,“沒了,真的沒了!” 隨即老公柔弱的倒在她懷中,“夫人,公司倒閉了,求包養!” 她:“……”
24.7萬字8 14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