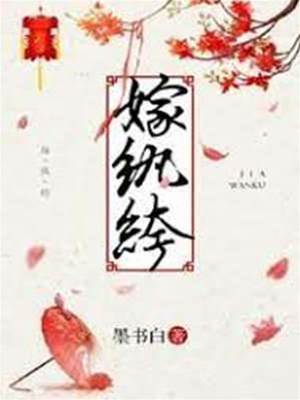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3卷 第一百一十章“扒了衣裳,雨里跪著。”
雨打在建章宮的重檐瓦當之上,殿香氣繚繞,燭火搖曳不止。
許之洐醉了酒,暈暈沉沉地臥在塌上,只看見面容模糊的姜姒態,正溫順地跪在一側顧盼生姿。
他已經許久沒見過這般溫順的姜姒了,他輕嘆一聲,“阿姒呀。”
那子嫣然笑著,一雙纖纖素手輕地解下他的錦袍。他那副醉玉頹山的模樣,實在令人臉紅心跳。
他本便是絕代風華的人。
子又開始褪去自己的華袍,出曼妙有致的腰來。他迷離地瞧著,捉住一雙荑,翻將在下,的眉眼含靈,段也是千百。若是沒有記錯,在隴西時是把心都付了他的。
“你還在生我的氣麼?”
他喃喃道,“你實在狠心,竟全把我忘了。”
他的覆了上來,“我不該不信你,不該罰你,我已知錯了。”
榻上的子/玉溫香,聲和婉,“我沒有忘記殿下,我心里一直著殿下。”
想來人若醉了酒,當真容易傷心,此時他眸中竟垂下淚來,“阿姒,你不許再離開我了。”
榻上的人婉轉迎合,綽態,“殿下,我永遠都是你的......”
那婉曼的長聲還沒傳出來便被越發大起來的雷聲雨聲沒了去。
他極了這子,但他已經許久不曾過了。
他手探向的腰間,那里平細,沒有朱雀印。但他酒意上來,只是昏昏沉沉的,也并未察覺出有何不妥來。
那子也了,極力哄著他。也不知過去多久他乏極了便昏睡過去,及至夜半時分,許之洐醒來,頭疼得似是要炸開一般。
以往他的酒量甚佳,不想白日里宴飲竟然在眾人面前醉倒。他扶著額好一會兒才清醒了來,披了袍子方要下榻,卻見旁的子只著了一層單薄的春衫,里竟寸縷不著,此刻正臥在一側酣睡。
Advertisement
那子眉眼如畫,與姜姒有五分相像,定睛看去,竟是長安來的蘇采。
許之洐眉頭一蹙,方才夜時分的纏綿一幕幕地閃進了他的腦中。
他竟將當作了姜姒。
正要起怒,一時想到蘇采的份,便又極力制了下來。
這是許鶴儀送過來的人。
許之洐輕笑一聲,自顧離開了建章宮,卻見外面下起了雨來,雷聲隆隆作響,不知道那飽了一雨季寒困擾的人此刻是否安好。
廊下候著的周叔離此刻上前來,“夜已深了,殿下還要回長信殿嗎?”
許之洐睥睨了他一眼,“你啊,終究不如伯贏懂我。”
周叔離不知是何緣故,只是試探說道,“還請殿下明示......”
許之洐道,“不清不楚的人,你也敢放縱爬上我的床榻麼?”
周叔離心里咯噔一聲,訥訥道,“末將只以為......末將不如伯將軍。”
“哪里有什麼伯將軍?”他嗤笑道,“不過是個馬夫罷了。”
話音剛落,他便抬步往臺階下走去,那夜里的雨涼意瑟瑟,毫無遮擋地打在上。周叔離趕忙撐開傘追了上來,再不敢多說什麼話。
伯贏是一直跟在燕王旁,已有十多年了,深知燕王的心思脾氣,一朝犯了錯被罰作長樂殿的馬夫。而他周叔離也不過是因伯贏被罰,許之洐邊暫時無人罷了,才有幸補了這個缺兒,哪里能揣得了燕王的心思。
長樂殿那邊傳來狗的吠聲,想來是那只獒犬挨了淋。
雨大路,周叔離小心地為許之洐撐著傘,卻又不見他回長信殿,反而冒著雨往長樂殿走去。也不知想起什麼,命道,“把那只狗放了,省得覺得我心狠。”
周叔離忙應下了,將許之洐送至廊下暫避著雨,又趕忙去打開了狗籠。那吠吠連日來被關在籠中,憋屈極了,此時鉆出籠子,瘋狂甩了甩滿的雨水便沖殿外跑去。
Advertisement
周叔離被甩了一的水,回了廊下問道,“殿下,可要去追?”
許之洐邊抿開一抹淡淡的笑意,“不必,宮門落了鎖,它能跑到哪里去。”
周叔離便候在一側靜等他的吩咐,不久聽他道,“回長信殿,備好艾草。”
定然寒發作,必要這艾草熏蒸了才能緩解。
周叔離應著,此刻自己全都了,原以為送他回了長信殿便能歇下換干凈裳,誰知道這一夜就沒有再消停下來。
*
表小姐不見了。
伯贏與白芙跪伏在廊下,噤若寒蟬。
許之洐心知不好,踹開殿門往殿走去,長信殿燭輕晃,一個人影也無。
“去哪兒了?”
白芙跪在地上瑟瑟不敢抬頭,聲音打著兒,“殿下恕罪,奴婢不知。”
他便轉去踢伯贏,“為何不報!”
伯贏亦是伏在地上不敢言語。
“說!”許之洐此時已然怒極了,眉眼之間鷙頓生,抬起腳來便將伯贏踹翻。
伯贏倒在地上,即刻復跪下來,“殿下息怒,宴飲時分,表小姐便不見了。奴本想稟告殿下,只是見殿下已醉,又有家人子相伴,便不敢再驚擾。”
許之洐聞言怔了一瞬,渾仿佛豎起一道堅冰,繼而越發冷漠,“伯贏,站起來。”
伯贏依言立起,但見許之洐一掌將他扇倒在臺階上,又順著那高高的臺基往下滾去。
“白芙。”
他低沉冷的聲音在這雨夜里愈發涼薄駭人,白芙頭皮發麻,惶恐哭道,“殿下贖罪!”
“了裳,雨里跪著。”
白芙愕然抬頭看他,殿的斜斜打在他剛毅的臉上,半張臉冷絕無,半張臉晦暗不明。撲過去抱住許之洐的,竭力哀求,“殿下!看在奴婢侍奉多年的份兒上,饒恕奴婢吧!殿下!奴婢心里全是殿下,殿下若要這樣懲戒,奴婢不如去死!”
Advertisement
“那你便去死!”他一腳踢開,繼而勾冷笑,“你如此惜命,竟會舍得去死嗎?”
白芙摔在地上,愣愣地看著他。
他的命令,除了姜姒,向來沒有什麼轉圜的余地。
見他冷冷地瞧著自己,滿眼都是鄙夷。白芙怔忪地站起,口中喃喃道,“奴婢領罪。”一邊已解了腰間绦、褪了長袍往雨里走去。
走進雨里,那瓢潑的雨水當頭澆下,再分不清流了滿臉的究竟是雨還是眼淚。
褪了外袍,亦褪了里袍,只余下抱腹與襯,撲通一下跪進了積水里。
在這一刻,才真正會到姜姒曾經的畏懼與絕。再忍不住,垂頭痛哭起來。
“還發什麼愣。”
許之洐幽冷的聲音乍然響起,周叔離這才回過神來,忙應道,“末將這便帶人全城搜尋表小姐!”
他疾步下了臺基,見伯嬴一的水躺在高高的臺基之下,不知是否還醒著。
曾經風驕傲的冷面將軍伯嬴,如今竟淪落到這般地步,實在令人脊背發寒。
周叔離不敢再去想去看,他穿過重重的雨幕往大殿外走去。若尋不到表小姐,只怕自己也是一樣的結果。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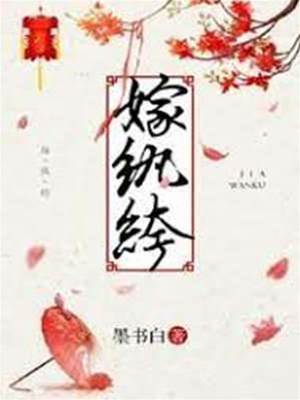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