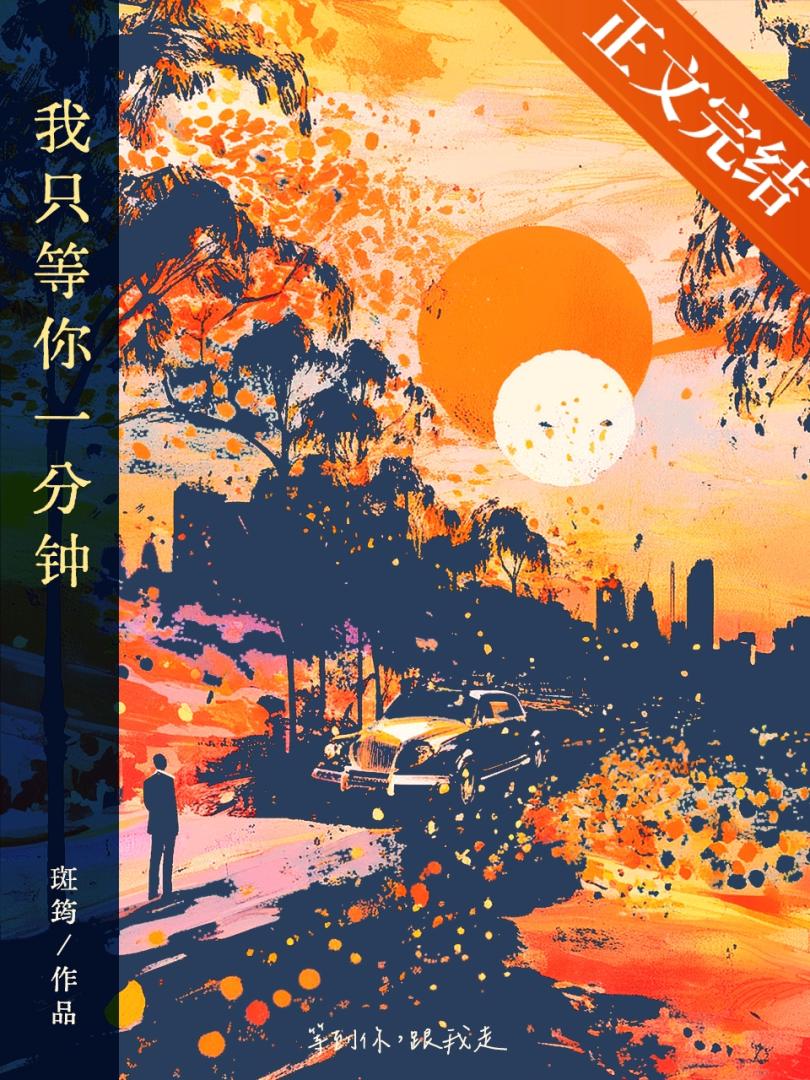《不小心和男神靈魂互換了》 第五章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五)
再醒來時已是早晨,單鷹起,猛地一怔,這周遭布置分明不是他家,再一看披散雙肩的長發,明白過來,多日不曾出現的互換,又毫無預兆地來了。
他掀開黃的絨被,打開臥室門,迎面遇上正在刷牙的馮奕國。
“你多大的人了?服穿好再出來,像什麼樣子!”馮奕國不滿地說,牙膏泡沫噴。
單鷹低頭一看,前隆起,十分尷尬,馬上退了回去,在床邊的靠背椅上找到馮牧早昨晚下的和家居棉服外套穿上,再出去時,馮奕國已經洗漱好了,一邊用巾臉一邊使喚兒——
“難得啊,周末從沒見你起這麼早過。我出去買菜,你到文印店幫我把橫幅拿回來掛店里去,讓走過路過的人都知道咱們要上電視了。”
“您是……我爸?”單鷹試探著問,無奈他現在頂著馮牧早的臉,這個表讓“”看起來智商堪憂。
馮奕國呆住了,還手去“兒”的額頭,確定沒發燒:“別添,滾滾滾~”他揮揮手,“我再不去菜場,好魚好都給人挑走了。”
單鷹轉回房,在枕頭旁找到馮牧早的手機,撥了一個電話給自己。
沒接。
撥了三個,都無人接聽。
馮奕國說得沒錯,一周只休一天的馮牧早不睡到十點不罷休,此時正夢見自己在游戲里養的青蛙兒子寄了一張從沒見過的明信片回來,高興得要命,但總覺得忽然有點冷,且下腹有什麼東西硌得慌,不由得有點轉醒,手想把那玩意拿開。
“夠了沒有?”
天降一個悉的聲,馮牧早猛地睜開眼,發現自己的臉出現在床邊,還披頭散發,配合著房暗暗的線,活像鬼片一樣。
“啊——”大一聲,發覺自己發出的聲音是單鷹的。
Advertisement
呆了一下,看看左右,只見被子被變馮牧早的單鷹掀開一邊,自己正“大”字形躺在床上。
馮牧早被迫蒙著眼睛換服,他則站一旁監督。不得不說,對面那個“單鷹”捂著口、夾著的樣子娘到了極致,單鷹覺得,多看幾次這樣的“自己”,三觀將被徹底扭曲。
馮牧早里叨叨著:“這可怎麼辦,中午還得去店里幫忙……對了,我還要去拿橫幅,下個月我跟我爸要上電視了。”
說起上電視,和馮奕國兩位小老百姓都顯得很興。
“什麼節目?”單鷹推開帽間的隔門,帶著馮牧早進去。
得意地賣關子:“你猜?”
這父倆能上什麼節目?單鷹幾乎沒有思考——
“《世界》。”
馮牧早小牙一咬:“單老師你……”
“《今日說法》。”
“不對!”
“《撒貝寧時間》。”
馮牧早泄了氣,私下揣道,單鷹換到的里去的時候八心里有緒,看也格外不順眼,干脆一改平日里的不茍言笑,放飛自我一個勁兒懟來泄憤,如果跟他換的是超級巨星或者世界首富,他可能就平心靜氣面對現實了,就像現在一樣。
他找出今天要穿的,一件件按順序排好,回頭見還梗在那里,就給了個臺階:“正確答案是什麼?”
有氣無力地公布:“《民間廚神爭霸》。”
“哦。”即便差點被甄選為此節目的評委之一,他依舊反應平平。
馮牧早換好單鷹挑的服,站在鏡子前,不被眼前撲面而來的英俊之氣給驚住。再看看一旁的“馮牧早”,大吃一驚,道:“你……你穿的什麼?”
現在才發現,他在的家居棉服外直接套了件黑長款羽絨服就出來了,遠遠看去就像一只企鵝。
Advertisement
他冷地斜睨:“這麼說,你希我按照自己的習慣,先洗個澡,再換上你平日出門的全套裝備過來你起床?”
馮牧早半張著,被他這句話堵得無話可說,只能雙手合十:“謝謝你的正直。”
因互換,單鷹不得不跟著馮牧早去往文印店拿橫幅,又以馮牧早的份去大排檔。
“那就是我家的店。”馮牧早站在街對面,指著前方說。
單鷹順著指的方向,辨認了好一會兒,眉頭不了一下:“賣國大排檔——這種反的字號,工商局允許注冊?”
“奕國!”馮牧早糾正。
到了店里,馮牧早卻不知要以什麼份進去,想了半天,忽然清清嗓子:“老板,我是文印店幫忙掛橫幅的。”
“來了來了。”馮奕國跑出來:“掛店門口。”
“哇!帥哥你誰啊?以前都沒見過……”
“你穿西裝來掛橫幅哦?好講究!”
“要不要我幫忙扶著梯子?”
阿珍等人像蜂見了花一樣圍過去,馮牧早言又止,只能嘆口氣,任太和阿珍把自己扶上梯子還借機在帥哥的屁上揩了油,只有小稍微矜持些,不敢這麼放肆。
單鷹站在店外五米,冷眼旁觀兩個半老徐娘對自己的上下其手,心里有多只羊駝狂奔而過,開始懷疑明家父倆開的到底是不是正經的飲食店。
馮牧早把橫幅掛好后,他抬眼看了看——
熱烈祝賀奕國大排檔參加《民間廚神爭霸》取得圓滿功!
語病多多不說,小市民的嘚瑟氣一覽無余。
“謝謝啊……”見前來幫忙掛橫幅的“小工”從梯子上下來,馮奕國掏出煙盒就要遞煙。
“不用了,我……我先走了。”馮牧早心里滿是“相見不相識”的苦楚,默默轉離去。見單鷹也打算走人,趕住:“單老師,你去哪?”
Advertisement
“我下午有個會。”
“今天……不是放假嗎?”
“深度調查部周五休,希你盡快適應一下。”
“咦?我為什麼要適應?”
“以防萬一,你還是到調查部來。”
那不是每天都會見到他了?馮牧早心里小小雀躍了一下,更多的擔憂卻翻涌上來。講真,調查記者這行當是很危險的,能應付嗎?況且,還可能時不時就跟他來個乾坤大挪移,怕就怕,被他曝的不良分子要報復的是他,罪的是自己。
“可你頂著我的臉,怎麼去給他們開會啊?”憂傷地著他。
“小早!別看人家長得帥就拼命搭訕!”二在店門口扯著嗓子喊,“干爸你幫忙打包!”
馮牧早一看表,十一點多了,午間食客和外賣的高峰期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換回來,馮牧早斗膽開口道:“要不這樣,我替你去開會,你……”
“想都別想。”單鷹瞬間黑臉,“我不允許你用這麼娘的語氣和作跟他們說話。”
“大家都說深度調查部氣氛太嚴肅了,偶爾換個風格不是也好的麼?”
他冷笑:“你想上一次《撒貝寧時間》嗎?”
跟單鷹鋒次數不多,馮牧早還有點不適應他的節奏:“又不是綜藝,我去能上哪個角?”
“所有警察和法醫都圍著你轉的那個角。”
馮牧早聽懂了,這是以命威脅啊!扁了扁:“那怎麼辦?”
單鷹瞥一眼:“替我開會,所有出口的話按我教你的說。走。”
“等等!”
“還有什麼問題?”
“你能不能換一套服?”指著黑羽絨服——那是幾年前的老款了,且有那麼點中風,被塞在櫥最里頭,結果單鷹用他強大的直男審直接給翻出來套上就出門。
Advertisement
單鷹想了想,同意了。
馮牧早掩人耳目帶著單鷹去了自己家,想到還沒吃午飯,就打包兩份盒飯一并拎上去。
櫥里翻了一會兒,找出條巾,玩捉迷藏似的把單鷹的眼睛蒙住,先掉那些七八糟的,再給自己的換上所有該穿的服。
偏偏,他們換服的地方正對馮牧早的全鏡,無意中往那邊一瞟,倒吸一口氣——鏡子里的場景分明是,馮牧早被蒙著眼睛,單鷹西裝筆站在邊,一件一件把服掉。
這跟看小電影有什麼區別?況且,主角還是自己!簡直不要太香艷!
不淡定了。
“你穿不穿?”許是遭遇了太久的停頓,單鷹不滿地問。
“穿!”馮牧早紅了臉,一下子扣上的搭扣,“那個……單老師,你彎腰一下。”
“為什麼?”
“整理整理。”
“穿好了還有什麼好整理的?”
“單老師,你不懂……”馮牧早不知怎麼跟他解釋人的不是穿上去就行的。
反正是的,想什麼弄就怎麼弄,單鷹也不再過問。
見單鷹稍彎腰下去,馮牧早站在他后調整了一下,他忽然發出一聲輕笑,說了句“原來如此”。
馮牧早很尷尬,不又看了鏡子一眼,里頭的場面簡直不堪目了。
穿好其他后,單鷹扯掉擋住眼睛的巾,許是嫌手腳太慢,一邊穿外套一邊不悅地瞥。
忽然,他見了一個不該出現的異狀,嚴厲地指著問:“你剛剛想了些什麼?”
“嗯?”馮牧早呆愣愣順著他指的方向往下一看,失神了幾秒,回想起自己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單鷹的那天……
“單老師,著名的詩人泰戈爾曾經曰過——遇見另一個自己,有些瞬間無法把握。”尬辯道。
單鷹以冷笑進行無地嘲諷。
“吃飯吧吃飯吧……”馮牧早一邊往客廳逃竄一邊悲傷地想,換回去后,單鷹估計理都不想理了……
單鷹來到客廳,見已拆了一份外賣狼吞虎咽,想到自己自從得知何遇死訊后就嘗不出任何味道,不問:“吃得下?”
“很好吃啊。”馮牧早不敢看他,只能埋頭苦干。
單鷹坐在對面,陷沉思。醫院的檢查顯示他的沒有任何異常,使用他的馮牧早能嘗出味道,看來醫生推測的沒錯,他味覺的喪失是心理因素。
一開始,他確實看過許多次心理醫生,近兩年放棄了。他覺得,如果味覺是何遇離去時從他上帶走的東西,那麼他甘愿用味覺與陪葬。
“單老師,你吃啊。”馮牧早吃了大半,才想起招呼他來。
單鷹拆了餐,掀開餐盒的蓋子。這幾年,他吃什麼都猶如嚼蠟,喝什麼都像白開水,淡而無味,真正會到什麼“有的人吃飯是為了活著”。
隨意吃了一口,依舊淡而無味。
他角輕輕揚了一揚,自嘲的笑意中泛著細若蠶的苦。
許是想起汪姐說單鷹沒有味覺的八卦,馮牧早抬眼看了看他。他修養很好,一份廉價的外賣也吃得優雅,看不出到底嘗不嘗得到味道。
“需要辣醬嗎?”試探地問。
單鷹不知心里的小九九,既然沒有味覺,當然來者不拒:“隨便。”
跳起來,從冰箱拿了那罐自己從來不敢嘗試的辣醬出來——那是馮奕國用國辣度最高的辣椒炒制的變態辣醬,用他的話說就是:辣得可以著火。
慷慨地舀了一大勺給他,撒了個小謊:“微辣,我平時都拌飯吃。”
單鷹不疑有他,用筷子挑了一些口。
馮牧早瞪大眼睛,期待地看著他。
過了幾秒后,他察覺到不懷好意的目,幽幽回。沒有味覺不代表沒有痛覺,間的痛讓他有所頓悟——這辣醬絕不是“微辣”的水平。
見他有所發覺卻毫無反應的樣子,馮牧早心想,汪姐的八卦八是真的,他確實沒有味覺。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分手後我懷了大佬的崽
褚雲降和路闊最終以分手收場,所有人都嘲笑她是麻雀想飛上枝頭。幾年後,她帶著兒子歸來。見到路闊,隻是淡漠地喚他一聲:“路先生。”那一刻,風流數載的路闊沒忍住紅了眼圈,啞聲道:“誰要隻做路先生。”
24.9萬字8 25546 -
完結830 章

裴少寵妻成癮
“喜歡我,愛我,眼睛隻許看我!”男人咬著她的唇,霸道宣告。為了讓她留下,不惜逼她懷孕產子。“裴慕白,你就是個瘋子!”她嘔盡最後一滴血,硬生生割裂了和他所有的聯係,他崩潰嚎啕卻於事無補。多年後她於人海中出現,長發及腰笑得妖嬈。“好久不見,裴總,有沒有興趣一起生個孩子?”男人咬牙切齒:“我倒缺個女兒,你感興趣嗎?”
150.7萬字8 4190 -
連載778 章

二嫁頂級豪門,婁二爺悠著點腰啊
領證的路上,言茹茵遭遇車禍,昏迷了三年。再次醒來,丈夫因車禍失憶,怪她惡毒,說她棄他不顧,身邊已另有新歡。 言茹茵對這種眼盲心瞎的男人沒有挽回,離完婚扭頭會所偶遇一個寬肩窄腰、八塊腹肌身體好的小白臉。 小白臉又欲又野,卻不要錢要名分…… “寶貝,你快跑吧,我跟我老公還在冷靜期,這點錢你拿著,我怕他打你。” 言茹茵丟了支票就跑了,電話都沒留。 第二天,言茹茵跟冷靜期的丈夫參加婁家家宴,見到了那位傳說中神秘狠辣的婁二爺。 男人將她抵在墻角:“錢我要,人也要!都是我的。” 言茹茵驚:“二,二哥??”
136萬字8.18 95736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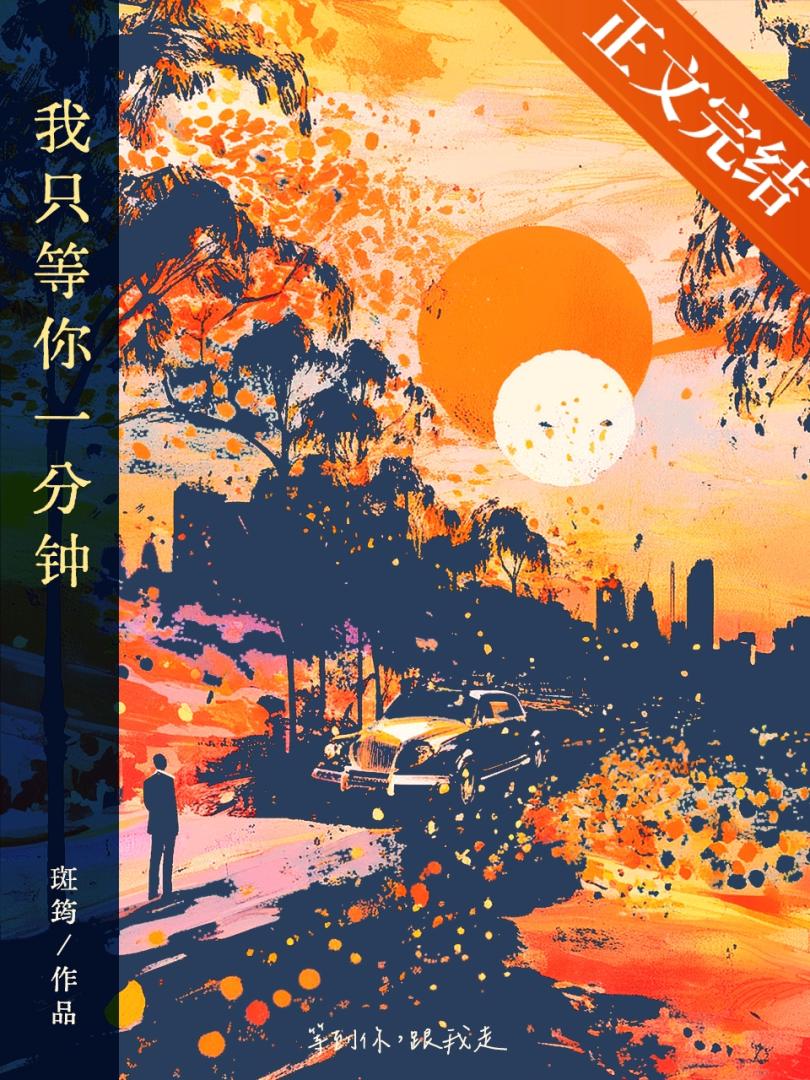
我只等你一分鐘
為躲避催婚,卿清也開始聽從母親的安排相親,意外與萬俟延相遇。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新聞報道裏的科技新貴,中國最強游戲制作人,美國海歸,同年少時大為不同。卻是一樣的氣質冷峻,淡漠疏離,仿佛任何人都無法輕易靠近。決定領證時,二人已有6年未見,卿清也稍顯猶豫。她站在民政局門口思考,還未等捋清思路,便看到有人迎面走來,臉色冷冰冰的,足足盯了她5秒鐘,才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問她:“不進來,站在門口做什麽?”這目光帶有重量,卿清也忍不住後退,忽聽他開口:“你可以現在走,走了就沒有下次了。”卿清也的腳步倏地頓在原地。緊接著,她聽到身後人語調平靜地說:“我和你,只有做夫妻和陌生人這兩道選項。”*在外人看來,這兩人一點都不搭、一點都不合適,他們的婚姻就像是兒戲,遲早要完蛋。但卿清也并不覺得,他們約好了不告訴父母,也不互相幹涉,并且萬俟延領完證就飛往國外工作,一去就是許多天。卿清也也開始忙起泥塑事業,沉醉忘我,晝夜顛倒,全然忘了自己已婚的事情。然而某天她忽然收到一條消息——【夜不歸宿?】這條尚且還讀不出那人的情緒。可間隔半小時後的下一條,萬俟延又給他發來一則消息,是一個簡單的“?”。小劇場:①某天,卿清也接到她母親的電話,徐蕙蘭氣勢洶洶地問她:“檔案上顯示你已婚,是怎麽回事?”卿清也裝傻充愣:“你聽誰說的?”徐蕙蘭:“警察。”卿清也:“假的,別信。”徐蕙蘭:“......你最好給我一個解釋。”②兩家父母來找他們討要擅自結婚的說法。卿清也把萬俟延拉到一旁商量對策,她沒想到會遇到這麽棘手的場面。還沒商量好,就見萬俟延轉身走到父母面前,隨即,卿清也聽到他說:“爸爸媽媽們。”他的態度端正,讓對面的父母們也不自覺正了正身子。卿清也走過去,坐到他身旁,打算聽聽他的解釋,下一秒,就聽他說——“我希望你們不要破壞我的婚姻。”卿清也:“......”父母們:“......”一個沒良心VS一個死心眼—————————————————————預收文文案:文案1:家裏即將破産,為幫母親分擔債務,郁芣苢答應去相親,一路猶豫不決地在酒店盡是蓮科名的包廂門前打轉,最後在“芙蓉”和“芙蕖”當中任選一間,走了進去。哪知,繞過黃花梨木嵌雲石插屏,卻看到對面露出一張矜貴清冷的臉。他正在接電話,聽聞動靜,冷冷地朝這邊掃來一眼。郁芣苢慌忙道歉:“抱歉,我走錯包廂了。”轉身就跑。薄言初本在跟母親討價還價,他不理解為什麽這樁生意非得自己來談。待看到誤入包廂的人奪門而出,薄言初趕忙起身去追。正巧,對門也同時打開,他看到“芙蓉”裏頭出來一對挽手的璧人,再看身側郁芣苢臉上露出“大事不妙”的表情,當即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想到郁芣苢當初同自己提過的分手理由,薄言初當即沉下臉來,質問她:“你來相親?”“你跟他就合適?”*搞砸相親的當晚,郁芣苢抓著手機思考該如何同母親交代,意外翻到了分手那天薄言初給她發來的消息:【你考慮清楚了嗎?】時間來自半年前。郁芣苢深思熟慮後,冷靜地給他回複:【我考慮清楚了,我答應跟你結婚。】薄言初不理解,并且很快地給她回來一個無語的“?”。*常年潛水、一言不發的薄言初,某天突然在家族群裏發了一張自己的結婚證照片。薄母先是鼓勵式地對他表示了真心的祝福和恭喜。過了三秒,意識到不對,又發來:【不是,兒子,配偶欄那裏的名字是不是不太對?】文案2:薄言初一側過臉,不看她,郁芣苢就知道他生氣了,不想搭理自己。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她就會把平日憋在心裏強忍著沒說的話沖他一頓瘋狂輸出。等到他終于忍不住皺起眉回看自己,想問她是怎麽回事之時,郁芣苢就會翻臉一樣,笑著對他說:“別生氣了嘛。”一個忘性大VS一個氣性大內容標簽:都市情有獨鐘青梅竹馬婚戀業界精英輕松卿清也萬俟延(mòqíyán)郁芣苢(fúyǐ)薄言初其它:@斑筠在流浪一句話簡介:等到你,跟我走立意:成為更好的自己
22.8萬字8 815 -
完結348 章

認錯白月光后,我慘死,他哭瘋
在向我求婚的游輪上,傅寒燚將兩億天價的鉆戒,戴在了養妹的手上。那時我才知道,這個對我謊稱得了絕癥,讓我拼死拼活為他攢錢買續命藥的男人: 竟然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金融大佬。 可他偽裝成窮人,玩弄我的真心。 他把我賣血換來的天價藥,一顆顆扔在地上,讓我被他們的上流圈子嘲諷。 他們說,窮人的真心可笑又廉價。 在生命消逝前的幾分鐘,我不甘心的打電話向他求救,他卻讓我去死。 我終于歇斯底里:“傅寒燚,明明是你隱瞞身份對我戲弄,為什麼你卻像個批判者一樣堂而皇之的踐踏我?” 他輕蔑一笑:“溫媛,等你死了,我會在你墳前告訴你。” 如他所愿,我真的死了。 可當他發現我的尸體被迫害得慘不忍睹時,整個人卻咆哮了。 再醒來,我重生在她人的身體里。 傅寒燚跪在我的墳前懺悔:媛媛,欠你的,我很快就能還了……
57.7萬字8 78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