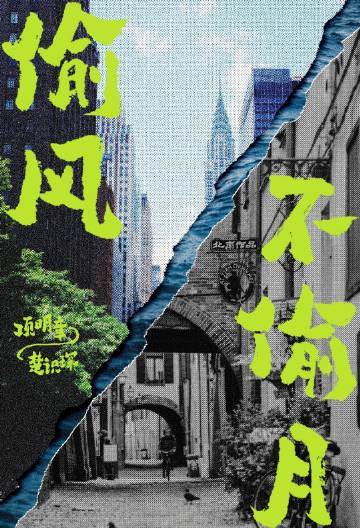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南嬌寵》 第1卷 第115章 花羽
清晨,云晚娇醒的时候觉到一丝冷意。
顾南砚抱着,将被子扯了扯,看向冷空气来源。
空调的温度很低,不解的将温度调高。
还没等问清楚怎么回事,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砚哥,嫂子,醒了吗?”
“什么事?”顾南砚问。
他刚刚醒,眉头皱着,云晚娇手抚平他的眉。
顾南砚穿上睡打开门,唐泽道:“那天送请帖的主家来了,是个的。”
听到这话,一直在床上躺着的云晚娇坐起。
“阿砚,你先去,我很快下。”
“不急。”
那天那人的口中并没有顾夫人这三个字,顾南砚始终记在心里。
他不慌不忙洗了漱,换了常服,坐在一的客厅沙发上。
齐梦欣和岑澜接收到云晚娇给们连接的监控视频,两个人坐在岑澜的房间内,一人抱了一袋薯片。
庄园外,一辆黑的法拉利停在那,穿白连的人等在门口。
十七打开庄园大门,仔仔细细打量着面前的人。
“我们二爷让你进去。”
庄园大门,到别墅大门的距离开车也需要几分钟,那人踩着高跟鞋,记恨般的看了眼十七。
“你们就这么待客?”
十七:“你看我没用,我们二爷说了,你不算客。”
话落,他从大门后拿出平衡车,踩上去,悠哉悠哉回了别墅。
回到别墅的十七笑的开怀:“你们不知道,踩着高跟鞋差点摔倒好几次!”
Advertisement
唐泽:“早知道我去把地砖松一松了。”
大概二十分钟,门口传来高跟鞋的声音,顾南砚示意十七将空调温度调低。
他们穿着长长裤,那个人进门的时候,已满头大汗。
屋内的冷空气让忍不住瑟,但很快便调整了状态。
“南二爷真是好大的架子,这么远的路,让我一个人走过来。”
顾南砚:“掌握着我的行踪,调查着我的庄园,就应该知道,我顾南砚的架子有多大。”
“南二爷说笑了,我怎么会调查你的行踪。”
长得不错,段崇靠在沙发上,将打量了一圈。
“呦,新做的头发,妆容也不错,这子不便宜吧?
打扮的这么好,倒是显得我们不怜香惜玉了。”
唐泽:“没调查?飞机落地的时候庄园外就有人守着,第二天一早就来送请帖。
这不算调查,什么算调查?难道要我说出你睡了几个男人才算调查?”
人笑了笑:“我是国内H集团的总裁花羽,我只是想和顾氏谈一下合作。
以及,想和南二爷吃顿饭。”
顾南砚笑着,眼睛里却满是嘲弄:“看来你的调查确实不怎么样,就连送请帖,也没将我顾南砚的夫人放在眼里。”
花羽眼底藏着不屑,面上却装着恭敬:“我自然不敢轻视顾夫人,顾夫人在京市的盛名,我还是知道的。”
Advertisement
“既然知道,怎么记不住我云晚娇最讨厌有人惦记我的东西?”
闻声去,云晚娇穿了件黑的针织衫与阔裤,顺着梯,一步一步走到顾南砚的边。
的眼妆很淡,眼尾的睫与眼线上扬,红魅,像极了勾人心魄的狐狸。
这是花羽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云晚娇,貌比照片更令人心颤,咬紧了牙关。
“顾夫人果然和传闻中一样貌,又危险。”
屋内的冷气十足,的后背发凉,上不收控制得起着皮疙瘩。
云晚娇弯,将手中一直拿着的照片扔在花羽边,照片散落了满地。
“喜欢我老公?”
花羽看了眼照片,抬头与云晚娇对视,笑:“是喜欢,顾夫人果然好手段。”
那些派人跟踪他们的照片,以及车内,藏着的顾南砚照片,被云晚娇查了个底朝天。
花羽翘着,着照片,而后撕碎。
“顾夫人,人要大度一些,你占着南二爷这样的优质男人,就应该知道,有多人喜欢他。”
云晚娇:“我当然没有你大度,可以与下属共用一个男人。”
云晚娇摇头:“说错了,是与外人共用数不清的男人。”
手中还留了一张照片,是那天晚上,顾南砚背着的照片。
云晚娇将照片塞进顾南砚的口袋里,而后出一抹妖冶的笑。
“花羽,你的眼睛很漂亮。”
Advertisement
“顾夫人还有喜欢人的癖好?”
“不,我只是有喜欢眼睛的癖好。”
那眼神,花羽虽与对视,可是微颤的手腕出卖了。
手,再次递上请帖,只是这一次的请帖,是递给云晚娇的独一份。
“顾夫人,我是真诚的邀请你们参加我的宴会。”
云晚娇示意十七接过请帖,顾南砚的手始终搭在的腰间,另外两个人全程不敢话。
云晚娇收起笑,靠在顾南砚怀里,甚至抬头,在他的左脸颊留下印。
“宴会我会去的,能屈能,我很欣赏,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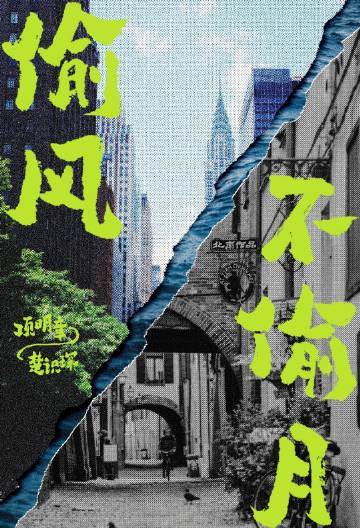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70 章

離婚后,秦少夜夜誘哄求復合
薄棠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她暗戀了秦硯初八年。得知自己能嫁給他時,薄棠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他的情人發來一張照片秦硯初出軌了。 薄棠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秦硯初不愛她。 他身邊有小情人,心底有不可觸碰的白月光,而她們統統都比她珍貴。 恍然醒悟的薄棠懷著身孕,決然丟下一封離婚協議書。 “秦硯初,恭喜你自由了,以后你想愛就愛誰,恕我不再奉陪!” 男人卻開始對她死纏爛打,深情挽留,“棠棠,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她給了,下場是她差點在雪地里流產身亡,秦硯初卻抱著白月光轉身離開。 薄棠的心終于死了,死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
30.6萬字8 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