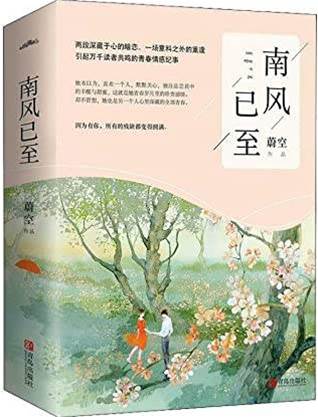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浪漫過敏》 第五章 總裁的女人也得在年會上表演節目
男人沉下來的冰冷聲線讓柯新猛然回想起前陣子一個讓他氣到險些癲狂的夜晚。
“是你?”
電話那頭的那個干脆利落的滾字,柯新至今還記憶猶新。
他之前一直在猜測那到底是誰——哪怕不是男朋友,大半夜的會出現在安念念的邊,柯新都覺得窒息。
之前聽說安念念這麼多年都沒有再找過男朋友,他的心里一直存著幾分希與竊喜,哪怕從來沒有要回頭再找他的意思,柯新也都把這一切理解臉皮薄。
畢竟當年的事畢竟還是他理虧一點的,柯新也在一直告訴自己男人就是要大度一些,原諒小生的小子。
在闕濯出現之前,柯新確實一直有絕對的自信相信自己依舊是安念念獨一無二的最佳選擇,自然也還保留著對的占有。
但闕濯公司的法務部門也確實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
闕濯看著柯新猛地森狠戾起來的眼神將安念念往后護了一步,依舊面無表:“言盡于此,柯先生好自為之。”
安念念就那麼呆滯地被闕濯帶回觀眾席,頂著任開已經熊熊燃燒的八卦目在闕濯的另外一邊了座。
現在臺上員工演出的部分已經結束了,接下來都是藝人的部分。
藝人畢竟經驗富,舞臺上的表現力立刻比剛才員工的那一班子雜耍團強上好幾倍,開場表演強勁而快速的鼓點過安念念的鼓直接擊打在的心口。
雖然并不清楚闕濯剛才是怎麼知道和柯新約在那個安全出口見面,但不得不說剛才柯新一條一條把在撒謊的證據拋出來的時候,是真的有點不知所措。
沒有人會想在前男友面前丟這樣的面子,但柯新剛才的話又確實條理清晰到讓沒有辦法辯駁。
Advertisement
說實話,如果闕濯剛才沒有來,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收場。
安念念想到這里下意識地側過頭看了一眼旁的闕濯,就見闕濯也看向:“怎麼了?”
四目相對的一瞬間,安念念突然被一種莫名的張擊中,幾乎是下一秒立刻便垂下眼眸避開了闕濯的目。
“沒什麼,就是……謝您的。”
闕濯看垂著頭的樣子,沉默著忍了一會兒才沒出手去抱。
這個工作其實對抗能力是有要求的,因為作為他對外對接的窗口,平時跑送文件,通傳達都是安念念來做,有的時候難免遇到董事或東心不好,就尖酸刻薄地刺上兩句來撒火。
就這幫人,之前的幾任男書都忍不住,好幾次跟闕濯晦地提過,闕濯自然心里有數,也有過擔心,想著安念念會不會比他們更不抗,如果沒過幾個月就離職,還得再找,又是麻煩——最早的時候,闕濯確實是不太信任的。
但安念念卻對此好像從來沒什麼緒,也沒有過什麼委屈。
有一次公司團建,闕濯和幾個特助一起打網球的時候聊起這件事,幾個資歷最老的特助都對安念念贊不絕口:“這小姑娘,真行,能忍,上次大東家那位不知道在哪兒了氣,說泡的咖啡太燙了,直接把杯子摔腳邊,當時道了個歉就收拾東西出去重新泡了。”
“是吧,我那次還擔心會躲茶水間哭呢,結果我進去想安兩句,笑呵呵地跟我說,還好今天穿的是加絨的什麼子,沒燙著。”
“什麼什麼子,你怎麼那麼土,那個神!”
“啊對對對,神……”
這不是闕濯第一次從其他同事的口中聽見關于安念念的正面評價了。
Advertisement
辦事妥帖,格溫和,滴水不,這些形容詞或是從同事,或是從合作伙伴的口中落到闕濯耳朵里,都了讓闕濯越來越認可,越來越信任的基石。
但聽得越多,闕濯的緒卻不是對此越來越滿意的。
他開始比之前任何一任男書在崗時都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書這項工作的不容易,明白安念念每一項工作順利完的背后,可能都夾雜著很多就連特助們都有所不知的心酸苦楚。
有的時候手上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在休息的時候會將目投向一面玻璃墻之隔的,安念念的崗位,看著正在電腦前忙碌的人影廓,總想出去問問,有沒有又遇到什麼不講道理的人。
但闕濯知道,只要他推開這道門,安念念永遠都只會朝他揚起無比職業又禮貌的笑容,跟他說:“闕總,剛才您跟我說的這件事可能還需要點時間,我盡快。”
其實他不是想催促的。
他只是想關心一下。
每當那個時候,闕濯就會覺有點生氣,也有點無力。
他有的時候就很想干脆把一切都捅破,就盯著的眼睛告訴,你可以跟我訴苦,可以向我求助,別什麼都自己扛著,無論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至以后不會再有潑婦敢在他的辦公室門前,把盛滿熱咖啡的咖啡杯甩在你的腳邊。
也是那個時候,闕濯發現安念念對他而言,不知不覺已經變得格外不同。
他已經開始想要分的生活,而卻對此依舊毫無所覺,讓他本不敢輕舉妄。
“過一會兒要獎了,你的獎券呢,丟了?”
安念念緒的低落眼可見,一旁任開聽見闕濯輕的聲線,直接一口口水嗆進了嗓子眼兒,把子側過去咳得面紅耳赤。
Advertisement
“沒有,在這兒呢。”安念念一提起獎又來了點勁,趕從兜里掏出自己的獎券給闕濯過目讓他老人家好放心。
闕濯看也沒看任開一眼,接過獎券掃了一眼上面的號碼,兩分鐘后,那頭負責今晚開獎的程序員就意外在獎環節前接到了來自闕濯的親自聯系。
大BOSS第一次與他直接對接,程序員相當張,小心翼翼地問了一聲:“闕總找我有什麼事嗎?”
“今晚大獎增加一個定名額,之前那個名額隨機不變,你現在改一下程序代碼,辛苦了。”
“……”程序員立刻下兩道寬面條淚。
人在后臺坐,活從天上來。
慘。
而安念念又怎麼會知道闕濯給安的方式會如此直白又晦,開獎的時候認認真真地看著屏幕上滾的數字畫,然后看著觀眾席不斷有人發出歡呼,蹦跳著上臺領獎,心真是憾又慶幸。
因為每一個號碼不會被重復選中第二次,前面出現的號碼雖然代表逃離保底,但同時也代表與大獎無緣。
可畢竟安念念去年還了個手機,此刻心里沒有別的,全是僥幸——去年拿了個三等獎,今年來個五等也行啊。于是一邊等一邊坐在那跟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似的合十祈禱,看得臺上負責頒獎的闕濯一陣好笑。
他已經有些迫不及待看著安念念狂喜尖將剛才的郁一掃而空、蹦跳著撲上臺來的模樣了。
果不其然,當最后頭獎的滾畫停留在自己手上的號碼的時候,安念念跑上臺來的樣子就像個開心的小學生,把柯新的事轉頭就拋到了九霄云外。
頭獎一共兩個名額,安念念前面還有一個男員工,倆人喜氣洋洋地登臺,主持人為了畫面觀特地讓兩人保持了一段距離。
Advertisement
男員工這輩子第一次這麼歐,紅滿面地走到闕濯面前,看著眼前這個比他高出大半個頭的年輕總裁,心是澎湃呼嘯的敬仰之。
他是去年年后剛進公司的,還是第一次參加年會,沒想到中了頭獎不說還能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到這個公司傳奇人的真容,這怎麼能讓人不激!
關于闕濯的商業傳說他早就在各種金融雜志上了解過,聽說他不商場上手段雷厲風行不拖泥帶水,私底下生活也干凈明,可以說是除了有的時候不通人之外簡直是行業模范、業界清流了。
男員工越想越張,抬頭看向闕濯的時候額頭上已經被高強度的舞臺燈照出了一層汗,然后就聽行業模范業界清流把裝著獎金支票的信封遞給他,道上一聲:“恭喜。”
然后他關了麥的收音又補上一句:
“可以和我擁抱一下嗎?”
“……”
男員工霎時陷惶恐——這是什麼況,霸道總裁上我?
他莫非是剛才在上臺的時候不自覺表現得太獨特然后被闕總注意到了嗎!?
但總裁的命令誰又能拒絕呢,男員工一番思想斗爭之后還是服從地和闕總來了一個簡單的擁抱,然后就再也沒有然后地拿著支票下了臺。
接下來到安念念,接過信封之后也按照前一個人的領獎流程照貓畫虎地伏進了闕濯的懷里,腦子里卻只有一個想法:大獎的獎金是多來著,早知道剛才數0的時候就仔細一點了!
闕濯就那麼當著全公司上上下下千名員工的面,抱住眼前滿眼雀躍的安念念,同時余不忘掃向臺下觀眾席專門給合作伙伴準備的區域,給了觀眾席上的柯新一個短暫的眼神之后才緩緩地松開了。
獎環節結束后是酒宴,在年會這種本就是以慶祝為目的的場合,還都是同一個公司的自己人,那氣氛簡直是難以想象的高漲。
安念念作為頭獎得主之一自然不可能逃過一劫,結束的時候被灌得神智都不清醒了,扶著墻兩條都直發。
小楊是早就在停車場等著了,可眼看著周圍的車都走得差不多了闕總也還沒來,正準備打電話詢問,就遠遠地聽見安念念口齒不清的聲音:
“闕!濯!我跟你說今天要不是我高興,天王老子也灌不了我!”
“嗚嗚嗚媽媽我中獎了,我要給我媽買個新羽絨服,再給我爸買雙好皮鞋,闕濯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的,我有錢、嗝……了!”
“我得謝謝你對我一年、哦不是,兩年以來的照顧啊,然后你今天還幫我趕走柯新,你可真是個好人啊闕總!!!”
闕濯本來都不想搭理這個醉貓的,但是聽發好人卡發得起勁才有點忍不住了:“閉。”
小楊看闕濯是抱著已經得沒骨頭的安念念過來的,趕非常有眼力見兒地下車幫他打開了車后門,然后幫著闕濯先把安念念塞了進去。
“闕總,先送安書回去嗎?”
安念念一沾車后座就困了,嚷嚷著要去刷牙洗臉,闕濯把外套了把人裹住就不再理會的絮絮叨叨嘟嘟囔囔。
“不用,”
他沉片刻。
“直接回我那。”
夜深人靜的城市主干道上只剩寥寥無幾的車輛穿行而過,安念念真的在后座上小睡了一會兒,直到闕濯想把抱出去的時候才再一次悠悠轉醒。
“爸,我了……”
“……”這人喝醉了酒也這麼氣人,好歹上次還問是不是散會了,這次直接認他作父,“誰是你爸?”
安念念癟著:“爸你是不是糊涂了,我好……我沒吃飯,我只喝了一肚子酒……嗚嗚嗚我要回家……”
“…………”
小楊都沒忍住撲哧一聲笑出來了,然后又在闕濯的注視下迅速收住了笑容。
“闕總,要不然我去附近的便利店給安書買點東西過來吧?”
“不用,讓著。”
朋友還沒追上就當了爹的闕濯心很不好,再想想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為自己一晚上送出去了十萬塊錢,簡直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更不爽了。
他把人抱進電梯之后就直接把往地上一放,又趕在坐地上之前把人扛在肩上,抬手在屁上狠拍了兩下。
“喝醉了也不老實。”
安念念不知道是不是真聽見了,吸了吸鼻子沒了聲音,過了一會兒闕濯就又聽嗚嗚嗯嗯地哭開了。
“闕總我其實真的……我覺你最近對我特別好……”
“……”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啊,就因為你是個好人嗎?”
“…………”
“你怎麼這麼好啊,你對你每一任書都這麼好嗎?就因為我天天和你朝夕相嗎,你能不能說個能讓我信服的理由啊,我想不通啊闕總——”
這一句一個好人卡讓闕濯真的郁悶到了,可酒讓安念念本就不夠敏銳的大腦再一次變得遲鈍,本不到闕濯的緒。
闕濯氣得不行,又別無他法,只能說一句他就在上拍一下,等到出電梯的時候安念念已經安靜如了。
“你怎麼不繼續說了?”
“……”安念念委屈地吸了吸鼻子:“屁疼。”
能把可和可惡這兩種氣質完全融合并永遠都能做到無切換的,只安念念一家。
闕濯的氣被可掉了一半,單手把托著往上掂了掂,就聽安念念無比痛苦:“闕總,我的胃好難……嘔……”
“…………………………”
有句話怎麼說的來著,見過你喝醉酒的樣子還能你的人,那是真。
闕濯對安念念也真的是真了,高級定制西裝外套直接被他扔進了垃圾桶里,除此之外這個生活中到被別人無微不至地伺候的男人現在反過頭來還要伺候這個吐完就睡得如同昏迷的醉鬼。
還好安念念晚上沒吃什麼東西,吐也只吐出來點酒,但闕濯實在是忍不了上那酒臭味,把的外套也一起送進垃圾桶之后直接把人丟浴缸里用花灑沖。
安念念過了一會兒又被沖醒了,胃里的酒吐得差不多干凈讓變相地醒了一部分酒,迷迷糊糊地眨眨眼,就看見闕濯只穿著一件白襯,袖子挽到肘關節,干凈得就好像學生時代很多孩心里都會裝著的那麼一號人。
——如果臉沒有板得那麼死的話。
“你……你能不能稍微有點笑臉啊,跟個殺手似的……”
這被人伺候的人要求還真不。闕濯倒是真想笑,氣的。他手上拿著花灑在浴缸旁蹲下面無表地故意刁難,“安書,我的笑是很貴的。”
聽聽這銅臭味十足的話,真不愧是個商頭目。
安念念癟癟:“那我拿東西跟你換。”
闕濯目些微下移,看襯泡在水中,里面枚紅的完全遮掩不住,深一塊兒淺一塊兒地洇出來。
“拿什麼東西?”
他嚨有點發,聲線也略微渾濁起來,正想清清嗓子,安念念的腦袋已經主地湊了上來,在他上了一下。
“這個東西,可以嗎?”
猜你喜歡
-
連載757 章

婚期365天(慕淺霍靳西)
(此書已斷更,請觀看本站另一本同名書籍)——————————————————————————————————————————————————————————————————————————————————————————————————————————————————————————————————慕淺十歲那年被帶到了霍家,她是孤苦無依的霍家養女,所以隻能小心翼翼的藏著自己的心思。從她愛上霍靳西的那一刻起,她的情緒,她的心跳,就再也沒有為任何一個男人跳動過。
133.4萬字8 2244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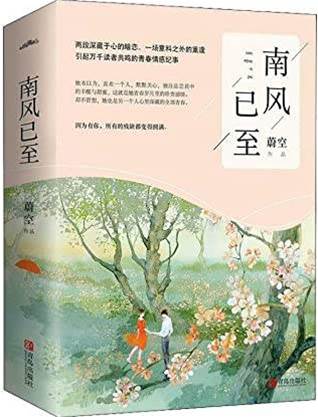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78 章

為情所婚
故事的開始,她闖入他的生活,從此天翻地覆。 故事的最后,他給了她準許,攜手共度一生。 一句話簡介:那個本不會遇見的人,卻在相遇之后愛之如生命。
20.9萬字8 19102 -
完結1547 章

墨少難惹:嬌妻帶球跑
他是商業帝王,清冷孤傲,擁有人神共憤妖孽臉,卻不近女色! 她是綠世界女王,冰冷高貴,卻…… “喬小姐,聽聞你有三禁?” 喬薇氣場全開,“禁孕,禁婚,禁墨少!” 轉瞬,她被丟在床上…… 某少居高臨下俯視著她,“禁婚?禁墨少?” 喬薇秒慫,想起昨夜翻雲覆雨,“墨少,你不近女色的~” “乖,叫老公!”某女白眼,拔腿就跑~ 某少憤怒反撲,“惹了我,還想帶球跑?”
272.3萬字8 60252 -
完結850 章

閃婚當晚,禁欲老公露出了真面目
【重生打臉+馬甲+懷孕+神秘老公+忠犬男主粘人寵妻+1v1雙潔+萌寶】懷孕被害死,重生后她誓要把寶寶平安生下來,沒想到卻意外救了個“神秘男人”。“救我,我給你一
87.7萬字8.18 36674 -
完結201 章

我欲將心養明月
高中暑假,秦既明抱着籃球,一眼看到國槐樹下的林月盈。 那時對方不過一小不點,哭成小花貓,扒開糖衣,低頭含化了一半的糖,瞧着呆傻得可憐。 爺爺說,這是以前屬下的孫女,以後就放在身邊養着。 秦既明不感興趣地應一聲。 十幾年後。 窗簾微掩,半明半寐。 秦既明半闔着眼,沉聲斥責她胡鬧。 林月盈說:“你少拿上位者姿態來教訓我,我最討厭你事事都高高在上。” “你說得很好,”秦既明半躺在沙發上,擡眼,同用力拽他領帶的林月盈對視,冷靜,“現在你能不能先從高高在上的人腿上下去?”
31.6萬字8 2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