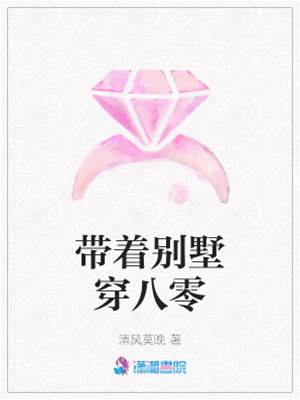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離婚冷靜期?鹿小姐上訴凈身出戶》 第1卷 第120章 老婆牽手,季總紅了眼
是溫硯禮發來的消息。
【有空一起吃晚飯嗎】
打字回復:【最近有點事】
溫:【晚星,你是在躲我嗎】
看著這條消息,愣了幾秒,【沒有,你別多心】
溫:【財團高薪挖鹿氏老員工的事,我已經查清楚了,想把犯事的人員名單給你,要怎麼置你說了算】
鹿晚星:【不用了,溫氏部的事,你決定就行】
這條消息發過去,溫硯禮沒再回復。
他似乎有點不高興了。
但鹿晚星這會忙著陪弟弟出院,沒空想他的事。
為了慶祝鹿子眠逢兇化吉,一家人決定出去吃,一直折騰到晚上九點多鐘才回家。
他們是打車回來的。
寧霞扶著鹿子眠,鹿晚星推著箱子,有說有笑地聊起元旦檔一部很火的新電影。
今晚沒有下雪,寒風依然蕭瑟。
家門口的墻邊上,坐著一抹頹然高大的影,手邊擺著幾瓶喝的洋酒。
鹿子眠率先注意到那抹影,沒好氣道:“哪里來的醉鬼,別臟了我家門前的地兒。”
鹿晚星跟著看過去,是季司予。
他臉上是明顯的醉意,被寒風凍紅的指骨拿著一瓶喝掉一半的洋酒,只當沒聽見鹿子眠的嘲諷,獨自惆悵。
“哎!季司予!你自己有家不回,在這裝可憐給誰看啊?”
鹿子眠上前兩步,想攆他走,被鹿晚星攥住胳膊,“子眠,你跟寧姨先進去。”
寧霞很懂,主拿走鹿晚星手邊的行李箱,拉著鹿子眠率先進家門。
夜寂靜,鹿晚星緩緩走到季司予腳邊,輕聲問:“是發生什麼不好的事了嗎?”
季司予眼睫耷拉著,盯地面,“沒有,只是……無聊。”
“無聊就跑到我家門口來嚇人?”
Advertisement
他沒什麼底氣,低啞的聲線也完全沒有往日的冷傲,“把我當空氣無視掉就好,我不會吵到你們,我待一會就走。”
“行吧。”
鹿晚星能覺到他心很差,似乎只是想找一個覺得舒心的地方消化緒。
繞過他,正要進家門,手腕又被他拉住。
“鹿晚星。”
他極低的聲線幾乎快淹沒進夜風里,但鹿晚星聽得很認真。
他說的是:“你心里,還有沒有一點點那個傻子?”
鹿晚星子僵住,沒回頭,也沒回答。
他微白的薄輕輕張合,言又止,“如果……”
如果你心里還有那個傻子,我可以拼盡全力,把那個傻子找回來,還給你。
作為換,你也試著我幾天,行不行?
他始終沒問出口,鹿晚星也沒給他機會問,手拿走他手上的洋酒。
“別喝了,趕回家睡覺去,一會凍暈了倒在我家門前,還得訛上我。”
拿著那瓶酒回了家,季司予沒攔,仰頭著無邊黑暗的夜空,一顆星星都沒有。
深夜十一點。
鹿晚星洗完澡,吹干頭發,余無意間瞥向窗外。
又下起雪了。
季司予走了沒有?
這麼蹲家門口,琢磨著,改天也像溫硯禮家那樣,門口安個大監控。
深夜零點。
翻來覆去睡不著,翻下床,刷地一下打開窗簾。
雪越下越大了。
自顧自道:“可能是晚上吃太飽了,該出去走兩圈消消食。”
寧霞和鹿子眠已經睡了,隨手拿了把傘,穿過前院小花園,去到大門口。
側目一瞥,季司予還沒走,就像黏在墻似的。
昏黃的路燈將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窄窄,孤寂單薄。
他任由雪淋著,正拿打火機點煙,惆悵吐納煙霧。
Advertisement
鹿晚星皺著秀眉,無語得嘖了一聲。
至在門前坐了三個小時,他覺不到冷嗎?
打著傘走過去,傘柄微微向他傾斜,開口有點怪氣。
“把自己弄得可憐兮兮,你學賣火柴的小孩呢?不過你應該算……賣煙的老男人?”
季司予像被抓包似的,有點心虛,“我沒發出聲音,吵到你們了?”
鹿晚星理直氣壯:“你的煙熏到我了,熏得我睡不著。”
“……”
酒被沒收了,只能煙,這好像是第六。
他沒辯解,乖乖掐滅煙頭,“不了,你回去睡吧。”
“那你呢?”鹿晚星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回家?”
蘭灣別墅沒了生活過的氣息,已經算不上是家,季氏莊園從來都不算家。
從離婚生效的那一刻起,他沒有家了。
這里是離鹿晚星最近的地方,哪怕只是坐上一會,心里都是踏實的。
“我再坐一會,一會就走。”
鹿晚星不肯:“可是你影響到我休息了。”
他短暫失語,看向車道對面的那棵樹,指過去,“那我離遠一點,到那里去坐。”
“不行。”
也許是被雪淋得腦子不清醒,鬼使神差地說:“跟我進去吧,允許你借宿一晚。”
季司予黑眸微亮,怔愣地盯著漂亮的臉蛋,沒反應過來。
有點難為,轉就要走,“不樂意就算了。”
“樂意的。”
膝蓋又僵又痛,雙凍得快失去知覺。
季司予咬牙,強撐著起,挪雙跟上。
腳下虛浮沒力,他了一跤,往地上摔。
鹿晚星眼疾手快地牽住他的手。
掌心相,溫熱附上冰冷。
他錯愕地看向。
這是他印象里,第一次主牽他的手。
掌心里的暖意直達心尖,融化了他心口淋漓的雪,使他的眼圈紅得一塌糊涂。
Advertisement
鹿晚星的注意力并不在牽手,觀察他的,“能不能好好走?”
他想說能,但又私心想多牽一會,“腳,麻了。”
鹿晚星冷下臉,吐槽了句:“麻煩的男人。”
將傘塞進他手里,抬起他的胳膊搭到自己肩頭,另一只手攬住他的勁腰。
就這麼扶著他,一瘸一拐地進別墅,往客房走。
“你以前說我作,依我看,沒人作得過你,大冬天淋著雪坐幾個小時,你是有什麼傾向?”
吐槽著,將人扶到小沙發前。
季司予雙力,鹿晚星松開他的瞬間,他幾乎是摔進沙發里,脊背登時一。
“嘶……”
他咬下,咽回險些出聲的痛哼,森然慘白的指骨按住左邊肩頭,擰的眉心極力忍痛。
鹿晚星立刻察覺不對勁,“你傷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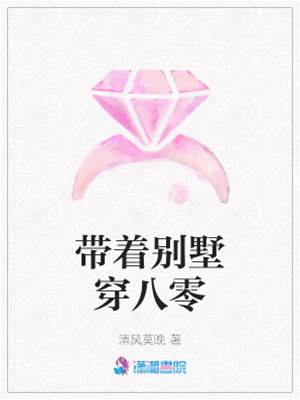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