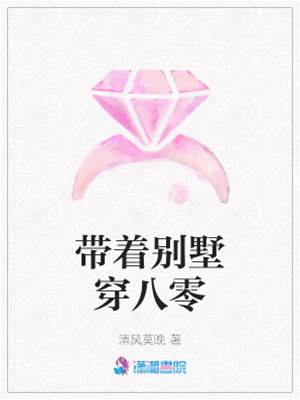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相依為病》 第1卷 第373章 最后的機會
景深默默的想。
肩而過相錯的船上,瀕死的是知道要打仗,槍彈無眼,一定被勸穿上防彈的江州。
還有……南桑。
景深不知道南桑和江州在獵場到底發生了什麼。
讓顰死的江州放棄了屠城。
只知道現在的事實是,南桑在那艘去京市的船上。
江州若死在半路,到京市后,南桑會因為知道屠城事,被就地被格殺。
若是不死。
會被江州關起來,永不見天日。
江州不會放回來,楊淺和忠叔就算知道了,也接不回,反倒可能被江州瞞著南桑,直接弄死了。
到那會,南桑將在豪華的籠子里吃喝尊貴,卻孤零零,邊無人的度過余生。
景深抵著門板的額頭收回。
扭頭看向阿財,“我會把帶回來。”
景深告訴他,更像是告訴自己,“平平安安的帶回家。”
景深大步走了。
幾步后,腳步加快,一邊打電話一邊在漆黑的夜里朝遠奔跑。
“幫我召集本地流竄過去的雇傭兵,越多越好。”
景深從東邊下一站的港口開始朝前報。
一直報到八小時前他停靠的下一站,“一站一查,無橫標民船,上下船為東邊人。目的地為海邊停靠點就近醫院搶救室,男一八九,臉上有橫向疤,下四個貫穿傷,附帶鐵銹。直徑十八公分,重度失,心肺功能有損,疑多次休克。”
“找到之后呢?”
景深在黑夜中狂奔,風像是那天去救南桑般,盈滿了風。
“殺。懸賞一億金。”景深呼吸微重,伴隨著颯颯風聲,聲音卻清楚到極點,“其余的與我無關,只其中一黑眼,帶走,寸發不得。”
景深頓足回眸,看向遠的鹽城,“登暗網,記住,只要逃竄過去,有無標槍支的雇傭兵。”
Advertisement
江州如果死在半路上,想保下南桑不難,在第一時間求鐘老出面就夠了。
但到那會知道南桑還活著的人會數不勝數。
南桑想回家,過回從前的生活不可能。
如果江州不死更糟。
一旦他帶南桑了京市。
想把南桑弄離開太難太難了。
把南桑送回家,接著沒人打擾的在鹽城平安生活到老,更難。
那麼想把再一次被不可控的江州弄的一切撥回正軌。
只有一個辦法。
在江州有可能活下來帶南桑到京市之前手。
讓江州死。
用假的雇傭兵混倒打一耙,踩著因為毀約,怕雇傭兵把這事鬧大,被牽連心虛不敢妄不敢多言多追究的東邊尾。
讓他們自己想辦法把江州的死合理化。
再從各方勢力中周旋,才能還南桑清凈,讓過回從前的生活。
這是景深能想到的唯一一個救南桑的辦法。
也是唯一一次機會。
……
聿白上船駛離鹽城沒信號的地界后第一時間聯系了他最高直連上級。
是江州在鹽城唯一聯系過,也是唯一知道他帶人去鹽城的上方。
江州家族強推上去的最高級,江州堂叔明年要接替,快要退休的劉老。
劉老給的指令是江州不能死在外面。
他份尊貴,為保萬一,必須送京市搶救。
接著晦說去了京市,萬一救不活。
江州的死因他們有可作空間。
畢竟他出來做下的事,見不得,不能被人知曉。
那些傷太重,宣稱自然死亡,對外也算是代,不會引起波瀾。
聿白狠皺眉,再次強調了遍江州傷勢的嚴重。
對面很不近人,也相當現實的臉收斂了。
方的說沒人想讓他死,北部變更手續繁雜,加上短時間變更數次,還有之前人人皆知的景深輿論在那放著。
Advertisement
誰也不想在事剛平息不過爾爾的時候再鬧出事。
也沒人能擔得起這事鬧出來的責任。
更何況雖然說他明年就快退休了。
但沒有江州,他不可能會在那種況下被從地方調過來。
他草草解釋了遍后。
改話說實在撐不住了,可以沿途停站急救,但要第一時間通告,他會坐直升飛機過去候著,如醫療條件不達標,方便轉移。
劉老算空降。
聿白本和他不,但因為位置的緣故,依舊百般敬重。
可他接電話之后說的話,莫名給聿白一種對捧他上去的江州,很戒備和算計的覺。
否則為什麼滿后續做法。
在他再次強調遍傷重后,像是蓋彌彰般,對他這種小份的人解釋說他不是想讓江州死。
最奇怪的是。
他份何等尊貴,尊貴到兒半年前婚嫁都不能出席面。
結果這個陌生的地界卻說來就來。不派親信,而是親自。
劉老冷不丁帶笑蹦進一句話,“對了,江總回來有帶什麼人嗎?”
聿白蠕片刻,“不曾。”
劉老輕笑且意味深長:“是嗎?”
聿白拿到江州命有保障的指令后,沒再多說,掛上電話。
他想就地讓江州去醫院,心里卻莫名不踏實。
就地的話,因為劉老親自來,尋常的直升飛機派遣,會鬧出極大的靜。
加上江州離開京市前下的指令。
查這一年來來往京市和鹽城的全部人員信息。
信息中還要有人臉。
這個靜巨大,這些天知道的人會無數。
一旦順著劉老的直升飛機靜查過來,想不知道南桑的存在都不可能。
再朝鹽城查,事就不可控了。
聿白始終記著江州短暫醒來那幾秒,氣若游攥住他袖子,磕磕絆絆出的話,“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南桑的存在,是任何。”
Advertisement
他決定如果有可能的話,還是回京市。
最起碼在他的認知里,京市不管是哪,江州都能掌控。
船在江州能撐住的況下不停歇的行駛了十一個小時。
距離回京市還有一半的路。
江州要不行了。
沒橫標的船,不用通報,急在夜幕降臨后靠岸。
聿白讓人抬著擔架把他送去最近的醫院。
拎著手銬走近南桑。
南桑腦袋靠著船板,虛弱掀眼皮看他一瞬,配合的出手。
聿白扣上。
拽著步履踉蹌的在黑夜里跟上前面人的步伐。
休克人事不知的江州被送進了搶救室。
江州大量失,有懂醫療的看護著心率和缺氧況。
但因為休克多次,嚴重的傷口沒妥善理,況還是危險到了極點。
聿白在醫生出來讓他簽字時,問他江州的況。
醫生語無倫次,該握手刀的手指枯黃,約發,典型的煙多了神經不靈敏。
從哪看,都不是個讓人信得過的。
聿白手掌握拳。
側目看向坐著外面鐵凳子上單薄的南桑,戴著帽子,罩了漆黑的毯,不起眼,但不經意出的白,還是顯眼的。
他不想把靜鬧大,最本的原因就是江州說不能讓人知道南桑的存在。
但……
江州要活著。
聿白給劉老打電話,請求和這座城市的主理人聯系,立刻馬上加派專家,救江州的命。
在劉老應下后莫名補充,“江總的傷有濃重的鹽城地方彩,瞞不住,除非火化,但火化只有親屬簽字,才能同意,否則便會被人輕易察覺出有貓膩,一查到底。”
聿白在暗示他,鹽城的事,江州是始作俑者,他是知者,出事都跑不掉。
劉老沉寂半響,笑笑溫聲說好。
半小時后,大批救護車停在醫院門口。
Advertisement
醫生護士魚龍慣出,涌進江州所在的搶救室。
聿白起,和親自過來的主理人握手。
而南桑,早在聿白打電話前,就被他關進江州所在搶救室,他守著江州也能看著的,三米沒窗戶沒開燈的雜間里。
手銬從一個變兩個。
一只在手腕,一只拷在旁邊的柱子上。
腳同樣。
南桑很,很,因為暈船的后勁,酸無力。
更想坐下來。
可這柱子略,手腕卡著的地方在上半段,中間出一圈的結環繞,下不去。
還有,熱。
船上為了維持江州生命征,開了制冷空調。
上是從鹽城來穿的羽絨服,還好。
這地不冷,尤其是沒窗戶的雜間,又悶又熱又小。
南桑的羽絨服因為被拷著不了,不了。
靠著柱子站著,一瞬后轉腦袋輕抵,任由額頭在難的冷汗下去后冒出熱的汗,低聲自言自語,“如果當時喊出來了……”
南桑看到那個背影后想喊,前奏已經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名字。
卡頓的兩秒。
船飛速駛過,那一聲前奏,被兩船相近濺起的波浪掩埋。
南桑瞳孔因為疲累和虛弱渙散,低聲喃喃:“就算知道他什麼名字也是白知道……”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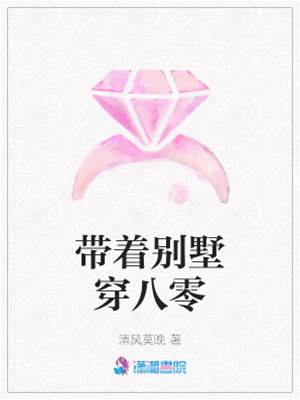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