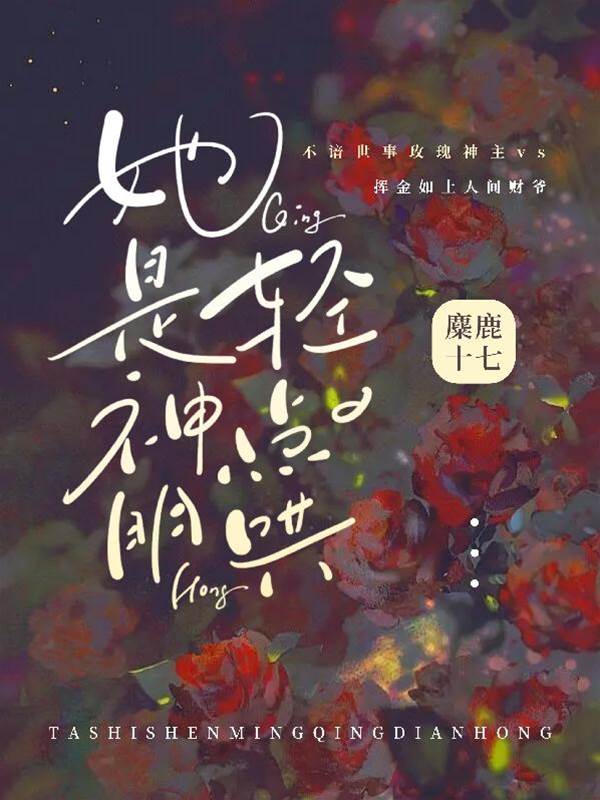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相依為病》 第1卷 第378章 快到家了
江州抱住大汗淋漓疼痛難言的腦袋,微微躬,一口又一口緩和著呼吸。
幾秒后抬手把聿白出想他的手打掉。
聿白猛皺眉:“我喊了您近三分鐘,您沒聽見嗎?”
“怎麼這麼多汗?您哪不舒服?”
“江總,江總,江總。”
江州啞聲打斷,“喊不醒是麻藥過去的后癥。”
他掀開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多的厚毯,“出汗是熱的。”
江州額頭汗水不斷,眼帶紅,臉發青,膛起伏弧度略高,但面卻平靜并且穩定,聲音同是,“我睡了多久?那邊的況怎麼樣?”
聿白打完電話江州已經睡著了。
他沒打擾,去了一直在哭的駕駛艙船員小曾那。
小曾是開船的,但只是副手,單獨控船這是第一次,而且屬于派遣,不是直轄。沒直面過任務,很害怕。怕船開不好,怕突然來的雇傭兵。
聿白穩定了他的緒,和他一起定路線。
又去看了眼背對門躺下的南桑。
去檢查了遍燃料和資,重新裝備了槍。
再出來,江州還在睡。
劉老的電話來了,找江州。
江州喊不醒。
聿白當時手探出,有呼吸,但好像不太對,心跳頻率也不太對,皮的熱度約都不太對。
三分鐘喊不醒,想告訴劉老,江州醒來了。
只睡了三個小時,但睡的太沉了。
像是……休克,還是最危險的后休克。
江州沒理會他的皺眉擔憂。
接過衛星電話,打給劉老,“抓到了嗎?”
“死了一個,剩下四個全擒。”
江州手指蜷了蜷,“重癥監護室那怎麼樣?”
“如果你沒突然跑路,必死無疑。酋州的槍你知道,火藥濃度比正常的大三倍。一槍就會讓人殘,你那沒人塞了個枕頭的床被十幾槍打篩子,都快被掀飛了。”
Advertisement
劉老似心有余悸的慶幸道:“還好還好,剛手完沒等麻藥,你就走了。但凡晚走幾分鐘,我千辛萬苦才從閻王爺手里搶回來的你這條命,就要這麼白白丟了。”
江州沒理會他惡心的惺惺作態。
囑咐審。
就在那,瞞住消息,審到底。
偽裝一切順利,把下懸賞的人引出來。
劉老似好奇,“不過你是怎麼知道他們行計劃還有逃跑路線的,如果不是你說這三條線,我們一個都抓不住,尤其是草坪上那個,不止抓不住,你和我兩條命都要代在這。而且還一口咬定是不想死的潛逃。”
江州沉寂一瞬,“老天爺偏。”
劉老笑,“老天爺偏不假,江總卻更有能耐,在這個隨便找的地界,都有自己龐大的眼線,劉某自愧不如,甘拜下風。”
江州冷笑一聲,沒說的確是老天爺偏。
順著他的聯想,裝作那的確有他的眼線。
讓他務必嚴審,把幕后人揪出來。
“以黑發黑眼的姑娘為切口嗎?”劉老突然悠悠丟出一句:“那姑娘是您帶走了,還是說在混中丟了。”
江州臉瞬間沉下。
劉老意味深長道:“剛才忘了跟您匯報,已經審出了一個。”
江州黑臉沉默許久,“要殺我的是景深。”
劉老明顯錯愕,“景深現在算鐘老那邊的,怎麼會呢?還有,他不是一直在國外嗎?”
江州打斷:“把我帶人回來的事咽進肚子里,生擒景深。證據證詞證人,三證齊全,抓捕他回京市定罪。消息不得泄半分。鐘家那不用你心,只要做足了罪名,鐘家不會管。我說的這些你做到,我許你指一門生,明年退后接你的位子。”
劉老靜默一瞬,再度提起笑,且親又親熱:“您堂叔呢?”
Advertisement
江州也笑,“撤走,你所屬部門,江家一個不留。”
江州補充,“資金持續不會中斷,咱們兩家依舊綁在一起,只是各司其職。”
“多謝江總大恩,劉某絕不忘您提攜之恩。”
江州不喜歡和這種偽善毒的人周旋,真的非常不喜歡,甚至稱得上厭惡。
為了江家榮耀,找景深報仇,他忍了一年,含笑周旋不斷。
他勸自己忍忍,一年都忍了,再忍忍沒什麼,角的笑卻還是沒了,冷道:“第一,景深的事事關重大,不能有失,必須要抓住,三證也必須要齊全。第二,鹽城所發生的一切,還有我帶人回來這件事,再多一個人知道,我江州把你這個該死的糟老頭子大卸八塊!”
江州北部負責人后,緒偶暴躁,也偶罵人,但對高位卻是客氣的,畢竟他現在不是自己,后面站著一個偌大的江家,代表的也是江家。
這是他第一次怒了。
還沒怒完,江州冷道:“聽懂就給爺一聲,你個該被丟進海里喂魚的老狗。”
劉老提起笑,勉強道:“劉某記下了。”
江州把電話掛了,沒讓聿白推,自己從船艙推著椅出去,坐在甲板之上。
“您現在不能吹風。”
“去看著里頭吧,不用管我,還有,看南桑怎麼樣,如果神好點了,讓吃點東西。”江州黑發被風吹揚而起,臉還是不好,呼吸也太重,但眼神卻是清明的。
聿白多看了幾眼去了。
快速行駛中的船只,帶起的海風出奇的猛烈。
江州被吹的發暈,上沒再出汗,反倒一層層的漫起了冷,卻一不。
因為他要保持清醒。
就因為那三小時的睡,還有事發太突然,忘了那些不想死的潛逃者是知道南桑存在的。
Advertisement
導致一時大意,南桑存在還是被劉老知道了。
江州其實可以回去。
把掌控權奪回來,事還有轉機。
但不行。
讓景深和南桑相見,是他的雷點,哪怕可能太渺茫,他依舊打死也做不到,他要盡快盡快帶南桑去自己的地盤。
不回去,全部事就只能給劉老。
事突變這樣,其實是因為江州想要的太多。
想趕回去,想讓劉老把鹽城還有南桑的存在抹去,想讓他抓住景深。
權衡利弊后,一個都舍不下。
就只能和他換條件。
劉老被他養的獠牙畢現,想咬他。江州不太有所謂,他多的是錢,權勢更多,只是煩和惡心,因為后續還要再重新捧人。
他真正有所謂的是之前給江家鋪的路,等劉老回去后會快速水一大截,遮掩不住。
并且回京市后,像原定屠城的權威加不可能。
像從前那樣肆無忌憚也不可能。
江家人被他進去的太多,轉瞬就會察覺出來。
這件事該怎麼和江家人代。
江州抬手按了按眉心,喃喃:“沒辦法代。”
他思維急轉。
想來想去,只要劉老閉,把鹽城的事遮擋住,再加上他不讓任何人看見南桑。
等過幾月他重新捧起人來,江家才不會再追著查劉老拿什麼拿了他。
他和南桑就可以安定下來了。
江州看著遠遼闊的海面,輕輕勾了,“南桑……”
聲音沙啞卻又溫存繾綣。
江州驀地有點得意了,自言自語,“雖然出了點變故,小小的,但我得到的更多,老天爺終究是偏我的。”
給了劉老要的東西。
鹽城和南桑,他會遮掩的比他還積極。
南桑的存在不會有被人知道的風險了。
幾月之后,劉老滾蛋,天下太平。
更重要的是他最忌憚的景深沒了。
Advertisement
江州角的笑放大了,昂首在海風的吹拂下嘿嘿樂個不停,約可見十九歲那年張揚肆意的年影子。
他的臉越來越青,呼吸越來越重,因為畏寒全發抖,明顯很不對勁。
一清二楚卻不擔憂。
搖頭晃腦,神采飛揚,聲音重且雀躍意味十足,看向湛藍的海岸線,似在隔空對景深炫耀,“老天爺終究偏我的證據是,先找到南桑的是我,而不是你景深。”
江州在甲板吹著海風保持清醒了八個小時。
卻不無聊。
因為雀躍和激,興致的看黎明、看海岸線爬起的日出、看太升起一直到高照、再到即將下山、半片天布滿晚霞。
船終于進京市邊界。
按照他的要求,速度慢下,等待天黑。
劉老的電話也來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他讓潛逃者和暗網人百般周旋。
在十一個小時后終于和景深達了直接對話。
不是上次的變聲,是真聲,確定為景深。
他要照片,船,姑娘。
劉老不解,“他說的是什麼船?”
景深原定他們跑路的船就是江州的船。
江州沒解釋,轉椅,對著船拍了一張發過去。
凍到有點僵的手推著椅去船艙。
沒了海風吹拂的醒神,眼前猛得黑了一瞬。
他晃了晃甩走,朝著南桑在的房間走。
輕輕擰開房門。
看著背過去的影,勾起笑,撇嘀咕:“沒良心。”這麼長時間了,也不知道出去看看他。
但江州的笑還是在。
尤其南桑的姿勢恰好,只能看到背影。
他因為偏執到病態的保護,不想任何人瞧見的臉,即便是已經約知道他帶來是誰的劉老。
江州對著南桑拍了一張,發給劉老。
躬想把門關上再回甲板,一瞬后手莫名頓住。
默默的看著。
不知道看了多久。
劉老短信進來——錢到賬了一半,定金,賬戶信息正在核對,人時間定在一小時后。
錢到賬,證據便齊全了,江州心里的大石徹底落地。
視線從南桑側睡的背影,看向狹窄床空出來的一點位置。
鬼使神差的推著椅走近。
呼吸微微屏住。
抬起四手指傷了,但其余完好的右手按上船邊,小心翼翼的朝上爬。
有點不順利,位置小,手臂酸沒力氣,子太重。
但江州還是蹭著蹭著爬上去了。
半個子懸浮在外,一點點挨著床邊。
按說不應該,江州除了和南桑捅破最后一層窗戶紙,能做的都做了。
甚至于捅破窗戶紙的人,因為刺激等可能不會做的。
他們也做了。
和南桑一起睡,更是家常便飯。
在鹽城醫院,一年未見,江州都不是特別張。
現在卻就是張了,還有點小心。
因為面前的南桑不是從前的南桑了。
是真的真的會好好和他過日子的南桑。
不裝不假,乖乖的,每日每日愿意主鉆到他懷里的南桑。
江州手輕搭的腰,朝前蹭了蹭,腦袋磕在單薄的背脊上。
低低啞啞的說:“你睡著了嗎?”
南桑不知道自己睡沒睡著。
只知道不太舒服。
好似是因為暈船吃不下東西,水喝的也寥寥。
十幾個小時一直蜷在狹窄的床上,因為疲累和困倦反復的醒來睡去。
迷迷糊糊的瞧著漆黑褪去,白天來到,天一點點的爛漫。
從小窗口看去,有時候睜眼,太在最上面。再睜眼在中間,再睜眼,像是下去了,只余晚霞爛漫。
說是睡著了,卻也像醒著。
從江州開門,便輕而易舉的睜開了眼睛。
對他進來,艱難上床一清二楚,卻一沒,只是呆呆的看著外面。
南桑沒答,江州卻約知道醒了,冰涼的手朝前,虛虛抱著,“對不起。”
“能說話的第一時間沒問你累不累,有沒有人在我沒意識的時候欺負你,還對你很兇,摔倒了也沒管,上船后也沒來看你。”
江州聲音沙啞,但疚又溫,再朝前摟了摟南桑后,像是撒般:“原諒我好不好,以后我不會了。”
江州哄南桑,“我會對你很好很好,每天讓你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什麼都給你最好的。”
“南桑。”江州聲音小小的,“求你了,別生我氣了。”
南桑看著外面緩慢移的暗云朵,開口了,“是快到了嗎?”
說話了,在江州想法中便像是和好了。
江州摟,悶悶的笑了,“恩。”
南桑喃喃:“快到了為什麼越開越慢。”
慢的像是蝸牛爬。
明明剛開始,快到了極點,船艙跟著橫沖直撞。
可半小時前,就開始了這個速度。
南桑……討厭船。
不想待在這上面了,一分鐘都不想。
猜你喜歡
-
完結551 章

總裁聽我的
顏可欣單槍匹馬去找未婚夫尋歡作樂的證據卻沒想被吃干抹凈血本無歸反擊不成?那逃總可以了卻沒想這男人恬不知恥找上門,百般無賴的表示。“睡了我,還想就這麼跑了嗎?”
97.1萬字8 19077 -
完結242 章

冷少的逃跑嬌妻
在陸琪琪20歲生日那天,不小心誤睡了總裁,還將他當成了牛郎,隨后甩下100塊大洋離開。向來不注重感情的冷慕晨卻對陸琪琪香腸掛肚了5年。5年后,陸琪琪帶著天才可愛寶寶回國,再次偶遇了冷慕晨——“5年前,我讓你逃走了,這一次,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了的。”冷慕晨對著陸琪琪愣愣的說道。
56.9萬字8.14 28173 -
完結1094 章

南太太馬甲A爆了
父母從小雙亡,蘇清歡從小受盡各種寵愛,來到城市卻被誤以為是鄉下來的。姑姑是國際級別影后,干爹是世界首富。蘇清歡不僅在十五歲時就已經畢業修得雙學位,更是頂級神秘婚紗設計師Lily,世界第一賽車手,頂級黑客H。當蘇清歡遇上南家五個少爺,少爺們紛紛嗤之以鼻……直到蘇清歡馬甲一個個暴露,五位少爺對她從嫌棄分別轉變成了喜歡愛慕崇拜各種……
193.8萬字8 127400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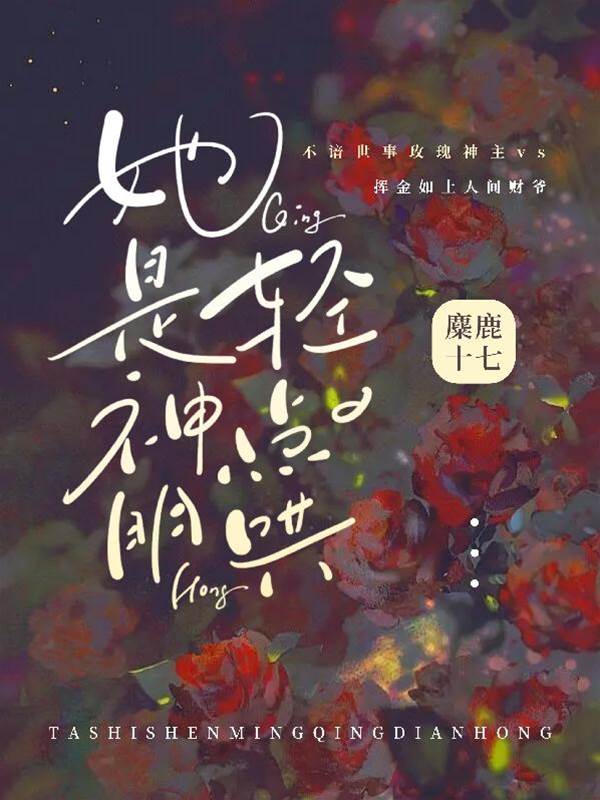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連載138 章

蓄意嬌養誘她入懷
【蓄謀已久+甜寵 + 曖昧拉扯 + 雙潔1V1 + 6歲年齡差】【人間水蜜桃x悶騷高嶺花】 南知做夢也沒想到,真假千金這種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狗血的是,她被下藥,把叫了12年的顧家小叔叔給睡了。 怎麼辦?跑路唄。 花光積蓄在暗網更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親手養大的水蜜桃,剛啃了一口,長腿跑了。 找她了三年的顧北期忍著怒氣,把她抵在車座角落,“睡了就跑,我算什麼?” 南知:“算…算你倒霉?” 顧北期:“這事兒怪我,教你那麼多,唯獨沒教過怎麼談戀愛。” 南知:“你自己都沒談過,怎麼教我?” 顧北期:“不如咱倆談,彼此學習,互相摸索。” - 顧家小三爺生性涼薄,親緣淺淡。 唯獨對那個跟自己侄子定了娃娃親的小姑娘不同。 他謀算多年,費盡心思,卻敵不過天意。 被家人找到的南知再次失蹤。 在她訂婚宴上,男人一步一句地乞求,“不是說再也不會離開我?懷了我的崽,怎麼能嫁別人。”
1.8萬字8 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