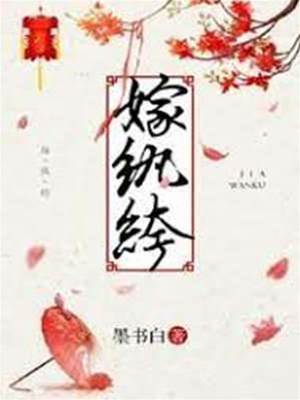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鳳鳴朝》 第63章
第63章
趁谷六幾人走神的空當, 胤奚袖口一擺,作嫻地擲了牌。
摴蒱是一種流行在江左的消遣玩意,五枚牌的兩面分別刻有黑與白兩種圖案, 若擲出五張全黑, 便是頭彩, 稱為“盧”;四黑一白, 則為次采, 名為“雉”, 餘者則是雜彩,各有說法名目。
谷六見他的架勢像模像樣,應該是個中高手,心中驚疑,出于賭徒的本能低頭去看。
卻見桌面上明晃晃擲出了四白一黑。
挫得不能再挫的雜采。
“……”谷六連同四個同伴無言以對。
胤奚面不改,說:“我輸了。”
說罷又手,還要再擲。
谷六這下子站起,“朋友,山有山路水有水路, 什麽來頭劃出個道來。我們兄弟玩的一局一千錢,輸了, 你認嗎?”
“認啊。”胤奚揮袖擲蒱, 瀟灑風流。
那從容不迫的作, 怎麽看都是賭慣了的老手。
谷六打量此人的氣派, 看他料講究, 不像市井出,可要說他上流出的那份不正經,又與他姣好的相貌格格不,倒像和他們是一路人。
剩下的那幾個人, 聚會神盯著桌面。他們原以為此人這般鎮定,必然深藏不,肯定是等著先輸之後,一把撈回。結果他們一直數了十把——
胤奚連輸十把。
谷六神愈發古怪,胤奚神毫不慚,轉頭向守在門外的乙生喚了聲,取來一張解典鋪的兌票,并指推到桌上。
胤奚含笑道:“一萬錢,請哥哥們喝杯水酒,還不要嫌棄。”
幾人互相看看,谷六警惕地瞅著這不速之客,“你逗我呢?”
這座簡易的酒寮,原是浮玉山部幾個小頭頭的一個聚點,用來傳達山上的指令報,閑的時候順便喝喝酒賭賭錢。
Advertisement
本地人都知道,這裏不對外做買賣,所以很有人會沒頭沒腦地闖進來。
像這樣上趕著來送錢的,就更了。
胤奚寵辱不驚的樣子,眉間出許歉,“主家管得嚴,不讓賭,是以不大會玩。讓朋友見笑了。”
他自長在羊腸巷,做人再老實本分,耳濡目染著東鄰西巷的三教九流,想學幾分氣,還不是手到擒來。
谷六盯著他:“那閣下是來做什麽的?”
胤奚擡眼:“初至貴地,想同諸位個朋友,打聽些事,不知谷六哥肯不肯給面子?”
谷六擰眉打量胤奚半晌,又單腳踩著凳子坐下了,皮笑不笑道:“咱們這些混子,可不敢同京城來的貴人朋友。聽說皇帝老爺新封了一位史,很是不凡吶,哪怕鄉野之地也有耳聞——”
胤奚眉梢微挑。
谷六向前傾:“這位小哥一口一個主家,你的主家,不會姓謝吧?”
胤奚指腹磨著木牌的邊緣,低頭無聲笑了笑。
聽這意思,對方看起來也不是全無防備。
這便怪了,要說郎打探封氏宗部的主事人,是為了找到失蹤的清田員,那麽他們等在這裏,揣測出他的份,卻毫不見驚慌,難道擄走朝的不是浮玉山的人?
否則,他們便是主等著請君甕,想兩頭吃嗎?
自古天高皇帝遠之地,沙海養虎豹,水深出惡蛟,何況郎推行的新政,了多方利益。胤奚審慎道:
“卑不言尊,我主家的事我不好多說,不過胤某本不過是挽郎出,白事裏尋生計,吃碗被人忌諱的飯糊口。若非主君垂憐,只怕我今日連各位的鞋面都夠不上,又談何‘貴’字?”
谷六一愣,挽郎是低賤的勾當,尋常人發達之後想掩蓋過去還來不及,誰會自曝其短?
Advertisement
可聽他言語誠懇,不拿架子,谷六又半信半疑:
“你真是挽郎?唱兩句我聽聽?”
這話多帶著輕挑。胤奚沉穩地回視他:
“唱給死人的,六哥敢聽嗎?”
左右神一怒,谷六若有所思地按住手下人,聽胤奚又道:“在下知道苦出過的是什麽日子。說起來,我還羨慕像貴宗這般靠山吃水,無拘無束,可不快哉?又何必為人驅使,不由己,惹禍上呢?”
谷六聽到這試探言語,眼珠輕轉,忽哼笑道:“你若果然會唱挽,正好莊子上辦喪事,不妨請郎君去一趟,我谷六出錢請你引靈,就當抵了賭債;若你不會,有意蒙騙哥幾個,今天就別想出這個門了。”
這提議出乎胤奚意料之外。
他想:莫非谷六口中的喪事,就是那幾名員……可浮玉山又何必用這種方法挑釁他們?
他站起,不自覺清肅了眉宇:“據我所知,送靈皆在清早,此刻,時辰不合吧?”
谷六也收起玩味之,深惻惻地盯著他:“好死好葬,至于橫死的,也就顧及不了那麽多了。”
胤奚心中輕沉,忽然有種直覺,對方是想帶他去看些什麽。
“某樂意奉陪。”
·
“權先生的意思是,浮玉山封氏常年與吳興四郡的士族暗中來往,所以這員失蹤案,多半和浮玉山不開幹系?”
另一邊,賀寶姿正與山越帥權達雅打探消息。
權達雅手下掌管著大幾百人的浮浪之民,這夥人既不上稅也無戶籍,聚在太湖一帶的山泊間自由活。因信服阮厚雄,他才答應來見人,聞言忙撇清:
“姑娘別套我,我只告訴你們關于浮玉山我所知道的況,別的一概不論。”
他言語謹慎,賀寶姿也不強人所難,換了個口吻:“權先生是當地豪傑,我家大人初來乍到,多虧先生慷慨解言。我家大人還想借貴宗的名頭用一用,不知是否方便?”
Advertisement
權達雅灌了口茶,嚼著碗底的茶葉子尋思了一陣,笑道:“只要不是讓我真的出人出力,名頭而已,隨閣下尊主取用。”
他不敢正面和浮玉山,卻也知從金陵來的京,不是好惹的主兒。
·
出鎮十餘裏,胤奚隨谷六來到一村落。
時近晌午,野無炊煙,烏群落在枯枝上,之不祥。
一片荒寂中,田埂旁的一間茅屋前突兀飄出一抹刺眼的白,胤奚看出那是一座簡易的喪棚。
“兩口子,吃耗子藥沒的。”
谷六面無表地朝棚子裏那披著蓑麻的小兒努努,“就剩下這麽個娃娃,還不知道過不過得去今年冬天。
“這才是第一家,後頭還有呢。”
胤奚皺眉問:“為何如此?”
“為何?”谷六睨眼冷笑,“皇帝老爺派了欽差來清田,明面兒上是給這些土裏刨食的人優待,可哪個穿綢帶玉的士紳老爺願意割讓自家産業,就來搶占這些窮苦人的田,農戶被得沒有活路,可不只能投井喝藥了!你是京中來的,看見了嗎,這清田策究竟鼓了誰的腰包?”
胤奚神沉得更深,這和他之前設想的有些不一樣。
谷六是浮玉山的人,他門路帶他來此,說明這個村落也是歸浮玉山管轄。若浮玉山當真與三吳世家關系融洽,又或說沆瀣一氣,他們怎麽會護不住下頭的附屬?
除非——是那些在儉田之列的世家用這種抄掠的方式,來威攝封氏宗部,令其扣朝廷命,抱團走前來清田的欽差。
那麽谷六帶他來,難道是想晦地告訴他,他們不是自願與朝廷為敵?
心思萬轉下,胤奚轉頭看著谷六:“若政策真有誤,那些被‘山匪’劫走的清田吏死有餘辜——可真的是嗎?”
Advertisement
這些出不高、卻頂著得罪士族的力來到吳地的小吏,正是郎為了避免士族暗地弄虛作假,欺百姓,才一個個選才提拔,委派過來的。
“若是這些吏還活著,”胤奚盯著谷六的神試探,“也許事尚有轉機。”
谷六猶豫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麽,又仿佛有些忌憚,最終只道:“啰嗦什麽,不是說會唱挽歌嗎?”
胤奚不再多言,正冠整,走到那座喪棚裏。
那個跪在靈前低頭啜泣的孩子,與他失怙時差不多年紀,胤奚蹲下輕聲與孩子說了幾句,取來香燭,開始招魂唱挽。
他嗓子一開,直接讓谷六睜大眼睛。
一把婉轉低幽的歌,驚飛枝頭寒,清哀不傷,又極有韻味,這還真是個行家!
胤奚一共沿著村廓走了四家,越看到後來,眼底的漆寒越不見底。
鄉裏人信奉狐仙兒,開始時鄉親們看見這個條頎長的俊郎君,覺得他上有仙氣兒,都敬畏著不敢靠近。待一曲挽歌終了,亡者的親屬又無一不被這清婉悠長的聲音,拭淚上前行禮拜謝。
停靈過後,鄉人們自發湊出了一桌簡陋席面,作為答謝。
胤奚看見桌上的酒壇,婉言謝絕:“舉手之勞,不必客氣。”
他喝酒誤事,急著想把所見所聞回去報給郎,谷六過來,嘆了一聲:“之前是我眼拙了,朋友別見怪。鄉下人沒什麽拿得出手的,待客的道理還懂得。你忙了半日,不喝杯水酒再走說不過去。”
他的口吻比先前和不,看來人不管份高低,都是佩服有真本事的人。
胤奚此來就是為了套關系,聞言不聲地瞟了眼酒碗,也不再推辭,趁熱打鐵與谷六幹了一碗。
“六哥,什麽時候讓我見見上頭的當家啊?”
谷六松口道:“好說,好說。”
胤奚心神略定,下肚的農家土酒也開始在胃海灼燒。他酒氣上臉,笑得佻達:“那賭賬抵了,我的工錢給結一下?”
時機正好,放下段打些無傷大雅的小算盤,更容易拉近彼此的關系。
谷六一樂,這人賭也賭得,喝也喝得,還開得起玩笑,真是有幾分意思,果然從邊的小兄弟那裏要來一袋錢,給胤奚。
“那便說好了,明日老地方,我為你引見我大哥!”
離開村子,胤奚不正形的神一掃而空,他斂起的眼鋒含著峻利,撐著搖晃的形,迅速對乙生吩咐:“給我醒酒石,你來駕車,速回阮家。”
他知道自己的病,外出時為免誤事,常備醒酒藥在上。
乙生忙從腰囊中取出一塊醒酒石,胤奚含在舌底下,了把被酒暈染紅的眼皮子,形逸上了馬車。
醒酒石的作用有限,一路回到城裏,進府門時,胤奚的眼神已經行將渙散。
但他心裏始終提著一線念頭:不能醉過去,要醉,也得等向郎稟告完事,不能誤的事。
顧不上換沐浴,他卻還記得用艾草拍去晦氣,路過西院的水井時,又掬冷水了把臉,這才進屋。
謝瀾安正等著他。
賀寶姿先胤奚回來,回報權達雅已經點頭同意了借名行事。舅父那邊,也傳回消息,已向幾大士族的宗主去帖,就約在明日悠然樓上。
胤奚剛進門,謝瀾安向那輕搖淺曳的影瞥去一眼,就看了出來,“喝酒了?”
“嗯。”胤奚褪了靴履,腳步無聲,走近了,額角的發還在往下滴水。
打的長睫黑得深翠,羽一般。
他上不好,像有一船水在腦子裏攪,越攪越渾,抓清醒的功夫將和谷六打道的過程說了一遍。
“我以為封氏和吳郡士族……”末了,胤奚舌頭不利索地打結,“未必就是一條心,今日他們讓我看見那一幕,也許便是在試探……試探……”
“試探我,是否真有撬本地士族利益的決心。”
謝瀾安盯著那張緋氣橫生的臉,喚人熬些醒酒湯送來。
同時撚指思量,這些山越宗部畢竟在江南紮,即便不滿士族欺淩,也不敢輕易與之撕破臉皮,除非,他們能得到朝廷的支持。
但他們本又介乎于流民與匪兵之間,多年來不朝天子,他們怕朝廷秋後算賬剿匪,朝廷也怕這麽龐雜的團不好管控,雙方間還于微妙的試探階段。
不過能打開一道口子就是好事。謝瀾安拿扇柄逗胤奚的下,“喝了多,還行不行?”
一個嘗口米酒都能倒的人撐到這會兒,也是難為他。
“行。”胤奚低頭蹭了下,話音未落,單膝一跪了下去。
口裏還喃喃,“我行……”
謝瀾安已經見怪不怪,低頭睥視著嫣紅,眨眼遲緩的小郎君,扇面有一下沒一下在他頸側的雪白上流連。
“對方可有關于萬斯春他們還活著的口風?”
胤奚,只覺舌更躁,遲鈍地想了一會兒,迷迷眼波含又純:“沒有……不過他答應引我見上面的管事……”
“娘子,醒酒湯熬好了。”
這時,一個小婢端著醒酒湯送進來。
看清屋一站一跪的景象,小婢眼皮驚得一跳,連忙低頭,放下後退了出去。
正好謝瀾安也問完了,胤奚帶回的進展已經超出的預期,指了指還冒著熱氣的湯盞,“事辦得不錯,去喝了,回房好好睡一覺。”
“什麽臭東西,”胤奚含蓄地皺皺眉,“我不要它。”
謝瀾安眉梢輕揚,好麽,這是徹底迷糊了。
“你香,”腹誹,鼻子又嗅到一點混著艾草的春花香氣,仿佛每次喝醉了,他上都浮出這若有似無的味兒,狐疑嘀咕:“莫不是背地還往上抹香吧?”
紆尊拉了胤奚一把,人沒起來,反倒耍賴似地歪在柞木地板上,“要你喂我。”
謝瀾安瞇眸:“胤衰奴。”
被警告的胤奚老實了一會兒,又窸窸窣窣地探手懷一陣。
最終給他出一只錢袋,臉上就出滿足來,拉過謝瀾安的手心,輕輕放上去。
低噥:“我掙的工錢,給娘子。”
謝瀾安輕怔,低頭看著那只織線老舊卻頗有分量的布袋。
尋常百姓家,求的是食生計,養家糊口。有那憨厚漢子,在外辛苦一日,回到家會把掙來的錢悉數給婆娘。
胤奚從小耳濡目染,他爹對他娘便是這樣。
是在廟堂心計公卿爭衡之外,能讓人口氣的,煙火溫。
謝瀾安斂著眼皮,無聲半晌,拿指尖撥了撥他的臉蛋。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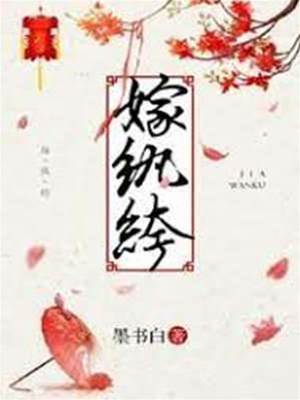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