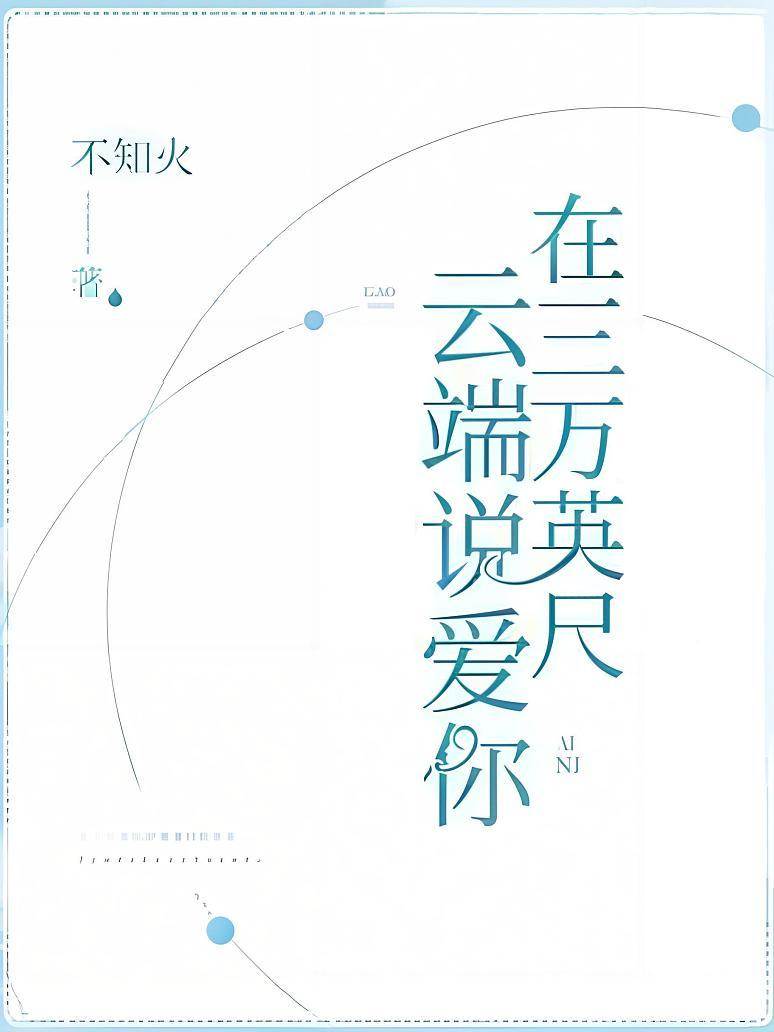《拋夫棄子離婚后,她驚艷了世界》 第226章 區區一條狗,他可真敢想啊!
墓園外。
林道上停著兩輛車,其中一輛橘的車,車門大開,蘇云眠一臉灰白捧著保溫杯,小口抿著溫水,緩了好一陣才瞪向站在車門外的郎年,“不是,你大半夜跑來這嚇我做什麼!”
知不知道人嚇人嚇死人啊!
有病?
郎年面上沒什麼緒,語氣卻帶了點無奈,“夫人,是您大半夜突然出門,又是來這里,我擔心有事才跟來,沒想到......”
“別我夫人!”
“......蘇董。”
“你在監視我?跟蹤我?”蘇云眠后知后覺到不對,語氣也冷了下來。
“我需要時刻關注夫人的安全。”郎年理所當然道:“而且您從老太爺那里出去,我不可能不知道。”
安全安全!
又是安全!
每次都是這麼一個說法,蘇云眠聽得發膩,這兩天又是反復刺激,終于是忍無可忍,索直言:“那也不是你監視我的借口,別再跟著我,我自己請保鏢!”
“蘇董。”郎年語氣仍是平穩,“正是多事之時,外面的人目前都不可信。”
“好,我信你們孟家。”蘇云眠沉下臉,“孟家能保護人的總歸不是只有你一人。”
“我更妥當。”
“可我就是不想要你!”
夜風吹拂,林道兩邊枝椏輕晃,樹葉沙沙聲在靜謐夜下尤為清晰,兩人都未再在言語,車車外、一坐一立,對視許久不言,反復刺激下蘇云眠終是發了火。
郎年沉默不語。
他清楚知道蘇云眠是恨他的,自從在八年前那一晚混,他聽命把鎖進房間,對人的哭嚎求救置若罔聞那一刻起,就預見到的事,會一直恨他。
這一年忍耐,終是發了。
可是不行。
“蘇董,不管您再怎樣厭恨我,怎麼對我都可以,但在這件事上希您不要任。”郎年平靜道:“您的安全比一切都重要,我不能辜負先生所托。”
Advertisement
“他已經死了!死了!”蘇云眠怒聲道:“而我不需要你!”
郎年眉峰略微一下,好一會,他才微微側頭目落在遠黑暗,發出不帶一緒的聲音,“保護您,是我的責任。”
也是他欠的。
哪怕并不想要。
蘇云眠一口怒火卡在口,怒瞪著面前的男人,不知怎麼地腦子里就突兀冒出一個想法......真是孟梁景的好狗,人都不在了還這麼忠心!
意識到自己在想什麼突然就愣住了,然后是巨大的挫敗無力......狗?
曾幾何時,
還看不慣孟梁景不把人當人的病——且不論旁的,數年忠心陪伴只當人家是條可以隨時拋棄犧牲的好狗。可現在,竟也會冒出這樣的想法,突然就有點崩潰,抱著保溫杯失聲無言......這是,被影響了還是過于憤怒?
見人沉默不語,夜風又涼,出來的又倉促沒帶厚,郎年猶豫了一下下西服外套披過去,“蘇董,夜里涼,還是先回去吧。”
帶著暖意的服落上,蘇云眠驟然回神,猛地把外套掃落,子也往車里退了些。
許久,
收拾齊整心,卻也沒了刁難的心,淡漠道:“只要科西奧的事解決,你是不是就能滾蛋?”
“......嗯。”
“還要多久?”
“境外是他的主場,只要他能境,就是我們的主場了。”郎年道:“但目前他還沒有要境的意向。”
“那我要等多久?”
“不會太久,他會來的,且那一天不會很久。”郎年語氣肯定。
在國對科西奧最大的威脅阻礙已經死亡,即便是他再謹慎小心,一年也足夠他放下戒心了境來捕獵了,且他也不一定有那個耐心再等了......只要等他境,獵和獵人是誰就不一定了。
Advertisement
“不需要再等一年吧?”蘇云眠冷笑。
“不會。”
行,那還能再忍忍,反正這一年也熬過去了。
不想在和郎年廢話,這會兒也不想看到他,蘇云眠索下車自己開另一輛車回去,卻不想站在車外的男人并未讓開,直接就撞了上去,臉也跟著黑了。
“讓開!”
“蘇董,我送你回去。”郎年淡淡道:“還有一件事,如果蘇董實在厭恨我,想要怎麼報復怎麼對我都可以,郎年都著,也是我應該的。”
“?”
蘇云眠默默無言,想罵卻又覺得沒勁,這人都沒脾氣的,再怎麼罵也不會生氣,可到底心里堵的慌,最后也只憤憤罵了一句,“有病。”
也懶得再起爭執,砰地把門關上,順便把落在車座上還留有余溫的西服外套砸去了前座。
......
本來就連軸轉幾天了,又連著兩天都沒休息好,蘇云眠索給自己放了一天假,正好去赴林青山的約。
“這樣沒關系嗎?”
驅車到孟氏集團樓下,接了蘇云眠上車,路上林青山瞟了眼后視鏡里,一直遠遠綴在后面郎年的車,忍不住出聲詢問,雖然知道孟家在保護蘇云眠,他多還是沒習慣。
蘇云眠無奈,“就這樣吧,明著來總比跟著強。”
林青山:“......”
“我們要去哪里?吃什麼?”蘇云眠還惦記著林青山提到的食,他廚藝好在吃上又很能花心思,探到的店一定不差,之前大學時也總是他找到的食店更多。
簡直就是食雷達。
“保。”林青山笑道。
“又賣關子。”蘇云眠嘟囔一句,頗為放松地靠在副駕駛上,緩緩閉上眼,“我能稍稍補個覺嗎?”
“沒休息好嗎?”
林青山余瞥見眼角青黑。
Advertisement
“......嗯。”小小回應一聲,蘇云眠人已經昏昏睡了。
余瞧見人毫無防備的睡,輕嗅車漸漸彌散開的茉莉花香,林青山畔笑意不由深了些,眉宇也放松綻開,在等紅綠燈時,隨手把下的外套輕輕搭在人上,將座椅往后放倒些,再起速也放慢了些。
這一小睡睡的很舒服。
蘇云眠迷迷糊糊睜眼,被窗外投來的照得晃眼,抬手擋了會才意識到車不知何時已經停下來了。
“不再睡一會?”
駕駛座上,林青山側笑問。
“怎麼沒我?”
蘇云眠忙起,蓋在上的白風也落下來,鼻尖還能嗅到淡淡植清香,耳也順勢染了些薄紅。
“看你睡的香就沒你。”林青山又問:“沒休息好,是力大還是怎麼了?”
“做噩夢。”隨口回應著,盯向窗外靜謐小巷,“這是哪里?我們到了?怎麼沒看到飯店?”
“還沒到。”林青山稍稍靠近些,將上安全帶卸開,笑道:“接下來還要走一段胡同巷子,開車不方便。”
“哦哦哦。”
蘇云眠拉開車門下了車。
一下車,空中飄的絮就浮而來,巷口還有一刻開滿細小花朵的花樹,再往里是窄小不規則的小巷,周圍都是高低參差不齊的獨棟小樓。
是京市常見的胡同巷。
林青山下車時,隨意瞥了眼隔了一條街的巷口停著的車,郎年正斜靠在車門上,淡漠來。
他笑了一下干脆無視,去喊花樹下仰頭張的蘇云眠,“蘇蘇,走了,還在里面。”
“來了。”
......
胡同靜謐。
灰白襯衫、手臂橫抬搭著一件白風的男人,同側難得穿一件休閑針織長的人并肩而行,時不時有談笑聲傳來。
Advertisement
郎年默默跟在后方不遠。
跟了沒一會,似是想起什麼,他出手機對著前方隨手又練地拍了一張照片,卻在按快門的瞬間,正與人說笑的林青山突然微微側頭,明鏡片后的眸子銳利來。
郎年坦然按下快門,面上始終沒什麼表,似并不覺得這樣有什麼問題。
林青山眼睛微微瞇起。
這人......
“青山?”
見剛剛還在同說話的男人突然停步,蘇云眠也停下,順著男人視線往后看去,繼而沉默。
跟的是真啊。
“抱歉。”蘇云眠無奈道。
郎年這人沒脾氣又死腦筋,除了把他從邊調離這件事,其它的事和話又全都聽,也沒辦法。
只能等科西奧的事解決。
“沒事。”
林青山突然手,輕輕落在蘇云眠肩上,引導著轉繼續往前走,余卻一直著后方,察覺到后方人微微停頓的作后,了然一笑,眼底寒四溢。
原來如此。
區區一條狗,他可真敢想啊。
在蘇云眠到不適推開之前,林青山就微笑著先松開了手,繼續剛剛的話題,“你還沒說呢,做了什麼噩夢?睡都睡不好。”
“沒什麼,應該是工作力太大的緣故。”不想在這種時候難得放松的時刻提孟梁景,蘇云眠隨意搪塞了一句。
“那今天就好好放松放松。”
聽出有問題,林青山也不追問,兩人又聊了些國外的風景食,卻在這時男人陡然話鋒一轉,“蘇蘇,那個郎年,你覺得如何?”
“啊?”蘇云眠懵了一下。
突然提他做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43 章

春色難馴
江城時家弄丟的小女兒終于回來了。 整個時家,她要星星還強塞月亮。 —————— 二中開學,時年攬著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妹妹招搖過市。 眾人看著那個被時年夾在咯吱窩里,眉眼如春的小姑娘,紛紛誤會,“小嫂子絕了,絕了啊。” “想什麼呢?!”時年忿忿,“這是我妹!” 時·暴躁大佬·年,轉頭笑成智障,“歲歲,叫哥。” 此時,一位時年的死對頭,江·清貧(?)學神·頂級神顏·骨頭拳頭一起硬·馴,恰巧路過—— 椿歲哥字喊了一半,就對著江馴甜甜一聲,“哥哥!” 江馴看著這對兄妹,鳳眼微掀,漠然一瞥,走了。 時·萬年老二·考試總被壓一頭·年:“???”啊啊啊啊你他媽什麼態度?!所以為什麼你連哥都比我多一個字?! —————— 時年曾經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江馴踩在腳下,讓那個硬骨頭心甘情愿叫他一聲“哥”。 直到看見死對頭把他親妹子摁在墻角邊(沒親,絕對沒親)。 時年真的怒了,“你他媽壓.我就算了,還想壓.我妹??!!” 江馴護著身前的椿歲,偏頭懶聲,“哥。” 椿歲:“…………” 時年:“???”啊啊啊啊別他媽叫我哥我沒你這種妹夫!! —————— 小劇場: 椿歲:“為什麼裝不認識?” 江馴:“怕你喜歡我啊。” 椿歲嘁笑,“那為什麼又不裝了啊?” 春夜的風,吹來輕碎花香。 江馴仰頭,看著枝椏上晃腿輕笑的少女,低聲笑喃:“因為……我喜歡你啊。” #你是春色無邊,是難馴的執念# 冷漠美強慘X白甜小太陽 一句話簡介:我成了真千金你就不認識我了? 1V1,HE,雙初戀。不太正經的治愈小甜文。
16.3萬字8.18 6106 -
完結1181 章
余生悲歡皆為你
婚前,她當他是盲人;婚后,方知他是“狼人”。 * “你娶我吧,婚后我會對你忠誠,你要保我不死。”走投無路,喬玖笙找上了傳聞中患有眼疾、不近美|色的方俞生。 他空洞雙眸毫無波瀾,卻道:“好。” 一夜之間,喬玖笙榮升方家大少奶奶,風光無限。 * 婚前他對她說:“不要因為我是盲人看不見,你就敢明目張膽的偷看我。” 婚禮當晚,他對她說:“你大可不必穿得像只熊,我這人不近美|色。” 婚后半年,只因她多看了一眼某男性,此后,她電腦手機床頭柜辦公桌錢包夾里,全都是方先生的自拍照。 且看男主如何在打臉大道上,越奔越遠。
216.9萬字8 1233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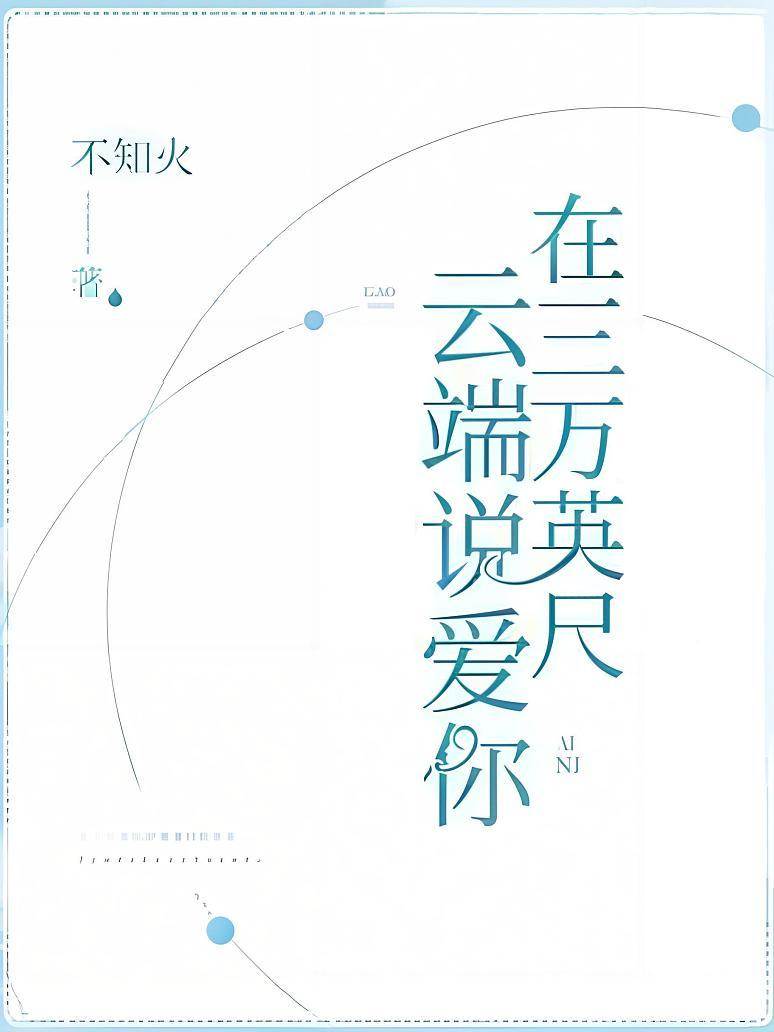
在三萬英尺云端說愛你
高考過后,楊斯堯表白周月年,兩人在一起,但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和楊母從中阻撓,周月年和楊斯堯憤而分手。分手之后,兩人還惦記著對方,幾番尋覓,終于重新在一起。周月年飛機故障,卻因為楊斯堯研制的新型起落架得以保全生命,兩人一同站在表彰臺上,共同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18.2萬字8 3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