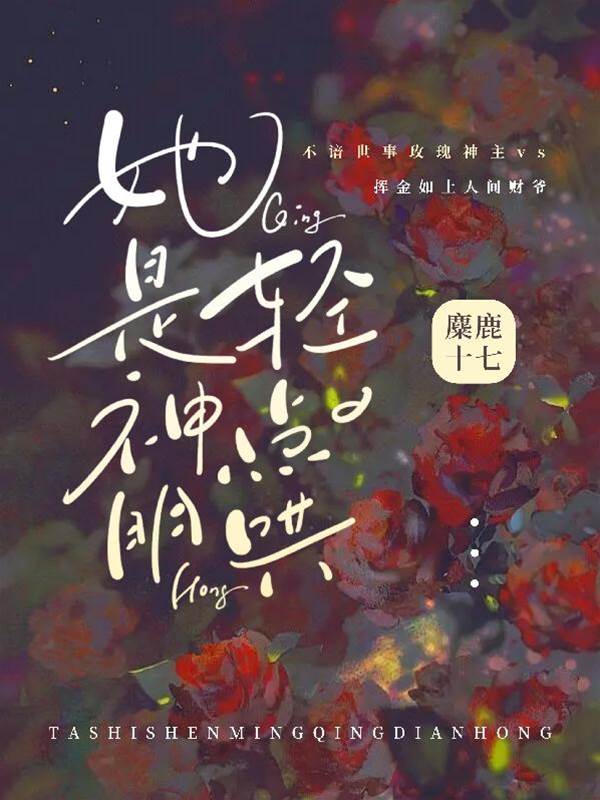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炙吻》 第69章
他一米九的個子,一百七十斤的重,渾然一座俊偉巍峨的山,如此無遮無攔在上,著實堪比泰山頂。
許芳菲雙頰紅如焰,被鄭西野沉重高大的軀在底下,強烈的男氣息侵占。就像只被覓食野俘獲到手的小獵,掙不又躲不開,焦心得甚至想罵人。
好不容易將右手擡高抵住他額頭,溫度高到燙手。
瞪大了眼睛,急切道:“天哪,你的溫度太高了,一定是在發燒。家裏有沒有退燒藥?”
“嗯。”鄭西野眼睛閉得死死的,修長雙臂擁懷裏的一小只,應得十分敷衍。
懷裏又問:“那你吃了嗎?”
他回:“沒。”
“有藥為什麽不吃,你當自己是鐵打的嗎。”小姑娘語氣焦急又不滿,兩只細細的胳膊不斷往他上推搡,“快點起開,藥在哪兒,我去幫你拿。”
鄭西野眉心擰起的結越來越。
天知道,高燒中的鄭西野頭痛裂,渾也酸脹乏力,眩暈讓他五的敏銳度大幅降低,只剩下最基礎的本能。本能地警覺,本能地自衛,本能地殺伐。
剛才察覺到有人靠近,多年習使然,他條件反便把人擒住。直到聽見一聲聲甜悉的嗓音,才反應過來,這個突然不要命闖進自個兒領地的小,是他的兔崽子。
鄭西野渾不舒服到極點,就想抱著這小家夥當抱枕,讓自己好好睡一覺。
可是,這個磨人的小抱枕一點兒不乖。
小叭叭叭說個不停,鬧騰得像個小喇叭,小手小腳在他懷裏東搗鼓西,過來過去,折磨得鄭西野快抓狂。
如果不是實在提不起力氣,他簡直想往這妮子的小上狠甩幾掌。
Advertisement
鄭西野惱火得很,氣得牙。
而此時,小崽子居然還在喋喋不休,碎碎念道:“怎麽這麽燙,你量過溫度了嗎?溫計在哪兒?我覺你肯定燒到了三十九度以上……昨天不是都還好好的嗎,為什麽會突然發燒?”
鄭西野:我他媽日了。
他眼也不睜,憑嗅覺湊近耳邊,咬著牙虛弱威脅:“安靜。信不信我親死你。”
許芳菲:“。”
如果是平時,許芳菲肯定又得想捂臉了。可這個節骨眼兒上,他發著高燒氣若游,所有的害心理都被濃濃的擔憂替代。
“我……我沒辦法安靜啊。”急得繼續推他,試圖將這副沉甸甸又滾燙的推開,“你燒得跟個火球一樣。”
這一回,鄭西野終于妥協。
他暴躁地低咒了聲,用盡所剩無幾的力氣往側一翻,四肢放松,解除了對懷中姑娘的桎梏。
許芳菲得以,連忙從床上爬起來,跪坐在男人邊,揪心地在他臉上打量。
視線中,鄭西野眼眸閉合,一只長隨意屈起,踩在床上,左邊胳膊略微擡高,搭上他潔飽滿的前額,幾縷碎發垂落在額前,整個人看上去野、淩,而又脆弱。
小心地彎腰近他,聲問:“退燒藥放在哪裏?”
鄭西野薄輕微開合兩下,說了兩個字。
許芳菲耳朵湊近他瓣邊上,費勁地聽,好幾秒才辨別出,他說的是“藥箱”。
可是……
可是,藥箱又在哪裏啊喂!
許芳菲囧了,本來還想再追問一下鄭西野,他家藥箱的存放位置。可還沒發出第一個字音,卻先一步聽見,空氣裏,男人渾濁急促的呼吸聲,在逐漸趨于平緩與規律。
許芳菲眨了眨眼。
睡著了?
……好吧。許芳菲心疼地皺起眉。
Advertisement
看他很痛苦的樣子,難得能睡著,還是不要再吵醒他。
如是思索著,著腳小心翼翼下了床,四下搜尋一番,找到剛才不小心踢飛的大拖鞋,穿上。接著便到客廳裏,打開大燈,翻找起來。
值得慶幸的是,鄭西野家裏整潔如新,偌大的屋子裏沒有堆放任何雜,要找東西也很容易。
沒幾分鐘,許芳菲便在客廳酒櫃的頂部發現了一個純白收納箱。
定制的酒櫃家,顯然都是按照適應房屋主人高的高度來制作。許芳菲由此判斷,鄭西野的父母都是高個子。
也是。
他個子都那麽高呢,看傳基因這一項,兩位長輩也不會矮。
心裏胡七八糟地琢磨著,許芳菲扶著櫃沿踮起腳尖,夠了夠,沒夠著。左右一瞧,邊上正好是餐桌椅,便隨手拖來一把,踩上去雙手齊用,終于將白收納箱取下。
打開一瞧,裏頭果然裝著各類藥品。
許芳菲仔細翻找著。
鄭西野的藥箱,藥品類別相對單一,大部分都是理外傷用的品。紗布、醫用膠帶、碘伏、消毒酒,另外占據大頭的,則是胃藥,奧拉唑腸溶膠囊、碳酸鎂鋁咀嚼片、溫胃舒顆粒……
廢了好一會兒功夫,許芳菲才從藥箱的最底部找到一盒布芬。
“!”
大眼一亮,連忙掰下一粒退燒藥,沖進廚房倒了杯溫水,再將水和藥一并拿著,小跑送進臥室。
鄭西野的臥房燈是純白,冷調的線,相對刺眼。許芳菲沒有立刻摁頂燈開關,而是先將水杯和藥丸放在床頭櫃上,擰開了床頭的閱讀燈。
和的暖橘燈亮起,依稀投落在床上男人的臉上。
許芳菲垂眸看著他。
忽然發現,病中的鄭西野,眼眸閉合眉目恬靜,看著有一種零落的破碎。這令許芳菲頗有幾分意外。
Advertisement
印象中,他總是彪悍野蠻得像頭雄獅,撒起野來能氣死人,不講半點道理。可此時的他卻又如此憔悴,憔悴得惹人憐惜,尤其那副深邃如畫的眉眼,愈為“破碎”二字添了幾筆神韻。
難怪一直覺得這是個“漂亮的混蛋”。
他的五是真的很,英秀的眉,濃的睫,琉璃般致易碎,只是平時那副眼神的威勢太過淩厲,才中和了這種。
心念微,許芳菲忍不住出指尖,輕輕過他的臉頰,聲喚道:“阿野?”
一聲喊完,人沒醒。
許芳菲便傾得更近,幾乎把近他圓潤的耳垂,低低說:“我找到藥了,你起來把藥吃了再繼續睡,好不好?”
須臾景,男人的眼簾終于掀開。
只一秒,破碎的從這張臉上瓦解殆盡。鄭西野黑眸微赤,眼神還是有些虛弱,但并未掩蓋住其中的冷戾與銳利。
鄭西野目落在許芳菲臉上。
小姑娘白皙的頰,與他僅咫尺之隔,見他醒來,那雙晶亮的眸子裏泛出喜。
忙顛顛從床頭櫃上拿起一顆白藥丸,周到地送到他邊,如同照顧三歲小孩子一般,聲:“張。啊。”
鄭西野直勾勾盯著許芳菲,很聽話,緩慢開啓上下瓣。
雪白的指尖攥著小藥丸,喂進來。
他神平靜,舌尖卻若有似無,勾了下膩的指腹。
“……”
許芳菲察覺,臉蛋瞬間又飛上兩朵小紅雲。嗖一下把手回來,沒忍住,豎起手掌就打了他一下,低斥:“生著病給我老實點,別我揍你。”
一聽這話,鄭西野咬著藥丸直接悶笑出聲,淡淡道:“真不知道你哪兒來的自信。”
“平時我打不過你,你都這樣了,難道我還打不過你?別太小瞧我。”
Advertisement
許芳菲小聲吐槽兩句。繼而雙手端起一旁的溫水,把杯子送到他面前,怕燙到他,還嘟起吧呼呼了兩下,說:“來,喝水。”
鄭西野躺著,紋不,盯著挑了下眉,問:“你不扶我起來嗎。”
許芳菲有點兒納悶兒:“你都有力氣調戲我了,沒力氣自己坐起來嗎?”
鄭西野的面容英俊清冷:“我沒有。”
鄭西野的語氣鎮定自若:“崽崽。我頭暈暈,要你扶扶。”
“……”許芳菲手一,被這驚悚的疊詞雷得差點兒把溫水潑他臉上。
幾秒後,一臉黑線地將杯子重新放下,傾上前,彎下腰,胳膊從他後頸穿過去,使出吃的力氣力往上一托,將他的腦袋置自己的頸窩位置。
許芳菲骨架小胳膊也細,單靠手臂力量本扶不起人高馬大的鄭西野,只能借用肩頸、調整個上半的重量,把他往起頂。
不料就在這時,灼灼呼吸卻噴過來。
有意無意,吹拂過細膩敏的肩頸與小耳朵。
許芳菲臉紅得像顆番茄,作一卡,眼睛往下瞪他:“喂。你再不老實,我真的要扁你了。”
“我怎麽了。”鄭西野整張臉都埋在香的頸窩,淡聲問了句。
許芳菲窘迫支吾:“你不許往我脖子裏吹氣。”
鄭西野聞言低嗤,話也回得漫不經心的:“小朋友,麻煩講點理。你總不能不讓我氣兒吧。”
“……”好吧。
一句話噎得許芳菲無言以對。笨,反應也不算快,當然說不過這個混球,只好老實地繼續使力,把他扶起來。
好不容易攙著鄭西野起。
許芳菲雙臂抱住他的脖子,箍住他往後挪了挪,然後又拿起一塊枕頭墊在床頭,帶著他輕靠上去。
誰知,就轉拿杯水的功夫,那男人竟又黏了過來。悍的一腱子,這會兒弱不風得跟林黛玉似的,直往上倒。那副滾燙的臉頰也像是糊了膠水,完全粘在了頸窩裏,半刻不離。
許芳菲臉越來越紅,一手端杯子,另一只手還得騰出來招架他,不住囧囧道:“教導員,你能不能坐好。”
話音剛落,鄭西野終于低笑出聲,善心大發,不逗這小姑娘了,徑直接過水杯,仰脖子一飲而盡。
三十幾度的水對比四十度的溫,出宜人涼爽,水流沿著食道滾落,帶走些許燥氣。
鄭西野閉眼緩了下,擡手眉心。
許芳菲還是擔心,趴在床邊目不轉睛地著他,小聲試探:“怎麽樣?現在有沒有舒服一點?”
“嗯。”鄭西野點了下頭。
“好些了就好。”
聽他這麽說,許芳菲揪的心總算松懈幾分。把空掉的水杯從他手裏拿走,放在一旁,又轉走進洗手間,接了盆溫水,再往水裏扔了一塊幹淨巾,折返回臥室。
鄭西野眼底的紅已褪去些許。
他擡眸,看著端著個盆的小姑娘,眼神中出對行為的一困。
只見崽子把水盆往邊上一放,接著便捋高袖子,低下頭,認認真真將巾撈起來,又認認真真地擰幹,最後認認真真地疊好,敷在他的額頭上。
鄭西野愣住。
水汽蒸發帶走熱量。
涼悠悠的,很舒服。
崽子小小一只,蹲在他跟前,一只小爪子把巾摁在他腦袋上,另一只手托著腮。停留幾秒後,問他:“這樣是不是覺得更好一些?”
鄭西野凝視著,黑眸裏閃著星河似的,輕輕點頭。
“理降溫最有用了。小時候我發燒,我媽都是這樣照顧我。”
見他神狀態明顯好轉,許芳菲喜悅的緒抑制不住,角不斷往上翹。
須臾,將巾從他額頭取下,放回水裏重新浸,擰幹,然後攥在手裏,聲指揮:“胳膊擡起來。”
鄭西野懶洋洋平舉兩只長臂,依言照做。
許芳菲拿著巾近他些許。手剛舉起來,又有點猶豫,紅著臉輕聲加了句解釋:“人管主要分布在頭部、腋下,還有大側。我現在要幫你……拭腋下。”
鄭西野微揚眉,看的目直勾勾的,灼灼如烈日,折出毫不加掩飾的興味。
他說:“你想哪兒都行,不用跟我提前知會。”
許芳菲臉蛋燙燙的,道:“是你的,我當然應該跟你說一聲。”
鄭西野語調平靜自若,回:“但我是你的。”
許芳菲:“……”
許芳菲服了。睜大含帶慍的眸子,低聲:“你才真的應該安靜一點。”
鄭西野勾了勾角,聽的話,閉。
許芳菲攥著巾湊得更近,瞬息之間,男人的各部位、各細節,無比清晰地展于眼前。
平實的理,因高燒而略微泛紅的皮,還有……許猙獰陳舊的傷痕。
因為張和,許芳菲指尖不控制地輕。
想起以前在學校,男孩堆裏總是有一怪怪的味兒,有時即使是洗完澡再集合,也能聞見。
但是很神奇,鄭西野上什麽異味都沒有。
即使這會兒已經湊近了他的咯吱窩,空氣裏彌漫的也只是他一貫的荷爾蒙氣息,幹爽清冽。
想到這裏,不好奇地眨了眨眼,口而出道:“教導員,為什麽你上的味道總是很好聞?”
鄭西野聞聲,明顯滯了下。
須臾,他黑眸注視著,道:“這是你第二次,說我上香。”
許芳菲面不解:“……我之前什麽時候還說過?”
鄭西野:“在奚海,你喝醉那次。”
“啊。”許芳菲狐疑地撓腦袋,冥思苦想須臾,發現那段記憶仍然是空白,什麽都想不起來。便搖搖頭,幹笑道:“我不記得了。”
話說完,那頭的男人停頓好幾秒,才遲疑地淡淡開口,問:“我上的味兒,是不是不太男人?”
這下子,換許芳菲愣住。
茫然地眨了眨眼睛:“什麽?”
鄭西野問:“你是不是不太喜歡。”
“怎麽會。”小崽子口而出,“哪個孩子會不喜歡幹淨又清清爽爽的男生。我最喜歡你上的味道,也最喜歡你了。”
這番話說完,整個屋子驟然一靜。
許芳菲後知後覺,反應過來自己把所有真心話全都和盤托出,頓時窘得低下頭,這顆腦袋火燒火燎,幾乎埋進口。
然後,下被兩修長的指輕輕住,溫卻不容違背地擡起。
許芳菲心口都起來。
頭頂傳來一個聲音,輕聲道:“崽崽,看著我。”
“……”許芳菲眼睫了,眸窘促地左右晃晃,好半晌才鼓起勇氣往上走,看向床上的男人。
鄭西野指腹著下,而後漫不經心上移寸許,又去的,力道和而曖昧地把玩。
鄭西野定定瞧著,道:“崽崽,再說一遍。”
許芳菲手掌心發熱,好像被他傳染得也發了燒,全都燥燥的。
:“說……什麽?”
“就是。”
男人另一只胳膊攬住的腰,輕輕一勾,便將整個人都摟進他懷裏。而後,薄潤的欺近,哄著:“剛才的最後一句。”
他上的味道被偏高的溫一炙,愈顯得濃烈,鑽進鼻腔掌控神經,熏得許芳菲腦子都有點暈乎了。
便如小八哥似的複述:“我說,我最喜歡你。”
“好乖。”
鄭西野面愉悅,輕輕在瓣上啄了口,正要撬開的齒切主題,不料,這崽子忽然呀了聲,驚道:“對了!你燒得這麽嚴重,是不是還沒吃晚飯?”
鄭西野:“。”
鄭西野:“嗯。”
“本來就病了,再不吃飯怎麽行,得補充力。”許芳菲滿腦子都被他還沒吃飯這一消息占據,也顧不上害不害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51 章

總裁聽我的
顏可欣單槍匹馬去找未婚夫尋歡作樂的證據卻沒想被吃干抹凈血本無歸反擊不成?那逃總可以了卻沒想這男人恬不知恥找上門,百般無賴的表示。“睡了我,還想就這麼跑了嗎?”
97.1萬字8 19077 -
完結242 章

冷少的逃跑嬌妻
在陸琪琪20歲生日那天,不小心誤睡了總裁,還將他當成了牛郎,隨后甩下100塊大洋離開。向來不注重感情的冷慕晨卻對陸琪琪香腸掛肚了5年。5年后,陸琪琪帶著天才可愛寶寶回國,再次偶遇了冷慕晨——“5年前,我讓你逃走了,這一次,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了的。”冷慕晨對著陸琪琪愣愣的說道。
56.9萬字8.14 28173 -
完結1094 章

南太太馬甲A爆了
父母從小雙亡,蘇清歡從小受盡各種寵愛,來到城市卻被誤以為是鄉下來的。姑姑是國際級別影后,干爹是世界首富。蘇清歡不僅在十五歲時就已經畢業修得雙學位,更是頂級神秘婚紗設計師Lily,世界第一賽車手,頂級黑客H。當蘇清歡遇上南家五個少爺,少爺們紛紛嗤之以鼻……直到蘇清歡馬甲一個個暴露,五位少爺對她從嫌棄分別轉變成了喜歡愛慕崇拜各種……
193.8萬字8 127400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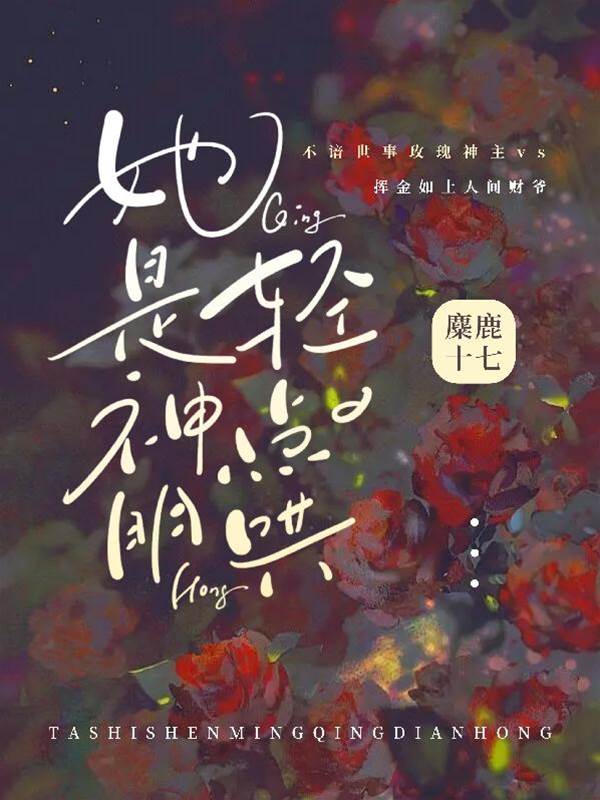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連載138 章

蓄意嬌養誘她入懷
【蓄謀已久+甜寵 + 曖昧拉扯 + 雙潔1V1 + 6歲年齡差】【人間水蜜桃x悶騷高嶺花】 南知做夢也沒想到,真假千金這種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狗血的是,她被下藥,把叫了12年的顧家小叔叔給睡了。 怎麼辦?跑路唄。 花光積蓄在暗網更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親手養大的水蜜桃,剛啃了一口,長腿跑了。 找她了三年的顧北期忍著怒氣,把她抵在車座角落,“睡了就跑,我算什麼?” 南知:“算…算你倒霉?” 顧北期:“這事兒怪我,教你那麼多,唯獨沒教過怎麼談戀愛。” 南知:“你自己都沒談過,怎麼教我?” 顧北期:“不如咱倆談,彼此學習,互相摸索。” - 顧家小三爺生性涼薄,親緣淺淡。 唯獨對那個跟自己侄子定了娃娃親的小姑娘不同。 他謀算多年,費盡心思,卻敵不過天意。 被家人找到的南知再次失蹤。 在她訂婚宴上,男人一步一句地乞求,“不是說再也不會離開我?懷了我的崽,怎麼能嫁別人。”
1.8萬字8 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