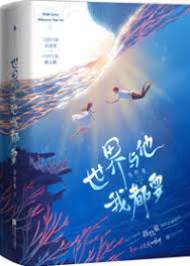《他的糖只給我吃》 第四章 第四顆糖
這頓晚餐是在祁家老宅里吃的,自從祁走后,祁爺爺就念舊的搬回了這里,說這里祁的氣息多,不愿意離開。
虞辭憂看著一路上千變萬化的景,的脖子一直朝著右邊都要僵了,但這樣也總比會不小心與祁景儒對視來的好。
兩人就像是各自心懷鬼胎,在算計著什麼。
車子一開到老宅,祁母就熱的拿著鍋鏟出來迎接了,眼的看著副駕駛的虞辭憂,先是上下略大量一番,得出一個評價:瘦了。
虞辭憂笑著回答說:“我們年輕人都是覺得瘦點好看。”
祁母不贊這話,小的時候的棗棗就跟個團子一樣,上去的的,可極了,如今多了幾分骨,雖然也好看,但畢竟老人家還是覺得胖一點有福氣。
祁爺爺聽到了靜也從樓上走下來,他拄著拐杖,笑呵呵的說道:“是不是棗棗回來了?”
虞辭憂聞言笑著上樓梯,老人似乎真的蒼老了很多,這些年忙著長大,總是著時間再過的快點,卻忘了老人也在日復一日的變老。
不知怎麼的,眼角有些發酸,這些小緒都落在了祁景儒的眼里,虞辭憂焦急的奔向祁爺爺那里,像是小時候一般親熱的將頭埋在老人前,撒著說道:“棗棗好想爺爺呀。”
老人也是眼眶一酸,自小就看著長大的孫,甚至在自己的心里虞辭憂的地位還要高過親孫子,他說道:“棗棗不哭,棗棗哭了爺爺也難。”
晚餐很快就一一擺上了餐桌,都是來自祁母的好手藝,祁家餐桌上的家規不嚴,沒有什麼食不言 寢不語的規矩,眾人都是其樂融融的坐在一起,大家都不停的給虞辭憂夾菜。
很快虞辭憂的碗里就疊起了一座小山,可憐兮兮的看了一眼祁景儒,自小到大吃飯都是這副景,只需要埋頭看著自己的碗就好了,不管是什麼菜大家都是第一個夾給。
Advertisement
正當祁母又加來一個扇貝時,祁景儒抬眸說道:“媽夠了啊,最后還不是落到我肚子里。”
虞辭憂食量小,碗里一大堆沒有過的菜全部都是到了祁景儒的碗里,第一是不浪費,第二就是好菜全在碗里。
祁母佯裝生氣瞪了祁景儒一眼,然后立馬笑臉相迎對著虞辭憂說道:“棗棗,你和景儒事什麼時候的事啊?”
“咳咳...咳咳”虞辭憂被一口菠菜嗆住了,臉通紅,雙手捂著口一臉痛苦的表,雖然知道祁阿姨是很直接的子,但是什麼鋪墊也沒有的單刀直也太可怕了吧。
祁父倒了一杯水遞給了祁景儒,祁景儒一邊拍著的背一遍給喂水,雖然話里多是責怪但是心疼的意味十足:“不是讓你每口都要多嚼幾下的嗎,吃東西這麼急?”
祁母滿意的看著眼前這樣,以前倆孩子這麼親也不覺得有什麼,畢竟棗棗是景儒從小看著長大的,對寵溺一點也就像是對待妹妹一樣,但是加上這層關系之后,兒子這麼做就是很上道了。
“棗棗啊,別害了,我們都知道了。”祁母眉弄眼,還以為虞辭憂這樣是在。
虞辭憂用手掩著臉,暗暗里憤恨的看著祁景儒,這人剛剛在車上就把謊給圓好了,編的有模有樣的,還十八歲就在一起,是一個等了整整三年的癡種。
當然虞辭憂可是只狡猾的小狐貍,提出了要求,要祁景儒公司新項目的合作機會,需要短時間在虞氏立足不借助點外頭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虞辭憂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準備一步一步往上爬,直到祁景儒答應了,才松開蹙著的眉,也順應了祁景儒編的謊話。
餐桌上,虞辭憂緩過來后,小聲說道:“對不起,瞞了大家這麼久。”
Advertisement
“這有什麼好對不起的。”祁母高興的都要斂上天去了,和虞辭憂的母親也算是最知心的朋友了,虞母走的早又只有棗棗這麼一個孩子,雖然現在還護的了棗棗,但是也有離開的那一天,如今棗棗了祁家,整個祁氏為撐腰,誰還敢欺負。
祁父也是難得出笑容,看著這個兒子也是順眼幾分,只有祁爺爺依舊瞪著自己這個孫子,“景儒,你如今也不小了,做事別再躁躁,你有了棗棗就要擔起保護好的責任。”
商業不比其他,更何況又是做到頭頭的大商業,商場里難免雨腥風,祁景儒萬一在外惹了事,那些仇人第一個找的就是棗棗。
“知道了,爺爺。”祁景儒乖張的答應,涉及到任何關于虞辭憂的事他都不會怠慢。
“準備什麼時候辦婚禮?”說這話的是祁夫,他的口吻完全是陳述句,不帶任何疑問。
祁景儒給的故事大綱里可沒有提到結婚這一條,虞辭憂在餐桌下用腳踢了踢祁景儒,男人吃痛,大手上的大示意虞辭憂老實一點,然后他才用厚重的影說道:“婚禮不急,我和棗棗先把證領了,婚禮我要多準備一點時間,好給一個不留憾的回憶。”
祁景儒要等,等到小公主全心全意上他時,再給一場小時候就曾構思好的婚禮。
棗棗兒園畫的那幅婚禮設計圖如今還在他的保險柜里鎖著呢。
虞辭憂低頭吃菜,男人低沉的語調就像是羽拂過心臟,的讓你罷不能,當然知道,這只不過是祁景儒為了緩住祁家人的權宜之計而已。
虞辭憂,你心什麼呢?
一頓晚飯吃完,大家又圍著虞辭憂問了很多事,確保在國外那三年過的很好,回國了也沒有不適,才依依不舍的允許祁景儒將棗棗帶回家。
Advertisement
祁爺爺還親自送到了門口,他像是得不到糖的孩子,撒著說道:“棗棗也不多陪陪爺爺,爺爺都這麼久沒有見過你了。”
虞辭憂其實也很想留下來,但是隔天還要去公司報道,老宅太遠了也不方便打的,實在不方便,抱了抱祁爺爺:“爺爺,棗棗保證一有空就來這兒看您。”
“好,好孩子。”祁爺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兩個孩子走后,祁母還在門口發呆,祁夫摟過妻子的腰,低聲說道:“老婆,在想什麼?”
祁母嘆息,“你說棗棗一個那麼小的孩子這麼拼干嘛呢。”祁母轉而一想,又自問自答道:“也是,這虞氏要是真落到了那個姓蔣的手里誰也不會好的。”
其實虞辭憂跟祁母的格真的很相像,一樣的固執也一樣的義無反顧,虞辭憂可以為了奪回虞家的公司而忍痛割放棄自己的音樂夢想,而虞母也可以為了當時的真愿跟虞家斷絕關系。
虞辭憂要求回自己的公寓,祁景儒是想拒絕的,但是這事兒也不能之過急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反正他還有大把的時間將小公主哄道心里來。
月朦朧,虞辭憂在車依舊是沉悶不語,看著那明月,心里又想到了小時候的事,那時候的祁景儒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各種嚇唬,其中有一句就是不能用手指指著月亮,不然會從天上下來一個月亮婆婆將你耳朵給割掉。
那一段時間,虞辭憂怕的每晚都不敢看月亮,心里有影。
祁景儒看著悶悶不樂的樣子,不知道從車的哪里出來一包薄荷味的糖,丟給了虞辭憂,他另一只手出窗外吹著夜風,左手有的沒的敲打著方向盤。
隔了許久,才出聲:“只準吃三顆。”
Advertisement
虞辭憂乖乖聽話,拿出了三顆糖后又將糖袋子封好,然后一抬頭,手里的三顆糖全都放在了里。
這薄荷糖極辣,吃一顆都會鼻子酸,虞辭憂一下子吞了三顆,此時眼淚都出來了。
恰逢紅綠燈,祁景儒轉頭看,瞇起眼睛,“一聽到糖這個字就迫不及待的塞里了?”
虞辭憂惡狠狠的瞪著他,這人居然還在一旁說風涼話,嗚嗚咽咽的什麼也說不清楚,眼淚愈流愈多,祁景儒急了手直接到的前,“辣就快點吐出來。”
隨后,手上立馬多了三顆大小不一沾滿口水還黏糊糊的薄荷糖,祁景儒倒是一點也沒有嫌棄,很快用餐巾紙包好了,然后繼續開車前進。
這樣一來,虞辭憂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怪只怪車子能太好,路程太過短暫,那白的月亮太過迷人,祁景儒不愿的在虞辭憂的公寓前停下了車,虞辭憂準備下車前,車門被祁景儒鎖死了。
孩疑的轉頭,的因為吃了薄荷糖的緣故,飽滿的上漉漉水潤潤的,讓人想要一親芳澤。
祁景儒轉頭不去看那張充滿力的,低聲說道:“明天早上我來接你上班。”
“好。”虞辭憂沒有拒絕,確實不來公車和地鐵。
“那中午一起吃午飯?”
“好。”
祁景儒愜意的瞇著眼,他用近乎平常的語氣說道:“明天再一起去趟民政局?”
“好...?”虞辭憂下意識的想要答應,但很快又想到了不對,皺著眉頭問道:“明天去民政局干嘛?”
祁景儒勾起角,懶洋洋一笑,“因為我還沒有本事大到能把民政局搬到你面前來,所以就勞煩棗棗公主移您尊貴的軀跟著小的走一趟了。”
虞辭憂剛想出口拒絕,但突然又想到了什麼,不再反駁,留給祁景儒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然后瀟灑的打開車門離開了。
那個眼神里充滿了的小聰明。
祁景儒低頭無奈的苦笑,目送小公主進了家門后,才從剛剛那糖的地方拿出了一煙,虞辭憂想的是什麼他很清楚。
棗棗的戶口本在虞家,他的外公外婆可都不是好糊弄的主。
接下來的全部都是仗要打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5 章

失憶后我成了大佬的白月光
[追妻火葬場,試試就逝世] 容初離家那晚碰到一個男人,陰差陽錯之后發現對方竟然是身家千億的頂奢集團太子爺,宴岑。 她生下了那個男人的孩子,卻沒能留住他的心。 三年后,國際時裝周,HF界的新晉寵兒云初作為開秀模特,一時風頭無倆。 這位東方面孔的頂級超模,邁開她一步六位數美金的臺步,又美又颯,勢不可擋。 突然,一個軟萌的小團子上臺抱住她的膝蓋,仰臉清脆喊了一聲:“媽咪!” 全場嘩然。 容初:“!!!” 震驚到裂開的容初望向臺下,看到第一排西裝革履的集團太子爺正深深看著自己。 男人黑眸幽深,“榕榕。” “我終于找到你了。” 容初:“?” 你誰?? ** #勁爆!那個新一屆的秀霸超模一門心思攀龍附鳳,為當太子妃甘作后媽!!# 一片“嘔口區D區”聲中,太子出來發聲了:“不是后媽,親的。” 那個最大珠寶集團新上任的CEO也發聲了:【那位新一屆的秀霸超模,是我妹妹,親的[微笑]】 那個剛參加完頒獎典禮的影后隔著時差,半夜上線:【自備身家,不攀不附,請有心人士莫cue我妹謝謝[再見]】 有心人士宴某人:“…………” ** #勁勁爆!超模竟是失蹤四年的珠寶千金!突然回歸欲跟對家鄭少聯姻!# 聯姻消息一傳出,鄭氏股價毫無預兆地暴跌,市值蒸發愈百億。 始作俑者宴岑親登容家門。 “跟我結婚。不簽婚前協議,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一臺步值六位數的頂級超模×一分鐘賺六位數的頂奢太子爺 *男女主彼此唯一,HE;狗血瑪麗蘇,請自行避雷 *涉及時尚圈HF圈,私設hin多,沒有原型,作者瞎掰
20.8萬字8 14265 -
完結1955 章
一胎四寶:轉走爹地十個億
蘇童雪嫁給喬墨寒時,所有人都說,她撞了大運。貧民窟出身,一無所有,卻成了權傾帝城男人的妻子。她以為隻要她努力,終可以用她的愛一點點焐熱喬墨寒的心。卻沒想到在臨盆之際,被硬生生割開肚子,取出孩子,踢下懸崖!四年後,浴火重生的她回歸。男人卻將她堵住,牙咬切齒:“蘇童雪!你這個無情的女人!竟敢拋夫棄子!”蘇童雪懵了。難道不是當初這男人嫌棄厭惡到都要將她毀屍滅跡了?
184.5萬字8 45888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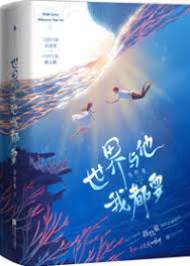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8147 -
完結177 章

前夫越界招惹
她一個姜家落魄的大小姐,跟一個窮小子結婚了,三年之后卻慘遭窮小子背叛。離婚沒多久,窮前夫突然搖身一變,成了帝國大佬。 她驚了! 直到有一天,前夫撞見她與別的男人說笑,開始瘋狂的趕走她身邊的爛桃花。 他抓著女人的手,極有占有欲的說。“我看老子的女人,誰敢招惹。” “不好意思啊,我對你這個老男人不感興趣,請拿開你的臟手,不要讓我的小奶狗看見了。” “看見了正好,讓他好好睜大他的狗眼看看,誰才是你的男人。”
35萬字8 1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