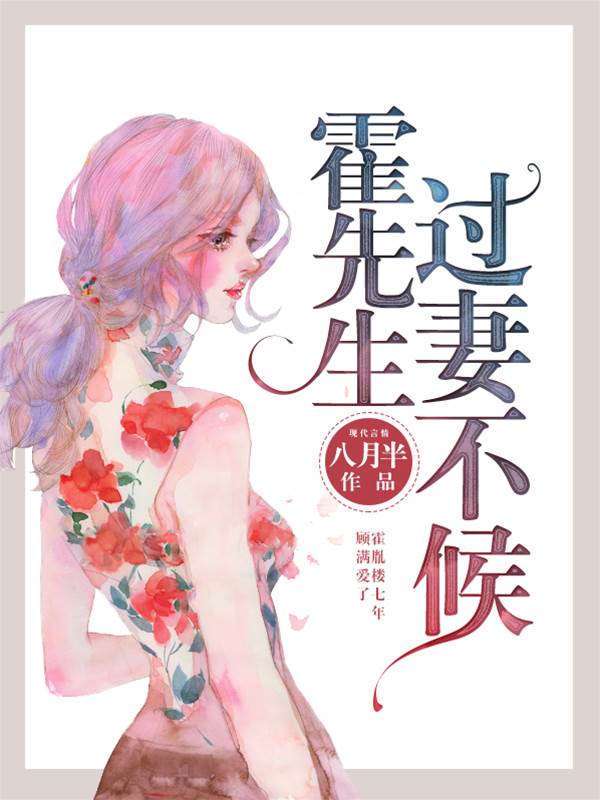《賀總絕嗣?和小啞巴閃婚后真香了》 第二百七十章 打一巴掌給個甜棗
阮清音一句廢話都不講,從包里拿出那張火紅鎏金的請柬,啪得一聲摔在桌上。
賀肆看著那張請柬,緩緩握拳,心臟有一瞬間的刺痛。
他蹲在阮清音的腳邊,仰頭看,目疼惜復雜,“誰給你的?”
一瞬間,賀肆想了很多,幾百個念頭在他腦海里浮現。
他明知道自己不會娶那個人,從來沒將這件事視為他們之間的阻礙。
可親眼看見阮清音委屈地摔出來一張請柬時,還是不由自主的心疼。
他握住阮清音冰涼的小手,到自己臉頰。
賀肆深吸一口氣,聲音有些發,“這是假的,這種事不會發生,我保證。”
阮清音似乎是聽懂了,主俯,用額頭抵住賀肆的頭頂,隔著一些碎發,兩人無聲地著對方的眼睛。
那一刻,賀肆清醒地覺兩人靈魂在共鳴。
阮清音的神迷茫,彎起角笑了笑,臉頰浮現小小的梨渦。
賀肆心下一,另一只手扶住的肩膀,輕輕在淺笑的梨渦落了個吻。
賀肆將人帶回別墅,他始終睡不慣阮清音國際港那邊的床。
他將人輕輕放到主臥床上,折返回從前的房間找了條質睡,親自手給換上。
賀肆看著那張睡的臉,心里得一塌糊涂,目定在床尾的那張請柬,笑意轉瞬即逝,眸子一暗,眼底冷得結冰。
不論是誰,只要想拆散他和阮清音,他都不會坐視不理。
在這世界,沒有人能不讓他們在一起。
哪怕是阮清音也不行。
他坐在地毯上,下埋在手臂里,出一只手了的臉,又溫地開側臉的一縷碎發。
他花了很多年才意識到他有多阮清音。
他浪費了很多年,務必會抓住未來,抓住阮清音。
Advertisement
賀肆靜靜地守了一會,轉出門了支煙,撥了通電話。
凌晨四點的夜里,電話足足響過六七遍。
蔡淑華披著外套,坐在客廳的座上,將電話接起來。
“您今天找過了?”
蔡淑華睡意朦朧,半夜被座機的鈴聲驚醒,仍然心里悸,平復了幾秒,問他,“你說誰?”
“媽,您別裝傻!您沒找過,手里怎麼會有張請柬,我看過了,那帖是我爸寫的,真是難為您,順藤瓜找到。”
蔡淑華愣了一瞬,有些惱怒,“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說什麼,我找誰了?該找誰?請帖早就發過了,我怎麼知道你指的是誰!”
蔡老師看了眼客廳的鐘,短的指針堪堪到四,窗外天微亮,按下怒火,反問道,“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嗎?你難得往家里打電話,非要專挑這個時間點,還上來就沖著媽媽發一頓火?”
賀肆深吸一口氣,勉強排除了蔡老師的嫌疑,但這還不算完。
他這一通電話,一是為了問清楚那張請柬的事,二是跟家里表個態。
“二十八號,我不會出席訂婚宴,這事沒得商量。這半個月,我托了很多人去給沈家遞話,只要他們點頭退婚,什麼補償我都給,但沈佳鐵了心要嫁我。”
“我就講這一次,哪怕是表面夫妻,我也不愿意陪著演這一出戲,娶回來冷著這種事我不屑做,因為我就沒打算娶。”
蔡淑華了額角,徹底沒了睡意,“阿肆,這件事是爸媽沒照顧你到你的,但覆水難收,下周就辦儀式了,所有的事都準備就緒了,佳甚至訂好了禮服,的陪嫁也清算好了,聘禮單子都出了。”
賀肆回頭了一眼那道房門,仰了仰頭,沉默片刻后突然開口,“媽,您要是想死我,您就繼續一意孤行,人我不會娶,您就當沒我這個兒子也。”
Advertisement
“混賬!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蔡老師難得失控,恨鐵不鋼地罵了句。
“媽,我其實佩服您的,我之所以能是賀家的獨子,離不開您的雷厲手段。”賀肆冷笑了幾聲,不到萬不得已,他并不想挑起母親的傷心事。
“住!”蔡淑華心頭一驚,用手捂住聽筒,猛地回頭看了眼臥室閉的房門。
賀肆不聲地繼續威脅,“媽,趁著儀式沒舉行,一切都還來得及。”
“請帖都發到京九四城了,怎麼挽回!”
“換個新娘我就娶。”
蔡淑華握聽筒,“誰?”
賀肆張了張,阮清音的名字到了邊又說不出來了。
他仍然有所顧慮,怕沒做好萬全準備就被家里知曉他和阮清音如今的關系,壞了他的計劃。
偏偏最不喜歡阮清音的還是他媽。
賀肆避開話題,不愿再答,“媽,比起來暫時的孤獨,我更畏懼徹底失去人的本能。我有喜歡珍視的人,我向您保證,不是什麼七八糟的人,但現在時機未到,您別管了,嗎?”
蔡老師披在外面的外套落一半,客廳的中央冷氣十足,想了想,掛斷了電話。
次日清晨
阮清音在床上翻了個滾,卻到一雙手,嚇得一激靈,猛地瞪大眼。
賀肆睡意朦朧,將人撈懷里,在耳邊小聲道,“別鬧,再睡會。”
低頭檢查了一下,翠青的質睡,兩細肩帶到胳膊上,前一片春。
阮清音惱怒,不輕不重地扇了賀肆一掌,聲音清脆。
“你最好能說出一個讓我不生氣的理由。”上一秒還在睡的男人,此刻睜著眼,眸子深不見底,冷峻的臉上有層薄薄的慍。
阮清音瞬間慫了,收回手,理不直,氣不壯的說道,“剛剛有蚊子。”
Advertisement
賀肆沒說話,沉默地看,滿臉都是“你看我信嗎”“還能編得離譜些嗎”的表。
阮清音想逃,卻被一雙大手叩住腳腕,往懷里一扯,瞬間彈不得。
“你做什麼!?”阮清音惱地用腳蹬他,兩只白的小腳丫噌噌噌地踢著。
他也不惱,只是目越發沉,眸底出幾分耐人尋味的危險神。
賀肆用手住的臉,輕輕啄了一口,“打一個掌給一個甜棗,聽過嗎?”
猜你喜歡
-
完結268 章

掌上尤物
白天,她是許清晝的私人秘書,負責替他賣命工作處理他接連不斷的小情兒。晚上,她頂著他未婚妻的身份任他呼來喝去,為所欲為。訂婚八年,許清晝的心上人一朝回歸,江羨被踹下許太太的位置,落得個眾人嘲笑奚落的下場。人人都等著看她好戲,江羨卻笑得風情萬種,當晚進酒吧,左擁右抱,勾來俊俏小狼狗,愉悅一整晚。她肆意卷土重來,各大財閥集團為爭搶她而大打出手;日日緋聞上頭條,追求者不斷。釣系小狼狗:“今晚約?房已開好等你來。”純情大男孩:“親愛的,打雷好怕你陪我睡。”快樂是江羨的,只有獨守空房的許清晝氣得兩眼發紅,...
55.9萬字8 6340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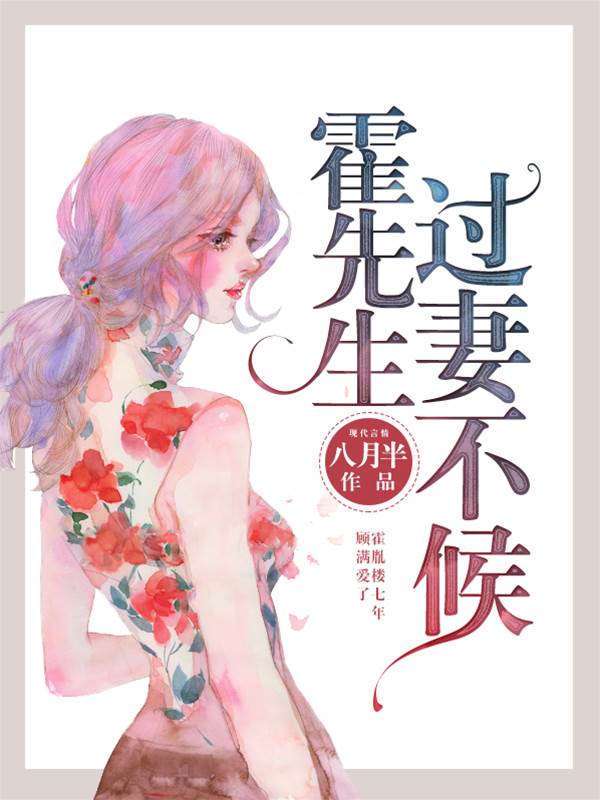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108 章

哥哥他總想與我保持距離
曾經的他是一輪皎月,祈望驕陽;后來皎月已殘,又怎堪配驕陽?江歲和斯年第一次分別那年,她八歲,他十四。 彼時她緊緊地抱著他不撒手,口中歇斯底里的哭喊著:“年年哥哥,你別走!” 可他還是走了,只給她留下兩樣東西和一個約定。 十年后異地重逢, 他來機場接她, 他在她身后試探地喊她的名字:“江歲?” 她朝他不敢確定地問:“你是,斯年?” 兩個人面對著面,都差一點認不出彼此。 而此時他已跌落塵埃,卻依然對她痞笑著問:“呵,不認識了?” 匆匆一年,江歲像驕陽一樣,熾熱地追逐著他,溫暖著他。 而斯年卻深藏起對她深沉的感情,時刻想著與她保持好距離。 江歲可以忍受別人誤解她,嘲諷她,但她見不得有人在她面前羞辱和挑釁斯年。 斯年同樣可以忍受任何屈辱和諷刺,卻見不得江歲在他面前被人欺辱。 他竭盡一身力氣洗去泥濘,只為能站在她身邊。 然而造化弄人,他只能一次次親手將她推開。 江歲此生惟愿年年長相見。 斯年此生惟愿歲歲永平安。 前期:清純大學生女主vs多功能打工男主 后期:高級翻譯女主vs神秘總裁男主
29.4萬字8 1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