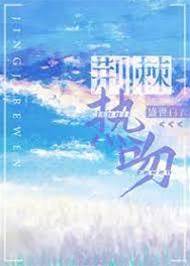《曠野烈風》 第22章 罪人
夜里,人的神往往更敏。
容易憂傷,也容易思、。
黑子四肢放松地靠著椅背,目毫不掩飾地將芮仔細打量,或者說。
人眉目著冷冷的清秀,眼睛生得極其漂亮,眼眸澄澈,似有雪。
怪不得徐凌當初一眼就相中的照片。
真人更漂亮生,一點不像那些人,人還沒死,上就已經有了一種腐爛的味道。
他長這麼大,還沒見過皮這麼白的人。
不是病態的那種白,而是像玉一樣潤的白。
因此,顯得格外嫣紅。
令他心生某種惡劣的沖,想要親那張。
不,不是親,是狠狠的吻,還有,夾雜著男人那種。
這念頭讓黑子嚨發干,他點了支煙,深吸一口。
察覺到他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對后,芮每神經都繃著。
呼吸很輕,盡可能地想降低存在。
然而,在這樣破敗又狹小的空間里,實在太亮眼。
黑子吐著煙圈,突然問:“想嗎?”
芮冷道:“不想。”
“口是心非。”黑子笑了聲,突然撐起上半傾向。
“煙,就是你的氧氣。”
他聲音低沉,有點心不在焉的味道,眼皮也微微垂著,盯著抿的。
“想要就告訴我,我給你。”
他的眼神,輕佻又危險。
暗線中,男人的臉劣又丑陋。
芮瞪著他的眼睛,咬著牙低沉地出一個字。
“滾!”
黑子哈哈笑著,朝臉上噴了口煙霧。
糙的手指著下,再緩緩向下,勾著領,笑容變得邪惡。
“聽說你勾搭男人很有一套,特別………………”
芮眼神厭惡,一字一頓。
“你敢我一下,我一定會弄死你!”
Advertisement
沒想到,在這樣的氣氛下,這樣的話對一個男人來說,無疑是催化劑。
黑子眼里燃起熾亮的火,大手掐著脖子,“那就試試看,誰先弄死誰!”
荒山野嶺,雨夜寂靜。
對一個陌生人,不管不顧,那該是怎樣的刺激!
就在黑子一手覆上的,一手按住的腦袋親上去時,門板被踹開。
冷風挾裹著男人的影涌進來,破敗的房屋頓時顯得更加狹小。
黑子怔愣間,來人抬腳踹在他上。
黑子倒在地上,椅子也散了架。
“我說過,不許。”
男人眼里跳著一層怒火,說話的聲線也染上了冰寒的怒意。
黑子掙扎著爬起來,無所謂地拍拍手,嘿嘿一笑。
“逗玩呢,你怎麼來了?”
男人對上芮的眼睛,手了的臉,聲音頓時變得溫潤。
“沒事了,別怕。”
芮冷冷看著他,“到底怎麼回事?”
徐凌笑了笑,“等我把善后理好,再慢慢告訴你。”
他將帶來的外套蓋在上,又在額頭上印下一個吻。
“等我。”
像是人間的喃呢,曖昧又繾綣。
之后,他看了眼黑子,二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
芮這時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緒了。
掙扎著嘶聲大喊:“徐凌,你放開我!”
“你們這些渾蛋!渾蛋!”
鋪天蓋地的痛苦好似將整個人席卷,拳頭攥得死死的,雙眼通紅的像是頭嗜的狼。
可就是沒有眼淚。
恨自己,為什麼要自投羅網!
為什麼要聽信那些混蛋的蠱!
芮,你為什麼那麼蠢!
說是解,其實是被自己蠢死的!
痛罵,喊,撕心裂肺。
黑子和徐凌卻再也沒有推開那道破門板。
Advertisement
……
段泊安甚至驚了縣刑警隊。
芮的份很快查明,他得到家人的電話號碼。
凌晨一點,電話打過去,有個蒼老沙啞的聲音響起。
“喂。”
段泊安嚨莫名發,“是芮家嗎?”
“什麼事?”
“芮在家嗎?”
“沒有。”
“你知道去哪里了嗎?”
“死了。”
電話掛斷,不到一分鐘。
“怎麼樣?”李亮湊過來問。
段泊安眉頭鎖,想說什麼,卻覺腔似乎被一塊巨石狠狠制,說不出話來。
怪不得閉口不談。
一個人,究竟是犯下了怎樣的滔天大罪,才能在家人眼里‘活著死去’呢?
刑警隊長路隊,和段泊安是老人了。
他晃了晃手里的資料,“芮的,要看看嗎?”
段泊安迫不及待地接過來,卻又好似有千斤的重量,一時難以翻開。
路隊給了他支煙,開口:“芮,本來是姓寧,三歲時在一場車禍中父母雙亡。后來被送到孤兒院,五歲被家收養。”
“浙南醫科大,赫赫有名的劉一刀劉教授的得意門生,浙南二院最有前途的外科醫生……”
“三年前,發生一起醫療事故,的哥哥璟就死在的手臺上。”
“被醫院開除,家回不去……竟跑到我們這兒來了。”
路隊并不知道段迫安和芮的關系,在他肩上拍了拍,同道:“你也是點兒背,怎麼就攤上這種事兒了。不過你放心,和你關系不大……”
段泊安掐掉煙,抬腳就走。
路隊莫名其妙:“哎,話還沒說完呢!”
“路隊……”
李亮忙住他,猶豫道:“那個……段隊和那姑娘好上了。”
“好,好上了?”
路隊一驚,“萬年鐵樹開花了?”
Advertisement
可這究竟開的是朵什麼花呀!
從路段監控看來,沒有發現芮的影,也沒有發現可疑車輛。
芮還在青云鎮的可能很大。
天還沒亮,黑沉沉的夜幕像一張巨大的網。
不知從何傳來悲鳴的鳥聲,和龐大的尋人隊伍,將整個青云鎮掀得天翻地覆。
天亮時,段泊安在醫院門口到黃婷婷。
黃婷婷住他,“段隊,我爸今天生日,你來嗎?”
段泊安哪有心,腳步都沒停一下。
“喂!”
黃婷婷急得大喊:“我看見了!”
段泊安猛地回頭,“什麼時候?”
“昨天中午。”
黃婷婷指向醫院對面的空地,“在這里,上了一個男人的車。”
段泊安:“那個男人長什麼樣?開的什麼車?”
黃婷婷歪著頭,吃力地描述。
“長得還帥,比芮高不了多……開的是輛黑轎車,車牌號好像是晉字開頭,外地的。”
是徐凌。
段泊安心里燃起的希又熄滅下去,“之后,還有在鎮上看到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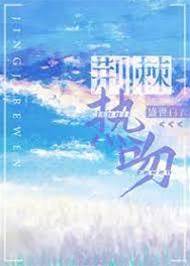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