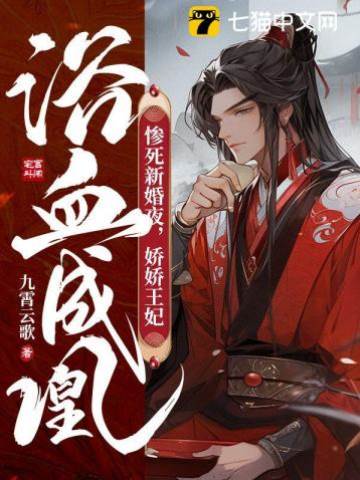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不喜細腰嬌軟?是朕口是心非!》 第1卷 第86章 打架
王裕神慌張地闖廂房,額角滲著細的汗珠。
“陛下......”
他言又止地瞥了眼在場的眾人。
赫連梟劍眉微蹙,見王裕這模樣,還是起出了包房。
一出門,王裕立即低聲音急道:“陛下,太后娘娘今晚抱恙,急召李太醫宮問診。可......可李太醫被您安排在文勛侯府為荊婭夫人診治......”
荊婭夫人是文勛侯的母親。
“太后得知后震怒,當即下懿旨召回了李太醫。只是......”
他聲音更低了。
“適才那達慕大會散場時,文勛侯府的車駕與冠軍侯世子相撞,荊婭夫人舊傷復發,疼得厲害。偏生今夜全城郎中都在參與大會,實在找不到開門的藥房.......”
赫連梟不明白這點小事王裕竟然來請示他。
當即道:“太醫院養著那麼多太醫,隨便派一個去侯府便是,在這里與朕啰嗦什麼?”
王裕雙膝一,額頭幾乎地。
“陛下明鑒......太后娘娘不待見文勛侯,如今宮門已下鑰,侯爺在宮門外急得團團轉......”
“可太后娘娘發了話......說文勛侯若能在宮門前跪滿一個時辰,便...便放太醫出宮救治荊婭夫人.......”
“現在文勛侯還一直跪著呢。”
赫連梟抬步就要去找阿茹罕,卻在邁步的瞬間頓住——
廂房,慕灼華的影過雕花門若若現。
他推開門,坐在慕灼華旁邊,溫地包住的手。
“朕有事要去理,很快就回來。”
慕灼華指尖微,前夜他也是這樣說的。
抬眸掃向王裕,驚得對方立刻低頭,連呼吸都屏住了。
“陛下請便。”
緩緩出手。
赫連梟口發悶,知道不滿,卻也得離開——
Advertisement
阿茹罕跪在宮門前,太后的懿旨,除了他無人敢違。
但他很快就會回來。
臨行前赫連梟冷冷瞥向蕭君翊,對方卻從容舉杯,角那抹意味深長的笑像刺扎進他心里。
珠簾晃間,他的角已消失在門外。
宮門前,夜如墨。
阿茹罕筆直跪在青石板上,月勾勒出倔強的廓。
侍衛們見駕親臨,齊刷刷跪倒一片,鎧甲撞聲在寂靜的宮門外格外清脆。
“阿茹罕,起來。”
低沉的嗓音讓阿茹罕猛地抬頭,帝王高大的影逆著月,宛如神祇降臨。
瞳孔微:“陛下?”
赫連梟負手而立。
“朕已命王裕調了太醫院不當值的太醫,此刻已在侯府候著。”
他目沉沉地落在阿茹罕慘白的臉上。
“你且回去。”
阿茹罕眼中剛泛起彩,又黯淡下去:“可太后娘娘......”
“朕的話就是圣旨。”
“你是前朝重臣,何須聽后宮懿旨?”
“臣......遵旨。”
艱難起,卻在站直的瞬間子一,竟直接暈了過去。
赫連梟一驚,箭步上前,接住下墜的軀。
懷中人輕得令他心驚,料下嶙峋的骨骼硌得他心頭一。
“速去侯府!”
駕在月中疾馳而去。
-
另一邊,蕭君翊趕走了李紜。
廂房門輕輕合上,隔絕了外間的喧囂。
蕭君翊緩緩晃手中的琉璃盞。
“不開心?”
蕭君翊嗓音溫潤,卻帶著幾分試探。
慕灼華冷笑一聲:“殿下今夜與赫連梟針鋒相對,想必很是盡興?”
杯中的酒突然晃得急了,映出蕭君翊驟然收的指節。
“看他費盡心思向所有人宣告你的歸屬......真是可笑。”
“只有握不住的東西,才需要這樣聲嘶力竭地證明。”
Advertisement
“東西?”
慕灼華猛地抬眸。
“原來在殿下眼中,我不過是個可以隨意轉手的件。看來將我送來紫原和親,殿下很是滿意?”
琉璃盞突然停在半空。
“婳婳......”
蕭君翊聲音微啞,“你知道孤不是這個意思。”
酒在杯中搖晃,慕灼華指尖微,一杯接一杯地飲盡。
酒水順著角落,混著眼角的淚,浸了襟。
“你們都說喜歡我......卻都將我當作可以隨意轉手的件......”
酒杯重重擱在案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你有了李紜,赫連梟邊突然冒出個文勛侯......”
仰頭又是一杯,間火辣辣的疼。
“在你們眼里,我不過是個戰利品......贏了就擺在架上,膩了就換新的......”
蕭君翊口發,手想要拭去臉上的淚,卻被偏頭躲開。
泛紅的眼尾在燭下格外刺目,像是被碎的海棠。
“蕭君翊......”
突然抓住他的袖。
“這個世道,我是不是永遠都......”聲音哽咽,“只能做你們這些男人博弈的籌碼?”
突然將酒杯摔在地上,一聲脆響中,問道:“我是不是只能依附你們這些臭男人!”
蕭君翊結滾,所有話語都哽在間。
問的每一個問題,都像利箭穿他的膛——
因為他心底最真實的答案,只會讓更加絕。
從來,都沒有選擇的權利。
他何嘗又不是呢?
夜風卷著酒香掠過窗欞,指尖挲著酒杯,分不清是淚還是酒浸了袖口。
“蕭君翊......”
聲音輕得像是嘆息,帶著三分醉意七分恍惚,連自己都辨不清此刻的哽咽是真是假。
Advertisement
——要他相信,相信與赫連梟之間裂痕遍布,相信甘愿為他做南朝的棋子。
可心底深,卻有個聲音在冷笑:
等南朝國破那日,要站在最高的城樓上,俯視著他錯愕的臉。
輕飄飄地說:“你以為青梅竹馬的分能困住我?”
指尖劃過他染的下頜,“我的從來只有權力,而你——不過是我登頂時,最趁手的一塊墊腳石。”
酒間,灼得心口發疼。
蕭君翊傷過的心,所以也要他痛。
可赫連梟呢?
那個利用傷害的男人,從指里出的權力,就能彌補被碾碎的自尊嗎?
慕灼華閉了閉眼,酒意混著恨意在腔翻涌。
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還能做什麼,只能一杯接一杯地飲盡。
最終,伏在案上,青散,酒杯傾倒,酒順著桌沿一滴一滴落下。
蕭君翊凝視著醉意朦朧的側,只見雙頰染著晚霞般的酡紅,纖長的睫上還掛著幾滴晶瑩的淚珠。
他輕嘆一聲,打橫抱起這溫的子,像對待易碎的珍寶,將安置在鋪著煙羅的人榻上。
時間緩緩流逝,蕭君翊看著樓下燈火一盞盞熄滅。
推開木門的剎那,濃烈的酒香混著子上的幽蘭香撲面而來。
赫連梟的視線掃過包廂——
蕭君翊正慵懶地倚在朱漆欄桿旁,玄錦袍半敞,指尖還晃著一盞未盡的琥珀。
順著他的目去,赫連梟瞳孔驟。
人榻上,慕灼華云鬢散,他親手系好的杏紗領口已然松散,出半截凝脂般的頸子。
醉意染得雙頰如三月桃花,上胭脂暈開一片,得驚心魄。
“怎麼了?”
赫連梟的聲音比檐下冰棱還冷。
蕭君翊晃了晃酒盞:“陛下看不出來?”
Advertisement
琉璃盞在指尖轉出譏誚的弧度,“醉了。”
“你的太子妃呢?”
“陛下好興致,這時辰來尋人。”
“太子妃早已安寢,倒是孤——”他眸掃過榻上醉酡紅的人,尾音刻意拖長。
“不得不替陛下守著這位......貴妃娘娘。”
赫連梟大步走向人榻,卻在俯時僵住——
他離開前在頸側留下的嫣紅吻痕,此刻竟泛著曖昧的紫,這是被人加深的痕跡。
指腹過那時,榻上人無意識嚶嚀一聲,出更多斑駁痕跡。
燭火“噼啪”了個燈花,映得帝王眼底翻涌。
蕭君翊間溢出一聲低笑,像一簇火苗倏地點燃了赫連梟眼底的暴戾。
廣袖帶起勁風,赫連梟已欺上前,拳頭裹挾著雷霆之勢直襲蕭君翊面門。
蕭君翊早有防備,側避過的同時反手劈向帝王咽——
兩人瞬息間已過了十余招,案幾翻倒,青瓷酒盞碎齏,鎏金屏風在掌風中斷作兩截。
“哐當——”
紫檀木架轟然倒地,驚醒了榻上醉意昏沉的慕灼華。
紫原烈酒的后勁燒得太突突直跳,朦朧間只見兩道影在漫天飛散的紗帳間纏斗。
踉蹌著撐起子,錦緞鞋踩過滿地狼藉。
蕭君翊余瞥見的影,原本格擋的招式突然一滯。
赫連梟的膝擊結結實實撞在他肋下,他順勢向后跌去,后背重重撞上朱漆圓柱。
“太子哥哥,你沒事吧。”
慕灼華撲跪在蕭君翊側。
這個久違的稱呼讓蕭君翊震驚,更讓赫連梟高舉的拳頭驟然僵在半空。
帝王猩紅的瞳孔里翻涌著比暴怒更可怕的東西。
猜你喜歡
-
完結39 章
寵妃彆太甜
她代替哥哥入朝為官,伴君在側三年,卻對他動了心。
7.3萬字8 19694 -
完結2973 章

替嫁醫妃
女法醫魂穿天陵王朝,父不在,母不詳,只為一個恩情替嫁給當朝殘廢毀容七王爺。
525.9萬字8 60015 -
完結1205 章

王爺,您今天后悔了嗎
楚昀寧穿成王府棄妃,被圈禁在冷院,肚里還懷了個崽。她含辛茹苦將孩子養大,誰知這瞎眼的爹聽信綠茶讒言,質疑孩子的身世。楚昀寧表示,行,這孩子跟你沒關系!手握銀針,救死扶傷,名滿天下!開商鋪,造美容配方,銀子賺手軟!徹查當年的真相后,蕭王懊悔不已,決定加倍補償母子二人,日日來獻殷勤。楚昀寧:“王爺,請自重!”
189.3萬字8.33 286479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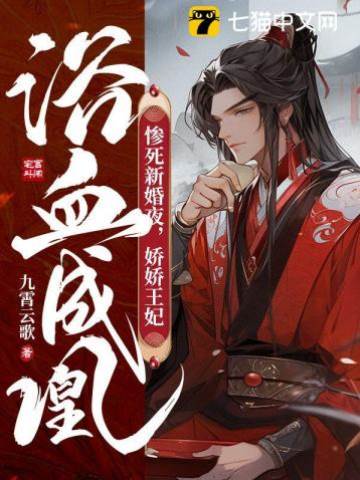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