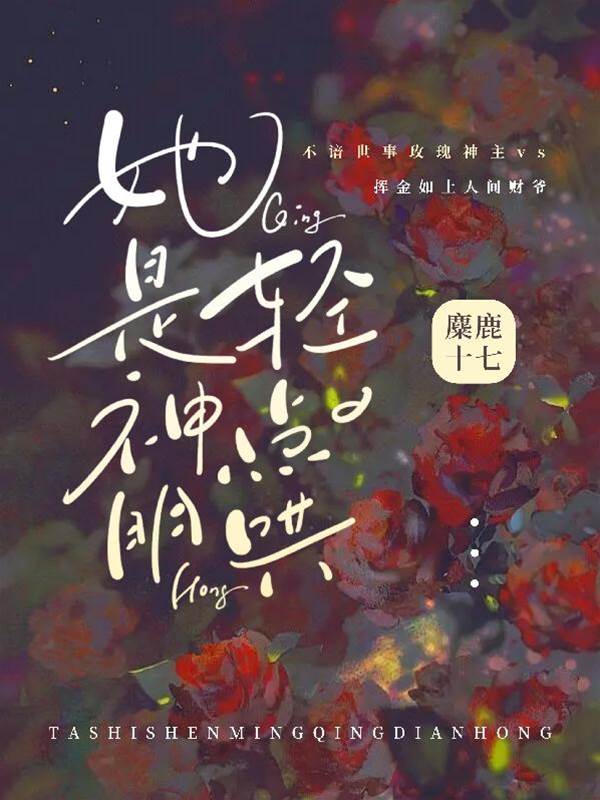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微醺夜,她狂撩,京圈大佬紅溫了》 第402章 墨家人回A國
清晨的機場被薄霧籠罩,云箏裹著傅凌鶴的駝羊絨圍巾,站在VIP候機室的落地窗前。
玻璃映出微紅的眼眶,后墨家長輩們正在做最后的行李確認。
"這個保溫杯里是紅棗茶,路上喝。"寧梔將印著櫻花紋的杯子塞進云箏手里,指尖在掌心多停留了三秒,"媽媽每天都會給你發消息。"
墨沉楓正與傅凌鶴低聲談,突然轉將一張黑卡放進兒口袋:"想買什麼就買,別委屈自己。"
他生地補充道,"包括酸辣。"
云箏噗嗤笑出聲,眼淚卻跟著落下來。墨時安立刻用手帕輕輕按在眼角:"妝要花了。"他今天特意穿了云箏送的那條深藍領帶,領帶夾是星星形狀的。
登機提示響起時,墨老爺子突然用拐杖敲了敲傅凌鶴的鞋尖:"記住你說過的話。"老人目如炬,在看到傅凌鶴鄭重點頭后,才轉了云箏的發頂:"丫頭,爺爺給你留了驚喜在琴房。"
直到墨家人的影消失在廊橋盡頭,云箏還站在原地不。傅凌鶴從后將整個裹進大里,下抵著發頂:"箏箏?"
"我沒事。"云箏聲音悶悶的,轉把臉埋在他前,聞著悉的雪松香平復呼吸。傅凌鶴的西裝口袋很快暈開一小片痕。
機場的玻璃幕墻外,一架銀白的飛機正緩緩向跑道。
云箏站在VIP候機室的落地窗前,指尖無意識地挲著腕間的星星鈴鐺,目追隨著那架載著至親之人的飛機。
傅凌鶴站在后半步的位置,手掌輕輕搭在腰間,無聲地傳遞著溫。
他能覺到云箏的肩膀微微抖,像一只在寒風中瑟的小鳥。
"箏箏。"他低聲喚,聲音輕得仿佛怕驚擾了什麼。
Advertisement
云箏沒有回頭,只是輕輕搖了搖頭。飛機引擎的轟鳴聲由遠及近,最終騰空而起,在蔚藍的天幕上劃出一道白的弧線。直到那架飛機變一個小點,徹底消失在視野中,云箏才緩緩轉,眼眶泛紅卻倔強地不讓淚水落下。
傅凌鶴什麼也沒說,只是將攬懷中,讓把臉埋在自己前。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的棉質襯衫,就是怕云箏哭的時候,面料會磨疼的臉頰。
"我們回家?"等云箏的緒稍稍平復,傅凌鶴才低聲詢問。
云箏搖搖頭,聲音悶在他前:"不想回去...家里太安靜了。"
傅凌鶴沉思片刻,突然有了主意:"我帶你去個地方。"
三十分鐘后,一輛黑邁赫駛離市區,沿著海岸線公路向南行駛。云箏靠在車窗上,看著窗外飛速掠過的海景,過玻璃在睫上投下細碎的金影。
"去哪里?"終于開口問道。
傅凌鶴的角勾起一抹神的笑:"。"
車子最終停在一私人海灘的口。這片沙灘是傅氏集團早年開發的度假區中最私的一,只對極數人開放。
細的白沙在下泛著金的澤,海浪輕輕拍打著岸邊,留下一道道潤的痕跡。
傅凌鶴從后備箱取出一個巨大的野餐籃和一條羊絨毯,另一只手穩穩地扶著云箏走下木質棧道。海風拂過,帶著咸的氣息,吹散了云箏鬢角的碎發。
"小心臺階。"傅凌鶴提醒道,手掌始終護在腰后。
他們在距離海浪十幾米遠的地方停下。
傅凌鶴練地鋪開毯子,又從野餐籃里取出幾個靠墊,為云箏搭建了一個舒適的休息。
"坐這里。"他扶著云箏慢慢坐下,然后變魔般從籃子里取出一杯還冒著熱氣的姜茶,"吳媽準備的,說對孕吐有好。"
Advertisement
云箏接過杯子,溫熱的從指尖傳來。小啜一口,甜中帶辣的過嚨,暖意從胃部擴散到全。
"你不喝嗎?"云箏把杯子遞向他。
傅凌鶴搖搖頭,從籃子里又拿出一個保溫杯:"我有咖啡。"他頓了頓,補充道,"低因的。"
云箏忍不住笑了。自從懷孕后,傅凌鶴就把所有咖啡都換了低咖啡因的,說是要和"同甘共苦"。
、海浪、微咸的海風,還有邊人溫暖的陪伴,云箏覺口的悶痛漸漸消散。
掉涼鞋,赤腳踩在細的沙粒上,著沙子從腳趾間溢出的奇妙。
"想去海邊走走嗎?"傅凌鶴問,已經站起出手。
云箏點點頭,把手放進他寬厚的掌心。傅凌鶴的手掌溫暖而干燥,指腹有一層薄繭,那是常年握筆和健留下的痕跡。
這雙手既能在一場商業談判中簽下上億的合同,也能在深夜為輕輕按筋的小。
他們沿著海岸線慢慢走著,留下一串深深淺淺的腳印。云箏的腳印小巧致,傅凌鶴的則寬大有力,兩串腳印織在一起,又被涌上來的海浪溫地平。
"凌鶴,"云箏突然停下腳步,指向遠,"你看。"
夕正緩緩沉海平面,將整片天空染金紅。云層被鍍上一層瑰麗的暈,海面上跳著無數細碎的金,仿佛撒落了一地的鉆石。
傅凌鶴卻沒有看風景,他的目始終停留在云箏臉上。夕的余暉為鍍上一層和的金邊,睫在臉上投下扇形的影,角微微上揚的弧度比任何風景都更讓他心。
"真。"他低聲說,卻不是在說風景。
云箏似乎察覺到了他的視線,轉過頭來,正好撞進他深邃的眼眸中。那一瞬間,海風、浪聲、夕,一切都仿佛靜止了。傅凌鶴緩緩低頭,在上落下一個輕如羽的吻。
Advertisement
這個吻不帶任何,只有無盡的珍視與溫。云箏閉上眼睛,著他間的溫度,聞到他上淡淡的雪松香氣混合著海風的咸。
當他們分開時,夕已經沉下去大半,天空呈現出夢幻的紫紅。云箏突然到一陣疲憊,懷孕后的力總是不如從前。輕輕靠在傅凌鶴肩上,打了個小小的哈欠。
"累了?"傅凌鶴立刻察覺到的狀態。
云箏點點頭,有些不好意思:"走不了。"
傅凌鶴二話不說,在面前蹲下:"上來。"
云箏猶豫了一下:"我很重的..."
"箏箏,"傅凌鶴回頭看,眼神堅定,"你現在的重加上兩個孩子,還不到我平時健負重的一半。"
云箏這才小心翼翼地趴上他的背。傅凌鶴輕松地站起,雙手穩穩地托住的彎。他的背寬闊而溫暖,線條分明卻不會硌人。云箏把臉在他肩頸,能清晰地到他有力的心跳。
"睡吧,"傅凌鶴的聲音從腔傳來,帶著令人安心的震,"我帶你回去。"
云箏迷迷糊糊地點頭,眼皮越來越沉。傅凌鶴的步伐穩健而均勻,像一艘在平靜海面上航行的船,讓不由自主地放松下來。星星鈴鐺隨著他的步伐發出輕微的聲響,像一首溫的催眠曲。
半夢半醒間,覺到傅凌鶴小心翼翼地踏上別墅的木質臺階,作輕得像是在搬運什麼易碎的珍寶。門鎖開啟的電子音,空調運轉的細微嗡鳴,然后是的被褥。
"箏箏,換件服再睡。"傅凌鶴的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云箏勉強睜開眼,發現自己已經躺在臥室的大床上。傅凌鶴正單膝跪在床邊,手里拿著一件質睡,眉頭微蹙地看著擺上沾的沙粒。
Advertisement
"唔...明天再換..."云箏翻了個,想要繼續睡去。
傅凌鶴卻輕輕扶住的肩膀:"沙子會硌著不舒服。"他的聲音溫卻不容拒絕,"我幫你。"
云箏迷迷糊糊地任由他擺布。傅凌鶴的作極其輕,先是用巾去腳踝和手臂上沾的沙粒,然后幫下連,換上舒適的睡。整個過程他目不斜視,仿佛在進行一項神圣的儀式。
當云箏重新躺回被窩時,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傅凌鶴為掖好被角,又在額頭上落下一個晚安吻。
"凌鶴..."云箏在半夢半醒間抓住他的手腕,"陪我..."
傅凌鶴看了看腕表,還有幾封重要的郵件需要回復。但云箏微微皺起的眉頭讓他立刻做出了決定。他輕輕掉外套,在邊躺下,將小心地摟懷中。
"睡吧,我在這兒。"他低聲承諾。
窗外,最后一縷夕也沉了海平面,取而代之的是滿天繁星。
海浪聲約傳來,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搖籃曲。
云箏在傅凌鶴的懷抱中沉沉睡去,角帶著安心的微笑。
傅凌鶴借著床頭燈的微,凝視著平靜的睡。
他的手掌輕輕覆上尚未顯懷的小腹,那里孕育著他們的結晶。
猜你喜歡
-
完結551 章

總裁聽我的
顏可欣單槍匹馬去找未婚夫尋歡作樂的證據卻沒想被吃干抹凈血本無歸反擊不成?那逃總可以了卻沒想這男人恬不知恥找上門,百般無賴的表示。“睡了我,還想就這麼跑了嗎?”
97.1萬字8 19077 -
完結242 章

冷少的逃跑嬌妻
在陸琪琪20歲生日那天,不小心誤睡了總裁,還將他當成了牛郎,隨后甩下100塊大洋離開。向來不注重感情的冷慕晨卻對陸琪琪香腸掛肚了5年。5年后,陸琪琪帶著天才可愛寶寶回國,再次偶遇了冷慕晨——“5年前,我讓你逃走了,這一次,我是絕對不會放你走了的。”冷慕晨對著陸琪琪愣愣的說道。
56.9萬字8.14 28173 -
完結1094 章

南太太馬甲A爆了
父母從小雙亡,蘇清歡從小受盡各種寵愛,來到城市卻被誤以為是鄉下來的。姑姑是國際級別影后,干爹是世界首富。蘇清歡不僅在十五歲時就已經畢業修得雙學位,更是頂級神秘婚紗設計師Lily,世界第一賽車手,頂級黑客H。當蘇清歡遇上南家五個少爺,少爺們紛紛嗤之以鼻……直到蘇清歡馬甲一個個暴露,五位少爺對她從嫌棄分別轉變成了喜歡愛慕崇拜各種……
193.8萬字8 127400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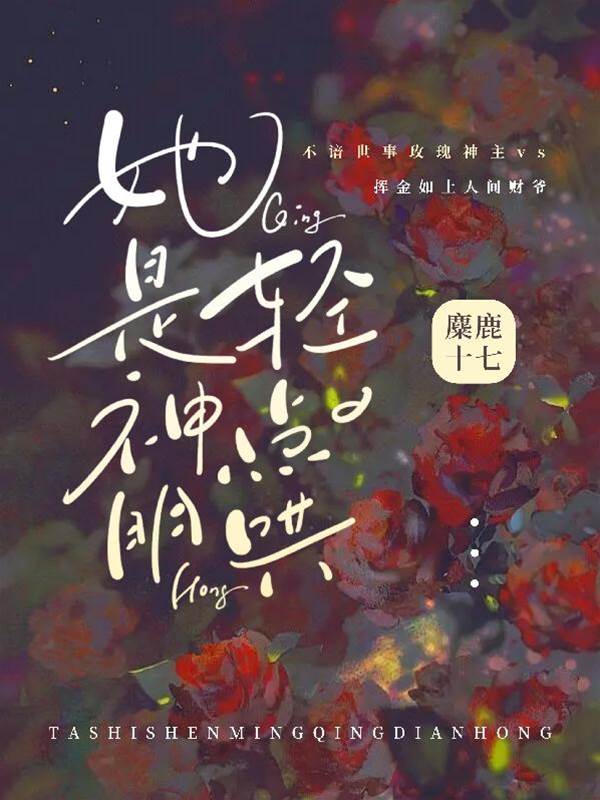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連載138 章

蓄意嬌養誘她入懷
【蓄謀已久+甜寵 + 曖昧拉扯 + 雙潔1V1 + 6歲年齡差】【人間水蜜桃x悶騷高嶺花】 南知做夢也沒想到,真假千金這種狗血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狗血的是,她被下藥,把叫了12年的顧家小叔叔給睡了。 怎麼辦?跑路唄。 花光積蓄在暗網更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親手養大的水蜜桃,剛啃了一口,長腿跑了。 找她了三年的顧北期忍著怒氣,把她抵在車座角落,“睡了就跑,我算什麼?” 南知:“算…算你倒霉?” 顧北期:“這事兒怪我,教你那麼多,唯獨沒教過怎麼談戀愛。” 南知:“你自己都沒談過,怎麼教我?” 顧北期:“不如咱倆談,彼此學習,互相摸索。” - 顧家小三爺生性涼薄,親緣淺淡。 唯獨對那個跟自己侄子定了娃娃親的小姑娘不同。 他謀算多年,費盡心思,卻敵不過天意。 被家人找到的南知再次失蹤。 在她訂婚宴上,男人一步一句地乞求,“不是說再也不會離開我?懷了我的崽,怎麼能嫁別人。”
1.8萬字8 7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