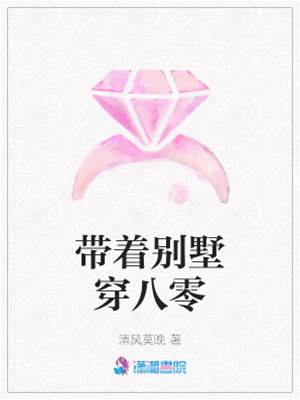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她浴缸里的魚》 第49頁
“屈歷洲。”在這時他的名字,“你聲音怎麼啞這個樣子?”
終于在這一刻后知后覺。
覺得這個聲音,略耳。當大腦告訴要理智,這個聲音還妄圖拽著沉迷,詞句音腔流蠱頹靡,字字纏絞的心。
而事實上,游夏絕不是個會被輕易的人。
上一次令置險境地被,是那個男人。
屈歷洲怔了怔,又很快恢復神。他淡淡掀眸,斂起多余的緒,平靜注視的漆黑眸底閃著微妙而不可名狀的芒。靜謐。又妖異。
他下頜稍含,看著好半天才溫吞吐字:“嗯,有點了。”
誠然,游夏是絕對齡的。段玲瓏,紅,骨如肩薄腰瘦,又如大膩。
纖細但不干瘦。看上去像云朵一樣,實際的手卻更韌。
凹凸窈窕的曲線條,被束裹在這條墨綠的真吊帶下,被勾勒得一覽無余。當絕妙的材匹配上高傲而無畏的神態,便會令整個人都染上一層活生香的彩。
可只是單純外在,遠遠不夠的。
他要全部的注意力都必須在他上。
是他用了近乎專業的手段伎倆,迅速從自己的聲線里剔除掉另一個男人的存在,讓游夏覺得那才那個悉的聲音,是自己一瞬恍惚的錯覺。
趕走那些不切實際的奇怪想法,有些沒好氣道:“你去喝水啊,盯著我看就能解嗎!”
盯著看,當然不能。
就像一團明盎然的荷爾蒙。的語氣是傲慢,的眼睛卻會邀請,的在晾曬,的心思對他來說完全明。
旺盛蓬的生命力招搖在他眼底,
Advertisement
他不得不為心容。
于是,或許屈歷洲是在某一刻真的無法忍耐。或許,他之前的每一次“忍耐”都是突破極限,或許他比誰都清楚,之后的每一次“忍耐”也只會越來越潰敗。
他在自我完全不知覺下,慢慢傾朝游夏不斷近上來。直到人抬起白皙纖靚的小,著腳徑直蹬踹在他單側肩頭,適時阻止他的探近。
“你要干嘛?”的聲音充滿警覺。
多麼天真。多麼人。
他甚至還想繼續往前迫兩分,游夏不得不趕腳尖更用力,踩住他的肩,不準他靠近,同時語氣倨傲地警告他:“喂,屈歷洲,你可別越界。”
一臉防備警惕地命令他,不許越界。
可那條界線分明是先逾越的。
當在他面前這樣缺乏防范心地抬時;當的真擺更加起時;當,完全暴私卻渾然不覺時。
還是太大意了啊,夏夏。
屈歷洲低淡失笑了下,帶有近乎寵溺與縱容的味道深藏其中。他一把扣住高抬起的那只腳踝,拉下去,順勢微蜷指節,將堆疊上去的邊也一并扯下。
之后,還是繼續朝傾靠過去。但又很快停住,控制兩人距離保持在“禮貌妥當”的范圍時,他緩慢抬手,長指勾住一側的細吊帶,替挑起來。
他看上去溫潤端方,紳士依舊。
“我們是合法夫妻。”男人彎起,強調。
他的口吻有點漫不經心,眸底浮出似有若無的笑意灼燒的眼睛。重新探手進下時,他問:“所以夏夏你說,夫妻的界限該在哪里?”
屈歷洲,這個男人真的很可怕。
他問完,指尖勾起蕾邊緣,極度危險地挑起幾毫米,又是一句反問:
Advertisement
“你該不會覺得,這一層小小的布料,就是不可逾越的邊界吧?”
他接二連三的問題把游夏問傻了。
因為是自己準許的,準許屈歷洲為涂藥,準許他更進一步,竟然這樣神經大條地認為,看過底不算什麼。
完全低估了屈歷洲,也太高估自己。
怎麼會在這種時候,對屈歷洲,流……
別再想了!
出他的手,扯邊蓋住大。
好在屈歷洲沒在最窘迫的時刻繼續追問。
反而是放下藥后,起無聞地退出到病房外。就連的憤,他都給以充足的時間,讓尋找自洽的理由。
游夏當然自洽不了,這種事,篤定是屈歷洲的惡意捉弄。
才不會輸,決定天亮后,就忘掉當做沒發生過,無論屈歷洲怎麼挑釁,都不會自陣腳。
不過,沒等來第二天跟屈歷洲飆演技的機會,因為他清晨就按照約定,離開踏上出差旅途。夫妻倆連面都沒再見到。
好在恢復得很好,上午就能出院了。
日子接近七月底,雖然婚假還沒有休完,但上次在港島時小叔說過的新項目,游夏總歸記在心里,希能盡快接手。
所以下午的時候,決定空提前回公司報到。
——【津尚天闕】
津尚建設工程份集團總部大廈。
廈京市許多商圈、辦公樓、工業園科技園都是游家代建的,【津尚天闕】也在其中。
游夏穿著久違的職業裝,一襲淡綠質襯衫,擺束進純黑A字半長,高跟鞋穩當地踏進藝充分的主大樓。
作為數一數二的超級建筑公司,津尚的業務涵蓋了項目設計,土木技咨詢,公共工程監理等等,近些年也和政府合作,承接了許多古建筑修復活化的工作。
Advertisement
公司調除了資本雄厚外,社會責任這方面也沒得挑。
大樓以菱形網格藍玻璃幕墻覆蓋,兩側延展出巧奪天工的生態翼廊。頂部向收束為錐形,打造出單108層鉆石棱柱大廈,完融合建筑剛毅與流線學,
一舉為整個廈京市最高寫字樓,四大建筑地標之一。
游夏輕車路,登上電梯穿過長廊,抵達自己的辦公層。
作為一個項目執行組的組長,手下核心團隊共有十人。
到達辦公室,把伴手禮分發給組員,游夏第一時間左顧右盼地找人:
“誒?岑卓那小子上哪去啦?”
“那小子?我們倆同齡,在工作上你都不稱呼我一聲副組長?”
年輕男聲從背后辦公室門口響起。
岑卓正好從公司外面回來,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門口,姿態端正而放松,看著游夏生龍活虎的背影。
游夏猛地回頭看去,還是沒改口:“好久不見……喲,你小子怎麼弄得這麼狼狽?”
岑卓站在白熾下,高瘦影剛好被四四方方的門框封住。黑框眼鏡的鏡片遮去他幾分神采,遙遠模糊了他眼底的。
淡藍純棉短袖洗得有些發白,但料質不錯,領口依然整齊簡潔,襯得頸項線條干凈利落。
一條耐臟的深灰工裝裹著兩條筆直的長,仔細看上沾了不木屑和灰漬,手里還抓著副剛下的勞工手套。
見他這個裝扮,游夏也明白了,揚眉調侃:“跑施工現場視察了?岑工這麼勤快啊。”
“是啊,畢竟游工新婚月,組里缺人手,我只能多跑兩趟。”岑卓嗓音質干凈清澈,不客氣地對游夏回擊。
游夏嘖嘖不滿:“我還以為休假這麼久,你們都會想我呢,結果只是抱怨人手不夠。”
Advertisement
岑卓走進來,把手套丟進工柜里:“我還以為你結了婚能點,結果還是一樣躁。”
“哪里看出來的?”游夏不解。
“返崗第一天,連頭發都忘了收拾。”岑卓從背后經過,被鏡片下彩的眼眸,無聲劃過披散在肩背上的,澤瑩亮的瀑布長發。
他走到工位,在雜凌堆砌的桌子上,準鎖定平時早會前一定會用到的鯊魚抓夾。用唯一干凈的手拿起,遞給。
發夾被他舉到面前,從游夏的角度看過去,近他的腕骨,和遠他的下頜線,都很清瘦明晰,著甘洌的書卷氣。
再往前放眼去,就能在很近的距離看到岑卓的臉。
不像尋常工科男的沉悶長相,倒是很清秀,單眼皮眼形狹長,厚實的鏡片稍許封印值。
其實他不戴眼鏡的時候,眼睛大的。
游夏笑了笑,接過抓夾隨手盤起頭發:“我今天又不算正式上班,倒是你,頭發長這麼長該理發了。”
其實剛和屈歷洲結婚那會兒,還工作在一線,是接下古建筑群修復項目,談好細節才休假。
期間的設計和施工都是組員在做,岑卓不停跑工地,想必也是忙的很。
岑卓習慣了說風涼話的脾氣,張口也能直擊痛點:“你嫁去屈家那種大戶人家,家長里短的不好理吧,還有心思管我頭發?”
“我……”游夏一噎。
還真給他說中了,先前屈戎那傻子搞針對也就算了,小姑屈明殷還時不時蹦出來,惡心兩下。
雖然都暫且解決,但過程確實曲折。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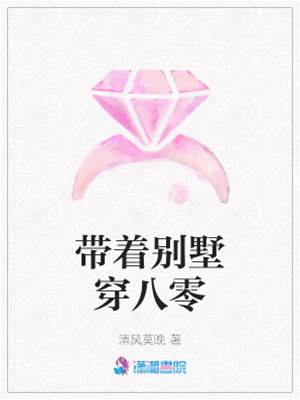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