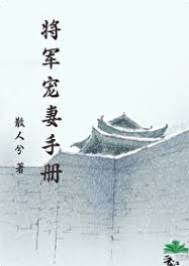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扶搖皇后》 天煞雄主 第九章 重重心思
長孫無極悠悠笑著,對孟扶搖的挑釁視若不見,端了茶淺淺啜飲,時不時和戰南笑談幾句。
孟扶搖憤怒,這世上就有這種人,不知道愧疚兩字咋寫!
一掀袂,大踏步邁出去,這回是第一場。
那位倒黴到的唐易中,苦笑著出雙劍迎上前來,還沒開戰先鞠一躬,道,‘璇璣唐易中,請戰孟將軍。”
他一個躬躬得殷勤,孟扶搖正要回禮,忽聽他低低道:“在下願意速速認輸,保存孟將軍實力,還請孟將軍手下留。”
孟扶搖似笑非笑瞟著他——這傢伙頭,看出怒火上行正想找人狠揍之,又知道自己實力無論如何也勝不了,提前賣好來了。
一個躬彎下去,也低低答,“放心,我只揍該揍的人。”
此該揍之人,殿上高坐者也。
兩人砰砰嚓嚓打起來——著實好看,雙劍舞如花,單刀曳似虹,也就是好看而已,不出一百招,唐易中一蹦三丈,將自己空門大開的撲了下來。
這種長空鷹搏兔的戰姿,向來只有強者對弱者,並且實力迥異才可以用,唐易中對孟扶搖用這招,等於把自己送上門,於是孟扶搖只好笑納。
把唐易中一腳踢了出去。
唐易中誇張的在空中翻了三個筋斗,才歪歪倒倒落地,落地後臉不紅氣不,“滿面愧”的“棄劍認輸”,大聲道:“佩服!佩服!”
孟扶搖忍著笑,煞有介事的回禮:“承讓,承讓。”忍不住多看了這個相貌平平的傢伙一眼,真是個妙人,明且豁達有趣,以後若去璇璣,倒是可以結一下。
殿上戰南鼓掌,笑道:“此戰極妙。”又問長孫無極,太子以爲如何?”
Advertisement
五洲大陸皇族都擅武,自然看得出這場比試形同兒戲,長孫無極淡淡笑道:“甚妙,這位唐兄實力不弱,本可支持兩百招上,難得他爲人淡泊。”
戰南‘哦”?了一聲,道,“太子真是誠厚,朕本以爲太子要爲孟將軍說上幾句。”
“陛下聖聰,在下豈敢矇蔽。”長孫無極出神的注視著盞中碧清茶,淺淺一笑。
“這位孟將軍,聽說很得太子鍾。”戰南試探。
長孫無極靜了靜,才答,“此子英秀,實爲人傑,爲上位者皆當之。”
“哦……此次孟將軍若在真武奪魁,無極國打算如何獎賞他呢?”
“敝國十分憾郭將軍未進前十,”長孫無極顧左右而言他,“否則以郭將軍百戰軍功,忠事王朝,又是極得人心的積年老將,若能奪真武三甲,金吾大將軍之位,必在其指掌之間。”
換句話說,無極朝廷本沒考慮過給沒啥子軍功沒啥子資歷的孟小將軍什麼煊赫的職位。
戰南目閃了閃,他約聽說過,這位孟將軍雖得太子寵,但更像是個男寵,據說太子出行止常帶著他,不避他人,而孟將軍的職位也很值得推敲,那般護城破軍大功,封的卻不是實職,不過是個尊榮的虛銜,和他的功勞不甚相符,那功勞聽起來也著實虛幻,單騎闖戎營?一人殺七將?城門被自刎?潛伏德王大軍?那麼忠烈豪壯的事蹟,會是這個流裡流氣的小子幹得出來的?八是長孫無極爲了提撥他,編的吧?
今日金殿之上,看他和長孫無極神,也很有些不對,聯想到男寵之說,戰南目一閃,覺得越看越像,長孫無極不是喜歡閒事的人,爲何肯接仲裁邀請?莫不是爲他而來?瞧長孫無極神,坦然中卻有幾分不豫,不像作假,他如果對孟扶搖故意撇清,戰南倒不敢信,畢竟長孫無極七竅玲瓏心聲名在外,戰南對他的話只敢信三分,然而他那微妙神,卻讓戰南多想了幾道彎。
Advertisement
他又忍不住看孟扶搖,也是這樣,看似神自然,卻對長孫無極很有些不滿的樣子,而且不似做作,難道這兩人之間真出了問題?孟扶搖當真如他聽說那樣,不滿男寵份,遠來天煞,待另搏一分功業?
戰南輕輕著膝蓋,在心底無聲嘆息,天煞武將人才凋零,北奇莫名其妙死在長瀚山脈,古凌風如今也了不言不將死的廢人,最優秀的兩名將領雙雙摧折,偏偏戰北野又到現在都沒擒獲,這個弟弟的存在,像一抹影,濃重的在天煞皇族心頭,他約到危機近,卻苦於沒有英才可用,要不是被如此,他怎麼會將主意打到別國將領上?
他的手按在上,覺到某依日存在的疼痛,忍不住冷的看了戰北恆一眼——西華宮那一夜,那藏了針的馬鞍讓他苦頭吃了不小,到現在還在每日治療,他怕自己真的因此廢了,堂堂天煞皇帝,卻遭遇如此命運,他每一想起都怒火上升,忍不住渾抖。
那夜那個黑年,若讓我抓住了你是誰,一定零割碎剮了你!
殿上對談旁敲側擊各轉心思,殿下爭鬥依日如火如荼,裴瑗已經勝了沈銘,接下來是雲痕對雅蘭珠。
雅蘭珠甩著十幾個辮子笑嘻嘻的跳到場中,對雲痕勾勾手指:“好好打,別指姐姐讓你。”
雲痕笑一笑,起時看了孟扶搖一眼,他眼神裡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看得孟扶搖心中一跳,卻又不明白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而等到兩人手,孟扶搖漸漸開始明白了那眼神的含義。
彩一樣滿場飛竄的雅蘭珠,有著極妙的輕功和招數,力卻不及雲痕,而且這幾日也悉了雲痕,自然不會用上那個藏了蠱的盅,那麼,對上輕功和劍法本就不弱於,力還比強些的雲痕,自然絕無勝理。
Advertisement
然而場中卻不是那麼回事。
那隻七彩的蝶,盤繞飛舞,化出流麗的軌跡,一圈一圈的纏繞住雲痕,雲痕的劍氣,明明可以瞬間破開那些彩霧,卻顯得暗淡了些,在霧中左衝右突,那青白的劍掃及的範圍,卻越來越小,從外圈看去,就見彩虹般的彩漸漸包圍了那一片閃亮的青白,將之一點點在了中心。
怎麼會這樣?雲痕第三是了傷,但好在不是嚴重傷,經過宗越調養,已經好了大半,怎麼突然弱到這個地步?
這場他的神氣和上場天差地遠,那些勇氣和堅持呢?他遠來天煞,不也是爲了爭奪真武三甲嗎?
第三百零八招,彩一收,青一滅,雅蘭珠掌中一柄短槍抵在雲痕頭,清脆的笑:“你輸了。”
雲痕笑一笑,笑得十分清亮坦然,隨即撤劍,無聲一禮,轉就走。
雅蘭珠立在場中,看著他背影,眼神裡也多了此奇異的神,那是佩服;隨即眼向孟扶搖一掠,翹起脣角,笑了笑。
那笑容,是羨慕。
孟扶搖已經沉默下去。
明白了那個眼神。
放棄,和犧牲。
一懷壯志的年爲了,所作出的犧牲。
他也看出了長孫無極試圖留下雅芒珠的用意,他擔心如果自己勝,未必能剋制得了來勢不善的裴瑗毒的巫蠱,所以,他把五強之位,讓給了擁有蠱王的雅蘭珠。
太淵最有希的魁首爭奪者,五強穩佔,註定要在天下武人面前實現自己的最高價值的年,僅僅爲了的安全,便放棄了自己走上真武前五位置的夢想。
天知道他爲這個機會準備了多久?天知道失去這個機會會有什麼在等待著他?
Advertisement
孟扶搖的手指抵在額心,拼命掐住自己待流出的淚。
當初對裴瑗還是太客氣了!
早該殺了!
----------
最後一,滿心鬱悶的孟扶搖正想著乾脆第一個上去擺擂,正好大開殺戒,不想臺上長孫無極突然對戰南道,“陛下,這最後一,改明日再戰如何?”
戰南皺眉,道,“太子何意?”
“今日一戰,諸位多半已疲憊,再戰怕力有不逮,”長孫無極手指虛點,微笑道,“尤其雅公主和燕夫人,都戰了兩場,如果讓們現在直接參加最後前五之爭,對們也不公平。”
戰南沉,長孫無極微笑,“在下一路行來,都聽聞此次真武大會,風霽月力求公平,連籤盒都花了心思,自不敢有拂真武公正真義……”
戰南立即答:“好。“
孟扶搖手攏在手裡,天,行,遲一天就遲一天,遲一天我一樣宰。
覺得到裴瑗的目,有意無意森冷的掠過來,這個人,和命中註定不能共存,唯一奇怪的就是,燕氏夫妻都知道的子份,爲什麼沒有告訴戰氏兄弟?燕驚塵沒有告訴也罷了,裴瑗爲什麼也不說?還是自負太高,覺得這個沒什麼用,只想自己殺了?
冷哼一聲,大步出殿頭也不回,不管後那縷牽般粘在背上的目——長孫無極,有種今晚不要來找我。
可惜認爲的有神,和某人認爲的有種從來不是一回事……
----------
當晚孟扶搖吃飯時,拼命給雲痕夾菜:“來,吃,多吃點。”不停往雲痕碗裡堆菜,似乎想用那些鴨魚來補償自己的愧疚。
雲痕只是平靜的吃,孟扶搖給多他吃多,孟扶搖夾著夾著夾不下去了,突然想起,雲痕不吃葷,平日裡吃得也很,本吃不下這麼多油膩膩的東西。
他卻平靜的吃,只因爲他不想拂逆的好意。
孟扶搖放下筷子,看著他一切如常的神,他還是那個清冷年,沉靜而銳利的氣質,像秋風原野上一竿獨自向風的青竹,不因世間沉浮跌宕而失卻亮,只向著一個方向舒展枝葉,翠葉因風搖落,心思卻靜若明淵。
他不失落,不沮喪,不覺得自己對有功,不覺得那樣的放棄是犧牲,甚至不試圖安孟扶搖——越安會越愧疚,他知道。
的好意,對他顯得蒼白又多餘。
飯桌上氣氛沉悶下來,雅蘭珠啪的一下放下筷子,不滿:“不就是我不小心贏了雲痕嘛……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孟扶搖笑笑,夾了一塊東坡給:“是,不關你的事,來吃。”
“這麼我會吐。”雅蘭珠拒絕。
“正好,明天吐裴瑗上。”孟扶搖頭也不回答,看見元寶大人棒著個肚子蹲在一邊,眼珠骨碌碌轉,不好奇,“耗子,咋了?大姨媽來了?”
元寶大人擡頭,給了一個猥瑣的笑容。
孟扶搖被那笑驚得一炸,突生不祥預,隨即便聽見外間,先吃過飯出去的鐵忽然一聲怒喝,隨即“呼!”的一聲猛烈的刀風捲起。
衆人都嚇了一跳,以爲有敵來襲,宗越一拂袖,一道白已經了出去。
白出廳門,如泥牛海毫無靜,連鐵的聲音都不見了,宗越眉挑一挑,雲痕和孟扶搖已經長而起奔出去。
先奔出去的是孟扶搖,本就靠近門口,一轉到了門檻,探頭一看立即向後一退,把後面的雲痕也撞了回去,然後立即大力關門,上閂,還拖過凳子往門後頂,拖了一個凳子不滿意,又拖一個,再拖一個,拖第三個時,拖不了。
那上面坐了人,淺紫袂,淡淡銀紋。
孟扶搖手僵住,視線慢慢上移,便見那見鬼的人穩穩坐著,含笑下,道,“扶搖,你真,知道我累了,幫我拖凳子來著。”
孟扶搖目看進那眼中半秒,二話不說,拔刀!
刀亮得像穹蒼神山上的雪,快得像掠過長青神殿上空的流星,一刀出,斷!
凳子的斷了。
四條凳被齊嶄嶄砍下來,只到個凳面,孟扶搖收刀,大笑,你坐!你丫坐!
的笑聲突然嗆在了嚨裡。
對面,凳砍落的剎那,白一閃,元寶大人推著個木墩子飛快滾了來,恰恰滾在斷了凳的凳子下,穩穩的將凳子支個正著。
……
媽的,漢和狗是世上最該滅絕的生!
孟扶搖咬牙,收刀,眼在神古怪的宗越和默然著他們的雲痕上掠過,實在沒辦法在這裡和這位腹黑祖宗糾纏,一腳踢開門直奔自己房間,一邊怒喝,“長孫無極你有種就不要跟來……”
“我沒種纔不跟來。”長孫無極拎著元寶閒閒跟在後,“扶搖……”
‘閉!”
“吱吱!,
“閉上你的鳥!”
元寶大人委屈,明明是鼠,咋了鳥?
孟扶搖一腳又待踢開自己的房間門,突然覺得不對,這什麼?引狼室?霍地回,往門上一靠,道:“有話就在這裡說!”
“你真的確定要在這裡說?”長孫無極含笑,四面看了一看:,你確定?”
孟扶搖疑的擡頭一看,一把抓起窗臺上的花盆就扔出去:“窺者殺無赦!”
砰一聲花盆砸院子花樹後的暗影裡,飛狗跳,狼奔豕突。
砸完花盆的孟扶搖拍拍手,道:“太子殿下,你有話就趕說,說完我好睡覺,還有,不要問我爲什麼生氣,雖然你有問這句話的理由,但是我提醒你一句,你問了我會更生氣。”
‘我知道我問了你會更生氣,”長孫無極抱著元寶,靠在樹上,“扶搖,我真慶幸你是個掩飾不住的子。”
他頓了頓,意味深長的微笑:“多虧了你這子,我纔多覺到,我和你這一場似乎註定要永遠面對拒絕的追逐,不是全無希的。”
孟扶搖冷笑:“太子殿下,是,我承認我生氣,我不會裝模作樣的一邊說我不在意一邊在人後傷春悲秋的吐,但是請你不要自的認爲我是因爲上你才因此生氣,我只是覺得,哪怕就是朋友,也不當一邊信誓旦旦滿口赤忱,一邊瞞事實左右逢源,這人品問題很嚴重,孟扶搖很生氣!”
‘好吧,我知道你不會承認。”長孫無極有點無奈的嘆息一聲,走了過來,孟扶搖立即向後一跳,道,“別過來!”
太子殿下本聽不見。
孟扶搖又跳,“再過來我和你決裂——”
“哐當。”
絆到門檻,子向後一栽,這一栽便暗不好,不是怕自己後腦和大地做親接,而是怕某人趁此機會和做親接。
於是更快的一個翻滾,就想離劣勢,可惜某人永遠比快上一步,只覺得子一停,後背突然多了一隻手,那隻手一旦佔領陣地立即毫不停息,瞬間連點七大。
孟扶搖氣苦,眼淚汪汪的天,老天爺,你助紂爲枉爲天!
長孫無極抱起,喃喃道,“怎麼又輕了呢?有時真想把你栓在我邊……”坦然抱著孟扶搖進屋,再坦然在某些窺視目中把門關上。
屋燈火未起,長孫無極也不燃燈,將孟扶搖輕輕放上牀,取了水,就著星月之細細洗去易容,他眼神綿邈,牽般長,淡紫煙錦袖拂過臉頰,春風般潤膩,執著面巾的手指,一點點拭過額頭、眼、臉頰、鼻、最後是脣。
他的手指停在了的上脣,在某個位置,手勢極輕的按了按,似是怕按痛了,隨即悠悠一聲嘆息。
他道:‘扶搖……你總是令我擔心……”
孟扶搖不能,用眼殺他——僞君子!
長孫無極對的眼若無其事,拭完臉又去拭的手,洗去故意染上的微黑彩,他的手指在及孟扶搖右手中指時,又停了停,然後,隔著面巾,輕輕握住了那有點變形的手指。
他就那麼長久的握著,微微仰著頭,似是要將那稍稍凸起的骨節廓,藉著此刻的長久而深深刻進心底,月淡淡進來,他沉在暗影裡的姿氣韻,靜而微涼。
隨即他鬆開面巾,換了隻手,把住了孟扶搖脈門。
孟扶搖只覺得渾氣息一震,一綿長而又沉厚的真氣自脈門流水般涌,迅速流全,向傷未愈奔去,那真氣運行軌跡極其悉,正是長孫無極的家真力,下意識要提氣拒絕,眼前卻突然一黑。
某個無良的人,又把給整睡著了。
等到孟扶搖被某人開恩的點醒時,只看見靠牀著月的長孫無極的背影,他長髮披瀉,氣息懶散,聽見坐起的靜,頭也不回,輕輕道:
“扶搖。”
孟扶搖板著臉,不回答。
“佛蓮不是我未婚妻。”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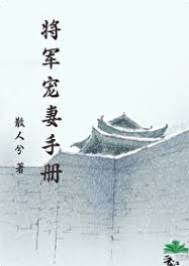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