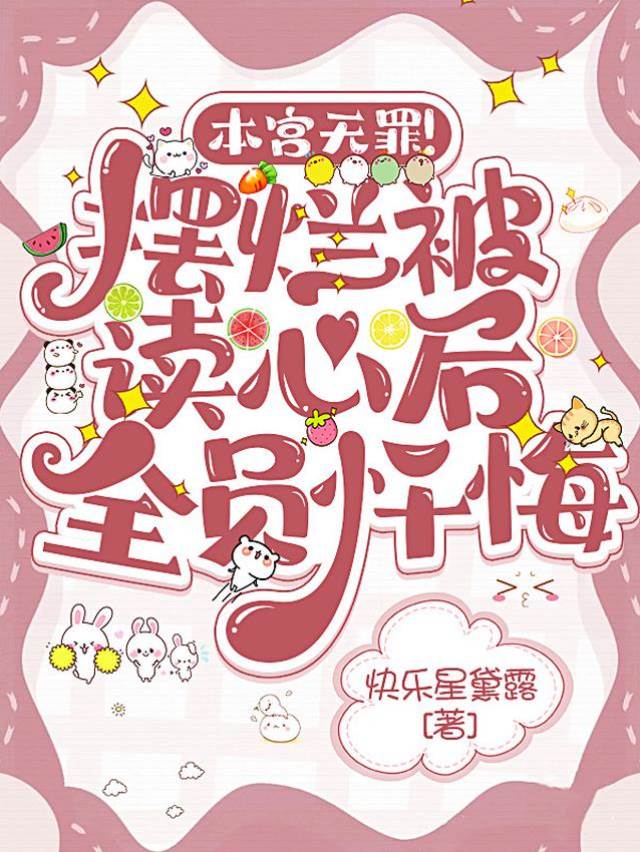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金枝》 第七章 2女1男
馬車駛出城外,視野便開闊了起來。
只是今日出城燒香的馬車實在太多,被馬蹄揚起來的灰塵遮天蔽日般的阻擋著人的視線。小虎子被灰塵嗆得眼淚直流,衛氏心疼得不行,連忙將人捉了回來。
這時候賀家走在前頭的馬車速度慢了下來,衛氏的這一輛馬車也跟著減緩了行速。萍兒探頭出去與車把式說了幾句話,回頭便稟報道:“太太,好像是元大人家的馬車在后頭,太夫人吩咐走慢一些,等元家的馬車來了一起走。”
李嬤嬤掀開車簾子往外看了一眼,皺眉道:“雖然路還寬的,但是兩家的馬車一起走的話是不是了點?”
衛氏正在喂小虎子喝水,頭也沒有抬:“元夫人是晚輩,怎麼會與太夫人的馬車并駕齊驅,元家不會如此行事的。”
李嬤嬤想了想,覺得也是。
元夫人跟跟著太夫人的馬車走不合適,跟在賀家晚輩的行列里更不合適,還不如走在后頭。
果然,沒過多久賀家的馬車速度又快了起來,而元家的車馬依舊在后頭。
從賀府到保安寺只不過是半個多時辰的車程,因出門得早,馬車抵達保安寺時還不到辰時,賀家的馬車在寺廟下的山門前就停了。燒香拜佛講究心誠,從山門到寺門這一段路是需要香客自己走上去的。
賀家的人下了馬車沒多久,元家的馬車就到了。
賀家與元家走得近這是京城的人都知道的,賀家的太老爺與元家的太老爺當年是拜過把子的兄弟,兩人甚至還玩了一出指腹為婚,只可惜賀老太爺開頭幾個生的都是兒子,而元老太爺只有一個獨子,等到賀太夫人生出兒的時候元老太爺已逝,元太夫人早已為獨子另配了淑。元家現任當家是元老太爺的孫子元丞,現任兵部右侍郎,深得當今皇帝重用。
Advertisement
元夫人張氏帶著兒媳秦氏走了過來,與賀家太夫人見禮。
賀太夫人對張氏和秦氏表現得很親切,是長輩對晚輩的親切:“你們家那兩個小子呢?怎麼許久不到我們府里來玩了,上回漸小子還給我們表演了什麼口技,逗得我喲,那日飯都多吃了一碗。”
元太太秦氏皺了皺眉,張氏卻是笑容溫和地道:“您喜歡他是他的福氣,這陣子我拘著他在家里讀書呢,等過些日子我讓他去府上拜見您。”
賀太夫人不以為意地道:“他們的祖父都是行伍出,我們兩家的小子們哪里是讀書的料?等日后蔭個武職也就罷了,你也別太拘著他的子了,男孩子野點就野點,可不能當病貓來養著。”
這時候賀家二夫人恰到好地話道:“我聽說漸哥兒兵法武藝都學得不錯,有他曾祖父當年的風采,淳哥兒卻是學問做得好,有文狀元之才呢。對了,兩位哥兒呢?今日怎麼沒瞧見?”
賀太夫人被轉移了注意力,往元家的人群里看了一眼,只看到秦氏的小兒元湘,元漸和元淳兩兄弟卻不在。
張氏道:“他們騎馬來的,還在后頭,我們先進寺如何?”
眼見著后頭又有馬車行來了,們在山門前也不好,兩家人便一同進了寺。賀太夫人一路上都拉著元夫人在說話,元夫人都含笑聽著。
元家姑娘元湘看了看跟在衛氏邊的賀林晚,刻意走慢了幾步,等賀林晚趕上來,卻始終與保持著兩三步遠的距離。
“賀大姑娘。”元湘朝賀林晚點了點頭。
賀林晚也笑著回禮:“元大姑娘,”
元湘愣了愣,又看了賀林晚一眼,然后才道:“我二哥有東西想要給賀三爺,等會兒你來找我,我把東西給你。”
Advertisement
兩人說著話,腳步就慢了下來,漸漸的走到了隊伍末。衛氏回頭看了一眼,見賀林晚是與元湘在說話,便由著們去了。
賀林晚想要打聽掛墜之事,自然是連忙應下了,惹得元湘又看了一眼。不過元湘與賀林晚的關系并不近,所以什麼也沒說,說了幾句之后就跟著自己的母親走了。
寺里的知客僧先帶著賀家和元家的人去休息,然后再去大殿進香,賀家和元家自然被安排在了同一個客院里。
賀林晚先跟著衛氏去凈臉凈手,喝了一盞茶休息了片刻,然后便打算去找元湘。
衛氏倒是沒有阻止,只是面容嚴肅地代道:“元家姑娘子溫順,知書達理,你與在一起玩我是放心的,只是你不可欺負知道嗎?”
賀林晚無奈地應了一聲便出了門。
讓丫鬟打聽了元家姑娘歇腳的地方,賀林晚便找了過去,只是還沒走到房門口就聽到院子里有一道甜的聲音以天真的語氣道:“元二哥,你上次給我三哥找的那一套十二個的不倒翁伶兒也很喜歡,元二哥能否為伶兒也尋一套來?伶兒想送給四妹妹當生辰禮呢。”
一個溫和靦腆的年聲音道:“好,我托人去幫你找找看。”
賀林晚走近了就看到一對年男站在院子里的玉蘭花樹下。
那一桃的衫,材小,容貌俏,笑容甜,正是賀家三姑娘賀伶。與站在一的年大概十二三歲的年紀,生得面白如玉,紅齒白,左邊的眉尾有一粒米粒大小的紅痣,端的是一副好相貌。
賀伶先看到了賀林晚,沖著意味不明地甜甜一笑,轉頭卻是對那年聲道:“元二哥你對伶兒真好,伶兒正跟嬤嬤學腌餞,等做好了就讓人送去元家給元二哥嘗嘗。”
Advertisement
那年正要說話,轉眼也看到了正朝他們走過來的賀林晚,面上一滯,顯出了幾分尷尬之,甚至還忍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賀林晚看到他的表正有些奇怪,賀伶卻是突然面上一慌,立即躲到了那年后,看著賀林晚的表有些懼怕。那年看到了,想也沒想就往前踏了一步擋在了賀伶前。
賀林晚不知道他們這是在演哪一出,便站了步子多看了他們幾眼。
這時候,賀林晚的大丫鬟春曉急急忙忙地湊到賀林晚耳邊小聲道:“大姑娘,三姑娘這是故意氣您的,元二爺只是脾氣好,肯定看不上那德的,您千萬別氣,氣您就輸了!您忘記出門前太太代的話啦?您若是在這里了手,回去肯定又會被足的!”
賀林晚皺了皺眉,沒有說話。
春曉以為不肯聽勸,一著急,拉了拉的袖聲音更小地道:“您要是實在氣不過,就暗地里整整,上次您的往兜帽里放十幾只大蜘蛛那事兒就做得有勇有謀,很有將軍風范!這回咱還這麼干!”
賀林晚面怪異地看了春曉一眼:“你這狗頭軍事做得還真不錯。”
春曉聽著這語氣不對,先是愣了愣,不過以前給大姑娘出主意的時候大姑娘沒夸過,所以也淡定了:“奴婢不用您的賞,您好好兒的別惹太太生氣奴婢就滿足了。”
賀林晚:“……”
其實這都是春曉的肺腑之言,當大姑娘的丫鬟容易麼?要想法子讓犯錯,在太太面前能代得過去,又要小心翼翼的不惹得這位祖宗發脾氣,這些年關于春曉的丫鬟生涯,是想想就是一臉的淚。
賀林晚面無表地點了點頭:“你說的對。”然后目不斜視地從那對年男面前走過去了。
Advertisement
躲在元二爺后的賀伶,原本看著賀林晚的目還帶著些挑釁,但是當賀林晚對視而不見之后,那挑釁就變了震驚。
以往以這種方式招惹賀林晚的時候,賀林晚沒有哪一回不上鉤,因為賀林晚最不能忍的就是別的孩子在面前接近元淳。
元淳也愣了愣。
正在這時候,元湘的房門“吱呀”一聲打開了,元湘出現在了門口。看了一眼已經走到門前的賀林晚,又看了看站在庭院里不的元淳和賀伶,皺了皺眉。
賀伶怯怯地開口道:“大姐姐,你是跟著我過來的嗎?我和元二哥只是說了幾句話而已,你別生我的氣。”說著賀伶連忙松開了剛剛“急之下”拉住的元淳的袖,低著頭站到一邊去了。
元淳見賀伶那委屈萬分又不敢言的模樣,想起賀林晚以前當著他的面欺負賀伶的事,心里不由得也升起了幾分惱怒。
“賀大姑娘,賀三姑娘只是想托我給找一樣東西送給賀四姑娘做壽禮而已,你……你不要小題大做,欺凌弱小!”
元淳溫和,就算的發了怒也是斯斯文文的,加上他容貌俊秀,生起氣來臉上微微發紅,眉角那顆朱砂痣更是紅似滴,很是有些秀可餐。賀大姑娘以前就很喜歡看元淳這副模樣,所以有時候總是有意無意地故意惹元淳生氣。
不過現在的賀林晚卻是懶得搭理這對自說自話不知所謂的年男,若非有事要找元家人詢問,早就轉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40 章

穿書之貴女咸魚日常
十三年后,那個科考落榜的少年郎李臨拿著一塊玉佩上門來要娶晉寧侯府的千金小姐。帝城轟動,紛紛在猜想晉寧侯府哪個千金倒了八輩子的霉,要嫁給這個癩蛤蟆。穿書的蘇莞暗搓搓地想,大伯家的嫡女是重生的,二伯家庶女是穿越的,她這個開局第一場就被炮灰掉的小炮灰,要智商沒智商,要情商沒情商,算了,咸魚點,還是趕緊溜吧。可是沒想到,她...
206.7萬字8.18 27162 -
完結1433 章

醫妃張狂:厲王靠邊站!
前腳被渣男退婚,厲王后腳就把聘禮抬入府了,莫名其妙成了厲王妃,新婚夜差點清白不保,月如霜表示很憤怒。老虎不發威,當她是病貓?整不死你丫的!…
221.3萬字5 93988 -
完結622 章

重生後,將軍她被冷戾王爺嬌寵了
她是北國赫赫有名的女戰神,守住了天下,卻防不住最信任的人反手一刀。 被渣男親妹算計隕命奪子,慘死重生后成了逃命的小可憐,轉頭嫁給了渣男他弟。 外阻南境,內聯七絕,天下消息盡在她手。 這一次,渣男的江山,狠毒妹妹的狗命,她全部都要! 她手段果斷狠辣,卻在那個清冷病弱的王爺面前破了功 磕磕巴巴:“我,我也不清楚是原來孩子是你的......” 冷戾的男人眼眶通紅:“你的前世是,今生也是我,生生世世我都不會放過你。 ”
110.5萬字8 34883 -
連載2433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于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不過,不是不能人道嗎?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只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里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542.7萬字8.18 13890 -
連載50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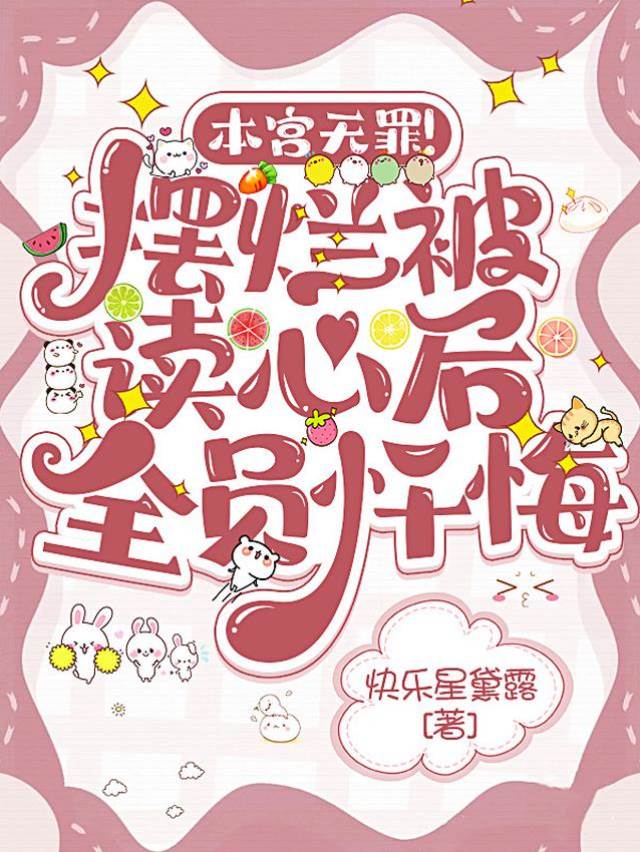
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
微風小說網提供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在線閱讀,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由快樂星黛露創作,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最新章節及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就上微風小說網。
85.5萬字8.18 3813 -
完結200 章

開局當兵發媳婦,我激活了斬首系統
穿越到古代,別人都因當兵發媳婦逃跑,就我激活了系統先挑了個潛力股,別人拼命練武殺敵攢軍功想當大將軍,我殺敵變強還能召喚千軍萬馬,一統天下不就是我的人生巔峰嗎?
37.3萬字8 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